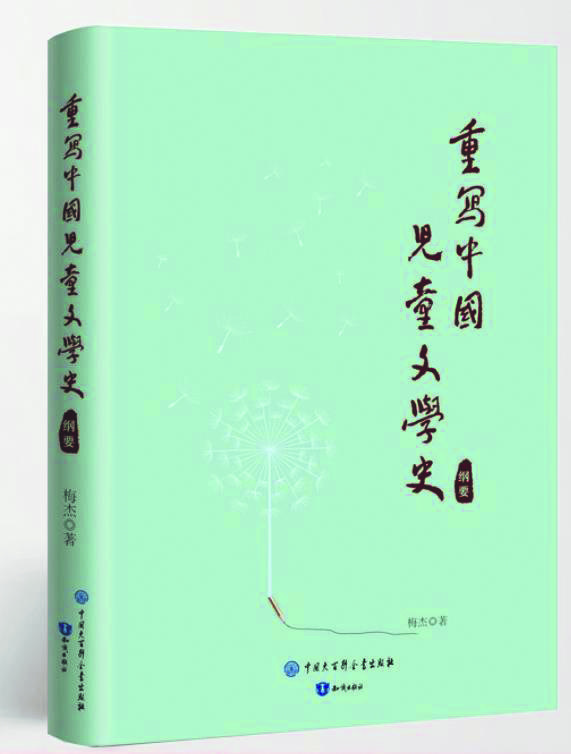2019年,梅杰在《为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做准备——“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漫谈》一文中发出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号召。因为“重写”的说法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并不多见,即便有学者自发地做着这项工作,也并没有成为学界共识。不过,这一写史理念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性或可行性,特别是当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浪潮为文学史研究开拓出新空间时,可以想见“重写”或可作为新的研究理念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尤其是随着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演进,其中一些问题亟待从新的研究视角进行阐发。去年,梅杰推出了新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此起到了表率作用。该书秉承“重写”的理念,以置身历史之外的理性客观的态度重审历史,基于审美体悟,置身文本之中反思既往研究的论断,重新划定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儿童文学史体系,为未来的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置身历史之外,用理性客观重写
在梅杰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文化组成部分,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关系,所以《纲要》的写作将部分近现代以来文学名家的作品也视为儿童文学。比如,他认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认为“梁启超可谓是中国第一代儿童读物的推手”,“大大激发了当时有意识为儿童写作的作家的写作兴趣和勇气”。不过,宏大的历史观并不意味着无边际地泛化研究对象,在扩大研究视域时,梅杰也意识到这种视域可能面临的困境——虽然个人写作的文学史有着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但也由于是个人写作,难免带着研究者的预设观点,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盲区。梅杰并不避讳这一点,引入了现代阐释学的历史观,表示该书所追崇的“重写”必然是“个人化”并“带有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味道”。正因为梅杰直面这一学术写作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时刻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做到了置身历史之外进行理性、客观的评价,时刻以是否符合儿童生命特性、儿童美学精神为基准线,用这一尺度筛选着《纲要》所要探讨的对象。比如,梅杰认为古典文学的确有适宜儿童阅读的作品,但也只能视为儿童读物,因为即便古代中国“那种零星的、个别的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没有在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更没有改变‘父为子纲’‘儿童是缩小的大人’的儿童观”。探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成就,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五四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期,“儿童文学的各个文体的多个第一部,都诞生于五四时期”,但梅杰客观地辨析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史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并未将其等同起来。比如,他在评价叶圣陶的童话时,表示叶圣陶童话的重要性在于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极为新颖的童话文体范式,而不是提供极高的童话美学内涵。鲁迅对叶圣陶童话的评价是中肯辩证的,他表示“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但梅杰深入原典后,却发现后面还有一句——“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因此,即便鲁迅赞扬过叶圣陶的文章,也要回到具体语境进行整体分析。梅杰也对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做了重审,他着眼于文研会具体作家的作品,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并不足以完全代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全貌”,并从观念、语言、文体意识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作出总结性分析。比对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著作,这种表达极为少见,可见在重写理念的烛照下,梅杰摆脱了既往研究束缚,尝试进行历史的再发现。
置身文本之中,用感性温度重写
梅杰对待历史保持着理性客观的态度,同时也有文学研究者的感性自觉。即便面对经典名家,该书也给出了公正的评点及具体解释。比如,梅杰认为“冰心的《寄小读者》,也难说是一部写给儿童的散文集”,因为《寄小读者》并不是直面儿童心理所写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抒发个人情绪的写作。他还对一些评价做了澄清式的反拨——“那些误读金波的学者,分明没有站在儿童文学立场品评,而是错误地使用了成人文学的标准。金波的这种探索,我认为标志着更深入、更透彻、更自觉的儿童文学文体的建构意识”。为了论断的全面性,梅杰还引入了多学科视角分析作品。在评价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时,梅杰表示这部作品不同于该时期的其他童话,回归了文学本位,且“致力于儿童的幻想空间的开发”,但从儿童心理学来看,这部作品的教育意图不够科学。
除此之外,梅杰对“童话”一词的溯源、辨析,较为典型地突出他对文本的重视。此前,学者朱自强曾撰文详细考证,表示“中国的出版物上第一次使用‘童话’一语就是1908年11月”,这一观点目前也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和应用。但是,梅杰并未止步于此,他注意到“童话”这一文体概念虽然很早就进入到中国,但当时其承载的并不是原有的文体内涵。梅杰找到相应的文本,认为:“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猫国》自然不是一篇童话,不过是一篇故事罢了。《大拇指》有一点幻想色彩,但更多也是民间故事的味道,并不是成功的童话。而且,《童话》丛书里的作品,延续清末编译多于原创的做法,基本都是从西方作品编译而来。”如此一来,尽管孙毓修最早使用了“童话”一词,但当时的“童话”代指的是儿童文学,而不是作为文体的“童话”概念,这样的评价也就变得有说服力了。这种坚持从文学文本中生发出个人体悟的写法,也避免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研究。
个人写史的限度与向度
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性使得个人写史有着一定难度,尤其是要跳出前人的研究进行“重写”,可能更会难上加难。当然,这本儿童文学史的“重写”既不是为了全盘颠覆此前的文学史观点,也不是有意拔高某一段历史,而是在历史之外理性看待儿童文学的流变,在文本之中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进程。不过,由于这本书是从讲义演绎而来,其中一些观点如果有进一步的阐述会更有说服力。譬如,谈到诞生期(1917-1927)的中国儿童文学,该书认为“五四时期,鲁迅与周作人保持着近似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这是周作人对儿童问题的研究,启发了鲁迅”。二者之间如何的“近似”,又是否真的是“周作人启发了鲁迅”?此外,梅杰在大历史的视野下尝试融通“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边界,那么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个维度,从中外儿童文学的对话关系中勘探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变迁,这是否会为中国儿童文学刻画出一个更立体的发展状貌?
总的来说,《纲要》一书是梅杰从新视角对中国儿童文学进行回溯与反思的成果,既有对历史保持客观理性的审视态度,又有深入文本置身其中的审美判断。诚如书中引用的学者刘绪源的观点那般,梅杰也遵循着“发现不写史、不从史的角度研究就无从看到的秘密”,“运用史的眼光,通过史的视角,给关注某一时段文学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参照”。这既是重写所要秉承的原则,也是重写所要达成的目的。没有创见的学术研究只是原地踏步,而“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梅杰以一种“真实”而又“个人化”的表达,为今后儿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