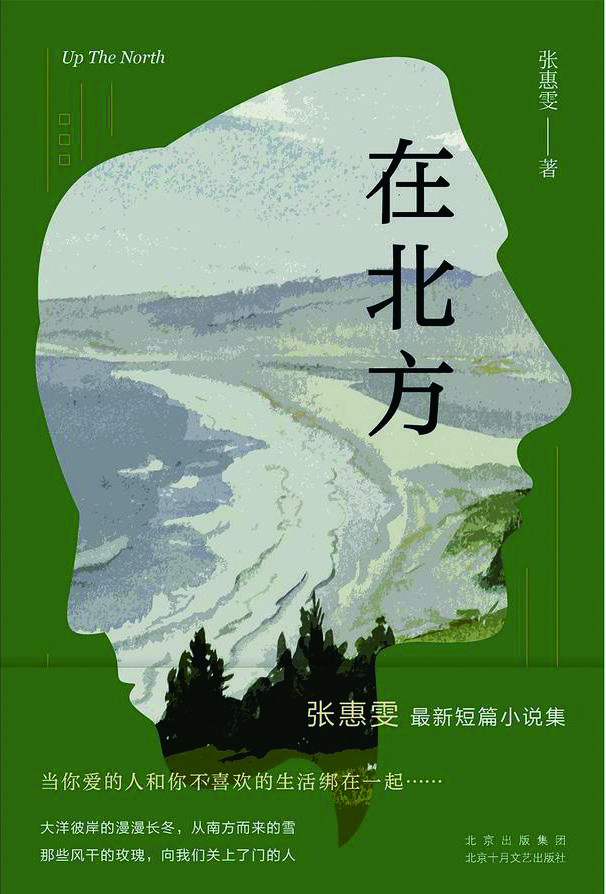远洋、异乡与女性意识,是张惠雯的小说集《在北方》中故事所携带的身份性认同和文化参照;但其文字所编织的内核,对“传统—现代”男女关系的置身其内和反思,对独立、勇敢、冷峻等气质的毫不掩饰,也同样打动读者。张惠雯把“北方”的潮湿性大陆气候——那终年雨雪丰沛的孤独与烦闷——恰如其分地融入到了其反思中。那被水汽、湖泊与森林所浸泡过的叙事,不再单纯地只携带破坏和愤怒,而仿佛雨带过后重又平复宁静的心田,看似了无痕迹,却已种下了刻骨铭心的种子。
《在北方》这部小说集的轮廓,如河流分岔而裂为两个部分:《雪从南方来》《二人世界》《沉默的母亲》三篇,皆立足于两代人、甚或三代人的关系架构,“家庭”“代沟”与“破碎”组成了叙事的核心;而《黑鸟》《双份儿》《钻戒》《奇遇》与《朱迪》,则以平面的现代男女情感为辐辏,讨论在爱欲与现实之间所作之艰难选择;而收束全书的《玫瑰,玫瑰》一篇,遗世独立于外,扩广了上述两个部分的美学,给予前文八篇一开放式的总结。值得一提的是,在张惠雯的叙事建构中,不论代际间的矛盾或是难得善终的男女关系,都好似以绳墨规矩过了审美,展现出匪夷所思的一致性:在隐隐作痛中陈述无可奈何。
“今年的雪像是从南方来,从纽约一路向北,最后到达波士顿。”“雪从南方来”的怪诞比喻,开启了张惠雯对家庭关系的思索与挖掘。小敏在感恩节时,选择向年过半百却依旧独身的父亲忏悔一桩16年前的“骗局”,但公开的秘密并不代表历史中那件事情已彻底走向尘封,恰恰相反,当年小敏设计赶走准继母的举动,反而加深了父亲在这个雪夜的孤独,并势必会持续整个寒冬。“从南方来的雪”是女儿从纽约和休斯顿突然寄送到父亲手上的信件,但刺痛他的绝非女孩少时的欺骗,而是对这一“欺骗”所产生原因的巨大愧疚。父母分裂的家庭、异国的他族感、自作聪明地引入继母……雪从南方来,但祸水之根源是否指向了自己,这一疑问也让父亲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中。
同样讲述家庭分裂下两代人之关系的,还有《二人世界》和《沉默的母亲》,前者将视角对准了一对甫建立关系的母子,后者则讲述了儿子成年时父亲对他的坦白。与《雪从南方来》一起,这三篇故事的连缀,仿佛诉说了一个单亲家庭的上辈与下辈是如何度过一生的。下辈从垂髫、成年到走入自己的婚姻,缺少父亲母亲的疼痛,始终如巨石般压在他的胸口。上辈除了不断诉说着“爸爸的车来了”和“你妈妈非常爱你”外,其余一切都十分徒劳与无奈。雪从南方来,从下辈人亦同样孤独的病症中来。张惠雯细腻地写出了不完满家庭的“诅咒”性,而唯一的疗愈,或许只有期待一场漫长的雪来覆盖伤痕。
从家庭转入爱情,从难言之隐转入愈发“难言”,张惠雯为书写当代男女提供了又一解法。《黑鸟》与《钻戒》十分相似,虽则爱情的隐忧总埋伏在日常相处中,但过于暴露的危机,也加重了“忍耐”与“理解”的限度。在张惠雯笔下,维护爱情的过程总比男女情感本身更过漫长。这使得分别来得如此急促,却也必然,即便在那过程中已到了钻戒相许和计划着共度晚年的地步。“现在,我把那枚钻戒戴在左手的小拇指上。我喜欢那种感觉:它和婚姻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美丽而无意义的装饰。”在张惠雯这里,长相厮守的结果伴随了太多的偶然和妥协,如同《钻戒》中的方杰与他哥哥,渴望的从来都是钻戒所带来的合法性,却拒绝思考“合理”与其他。
《双份儿》也讲述了一个潜藏在“合法”意义下的“合理”思考。女主听完男主讲述其如何守身如玉,拒绝了社会上污浊的习气,并英雄般地试图解救一位惊艳的妓女后,两人那暧昧的关系也就此终结。这并非出自女主对故事里妓女的嫉妒,而是通过男人的自述,更清晰地看见了躲藏在男人绝对理性背后的自私与冷漠。在《朱迪》里,“我”因为闺蜜丈夫的亲昵举动和不断来访而彻底失去了一段友谊。但在无数个受到闺蜜丈夫照顾的瞬间,“我”又何曾没萌生过突破“合法”的念头?张惠雯叙事的令人惊讶之处也在于此,我们喝下一杯杯苦咖啡式的故事,妄想提振精神,转念来,只落得沉浸于她搭建又毁掉的感情乌托邦“谎言”里。
《玫瑰,玫瑰》并没有终结这样的“谎言”,也并非释怀了家庭故事中的裂痕,但却称得上完美的结尾。从初入缅因州豪宅的想入非非,到离开时的惊悚和疲倦,青春、性压抑、中年危机、异国孤独,都被张惠雯纳入了这篇了无叙述和虚构痕迹的小说中。它是如此真实,别墅和海滩的死寂、夫妻间的窒息捆绑,如同人类首次仰望夜空的虚无时所染上的茫然无措。“从后视镜里,我看见男人反身离开,她还站在车道和马路的交叉口,不离开,也不挥手”——张惠雯好似这对举措相反的夫妻,给读者留下了言说不清的畏惧,并永远留在了相去重洋的那一边;而我们正如那开车离开的人,带着她讲述的九篇故事,刻骨铭心地重返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