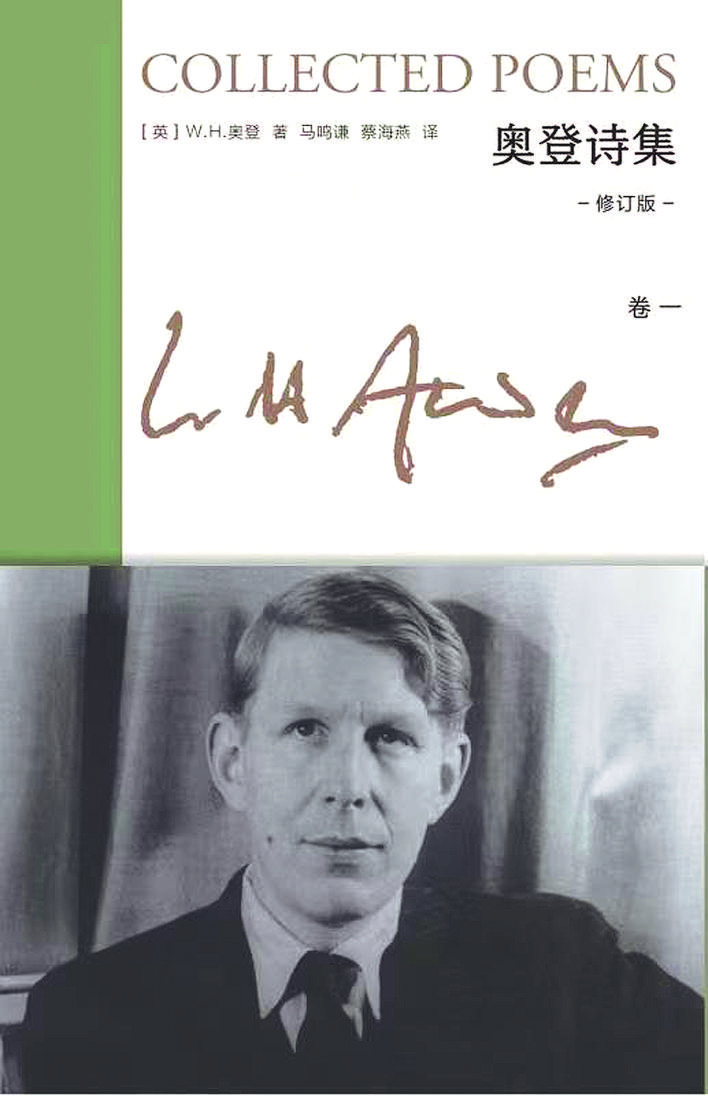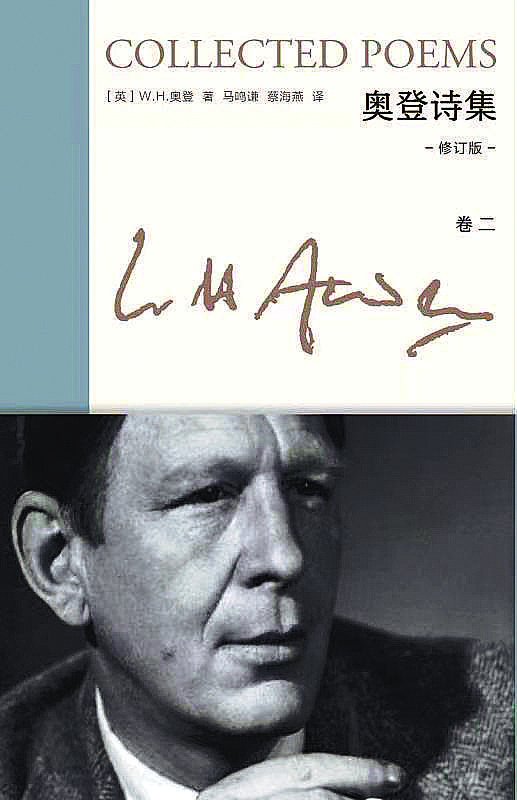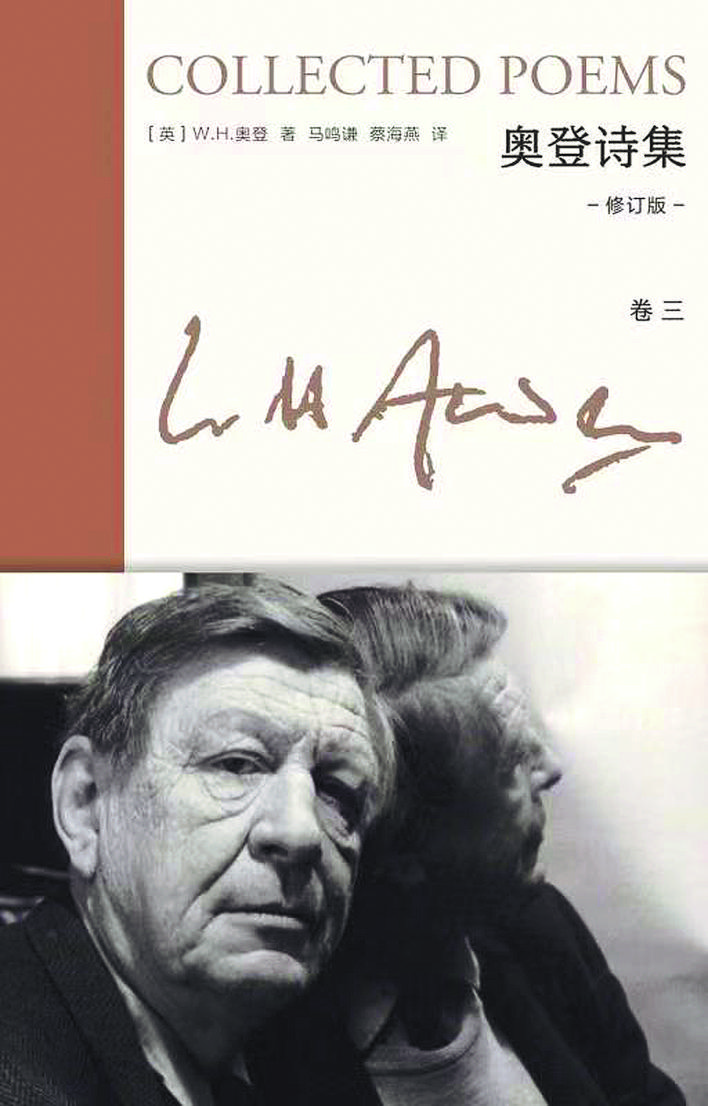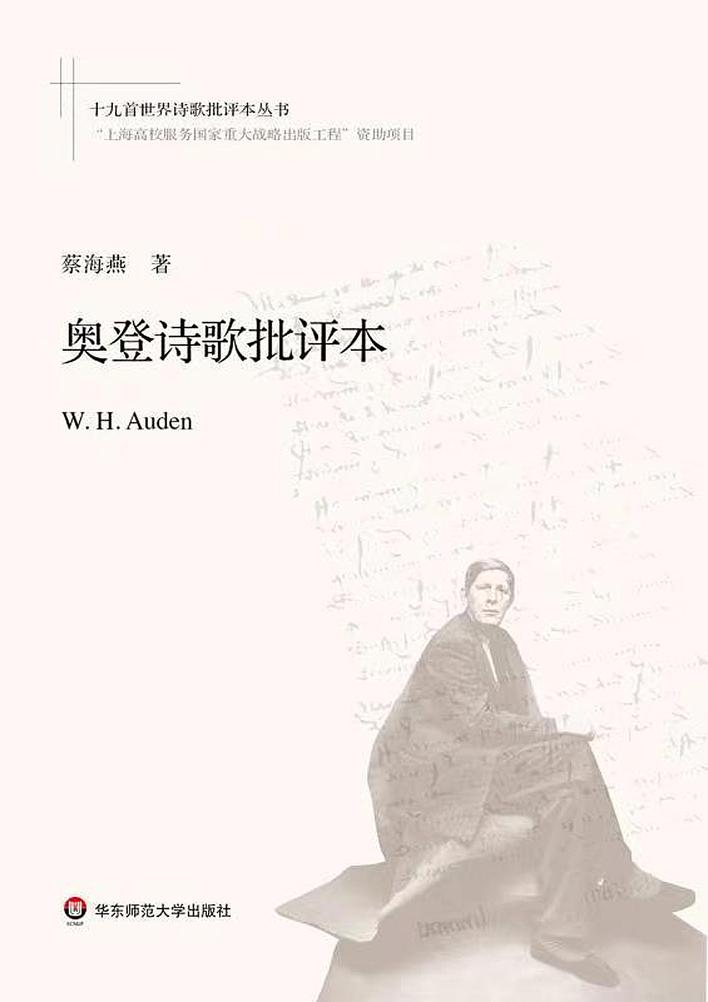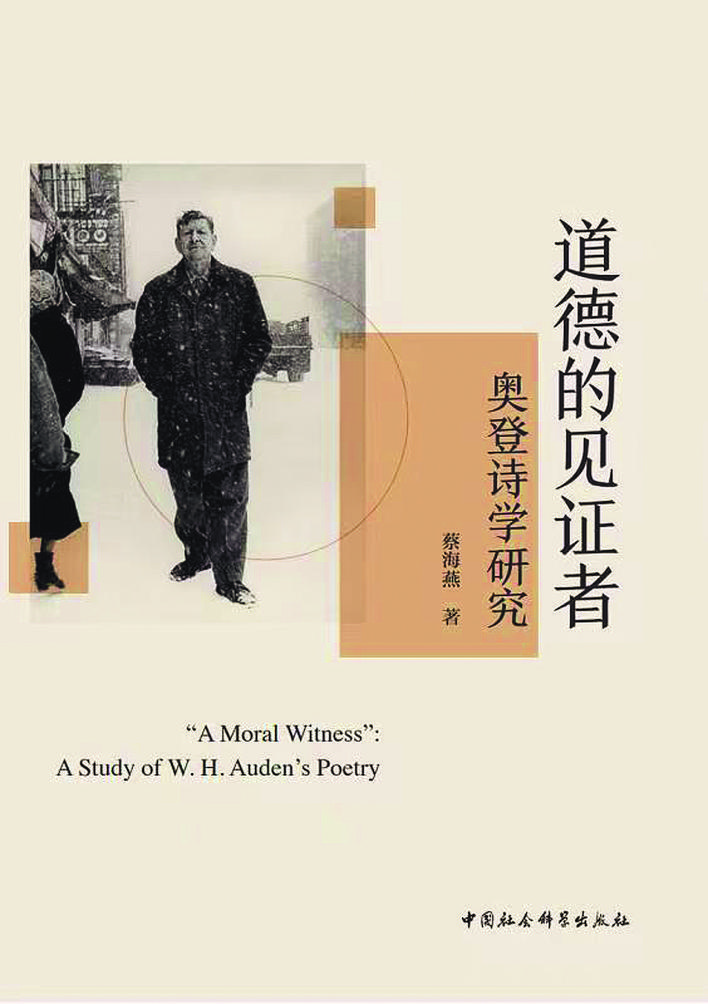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声喧哗的时代让诗人们陷入了混乱不堪的诗歌评价体系,一类诗歌强调审美功能,要求诗人专注于纯艺术和发展绝对美,另一类诗歌强调现实功能,要求诗人的作品能够参与社会行动并且救助破碎的人生。它们之间的冲突豁开了一个巨大的悬念,让诗人们在诗歌的审美和“介入”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英语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初登诗坛时,追求的是诗歌事业的成功,年纪轻轻就立志要成为“大诗人”。时代却裹挟着他向诗歌注入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他的名声连同他的创作都被时局变化和公众舆论所“绑架”,公共事务和私人情感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态势,严重侵害了诗人的独立品格和艺术操守。
“真诚犹如睡眠”
奥登于1939年初移居美国,这是他在认清了公共生活搅扰私人生活之后做出的一种合乎自我定位的理性选择,却为此背负了长久的骂名。暂且不论当年伴随他“离开战争中的英国,去了美国”的行为而掀起的轩然大波,哪怕时隔多年后,在他参与竞选牛津大学诗歌教授这一学术性教席时,人们依然纷纷调用他的“战时档案”来审度与评判。关于奥登何时、缘何做出移居的决定,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在之后的岁月里,奥登以及与他相携移居美国的小说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各自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不少解释看起来的确很有道理,但这些都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我们应该谨慎地区分其中的真实性。诚如奥登的传记作家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所说,最好的处理方式莫过于充分考察奥登彼时的特殊处境。
借助于汉弗莱·卡彭特在《奥登传》中筚路蓝缕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除了务实的金钱问题,奥登选择移居美国主要源自深层的“逃离他的公共地位”的意图。1936年的冰岛“寻根之旅”是奥登反思自己在英语诗坛处境的开始,他越来越多地思考“诗人的文化身份”“诗人与政治活动的关系”等问题,岂料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视他为左派诗人的领袖。他敏锐地发现了“藏匿在他的公共道德形象背后的复杂动机”,察觉到“自己在被崇拜、被称赞时的心满意足”。在1937年秋写给朋友的信中,奥登已经在清算自己面临的窘况:“你只能书写自己知道的东西,而这些仰赖于你如何生活……艺术家……只能说出他知道并且感兴趣的真相,这仰赖于他在哪里以及如何生活……假如他对自己的知识并不满意,便只能通过改变他的生活来获取希望得到的知识。”英国社会的期望与奥登本人的意愿逐渐脱节,这不但促使他反思自己的早年成名,也连带着深思自己在社会和时代中的位置:“那时的处境,对我来说,英国已经不适合待下去了。我在那里不可能再成长。英国的生活就像是一种家庭生活,我爱我的家人,但我并不愿意与他们共处一室。”离开,改变自己的生活,无疑可以成就一个全新的起点,尤其是选择一个迥异于老欧洲的美国新世界。
奥登后来指出:“真诚犹如睡眠。一般而言,人们当然应该假定自己是真诚的,然后将这个问题抛诸身后。尽管如此,大多数作家偶尔会遭受不真诚,就像人们遭受失眠。要补救这两种情形通常十分简单:对于后者,只需变更饮食,对于前者,只需更换身边的伙伴。”根据奥登的观察,当欧洲诗人们试图在未曾断裂的历史时空里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痛苦地感受到分裂的自我在旧社群的废墟上举步维艰的时候,生活在美国的诗人更有机会“将想象力从人之外的一切转向人,并专注于人本身”,从而更有力地捍卫了自己的“私人面孔”。
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1970年担任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时,围绕历史中的自我之真诚和真实的问题展开了系列演讲。他认为自16世纪以降欧洲的道德生活增添了一个新要素——“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考验着自我的真诚状态或品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们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流动,独立的自我意识驱使我们渴望成为一个个“大写”的人,成为忠实于自我的人。然而,我们所忠实的自我究竟是什么?译者刘佳林替特里林发出了一系列的追问:“它在何处藏身?它是随社会的变化、文化的熏陶、制度的规训、自身的努力等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呢,还是具有某种生命体的坚硬性?”显然,自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它的变动不居带来了一个事关真诚的问题,即我们该如何诚实地面对已经变化了的自我。奥登无疑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为了能够更为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在精神和诗歌事业,奥登选择移居,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声誉代价。他“更换身边的伙伴”,开启了新的创作环境,很多人将之视为他的文学生涯的分水岭,也有不少人从政治角度出发指责他“动摇易帜”“变节”“背叛”,这些论调直至今日仍不绝于耳。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声称只有两种文学声誉值得赢取的奥登——“一种是做这样的作家——也许他的地位无足轻重,但经过数代之后某位大师在其作品中找到解决某个问题的重要线索;另一种是成为别人眼中献身文学事业的榜样,被一个陌生人在他的思想密室里秘密召唤、想象、安置,从而成为他的见证人、审判官、父亲和神圣的精神导师”,应该不会在意这些批评的声音。
“一个人必须保持诚实,即便在谈论自己的偏见时”
正如特里林鞭辟入里的推导,真诚不仅是一个关乎感觉的问题。感受上的真诚是一种想象力,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牢靠。真诚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这就出现了有关真实的问题。“真实”要求更为繁复的道德经验、更为苛刻的自我认知,文学家们事实上是以语言艺术为切入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参与到事关真诚、真实和自我的纠葛之中。在对“诚”与“真”近乎苛刻的自我反思中,后期奥登否认、修改、删除20世纪30年代的部分诗歌。他自我剖析道:“对于诗人而言,最痛苦的经验是,发现自己的一首诗受公众追捧,被选入选集,然而他清楚这是一首编造的作品。就他所知或关注而言,这首诗可能不错,但问题不在这里;他就不应该写下它。”这类被否认的作品,包括现在依然被推举为他的经典作品的《西班牙》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1965年为自己的诗选撰写前言时,他直言不讳地写道:“一首不诚实的诗歌,不管有多好,总在表达它的作者从未体会过的感情或并未抱有的信仰。”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诗歌《请求》为例,指出自己“一度表达了对于‘建筑新样式’的期望”,但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现代建筑”,而是“更喜欢旧玩意”,最后总结说“一个人必须保持诚实,即便在谈论自己的偏见时亦复如此”。诚然,奥登的表述经不起推敲,我们只消通读《请求》,就会发现字里行间绝非述说建筑方面的喜好,语句的重心落在了紧接其后的“心灵的改变”。奥登在此刻意回避的,恰恰是促使他成为20世纪30年代英语诗坛领军人物的“介入的艺术”。他对那个“十年”的持续性否定,恰恰源于“诚”与“真”对他的内在良知的持续性拷问。
奥登说,“真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其实是“真实可靠”,它应该是作家最应该关注的事情:“任何一位作家都不能准确判断自己的作品可能是优秀或低劣的,不过他总能知道,即便不是立即能够短时间内知道,在书写时,他写下的东西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诗人越来越渴望由本真的自我引领,也越来越希望按照真诚的方式写作,这是诗人对自己、对真相、对诗歌这门艺术的尊重,为此需要不断支付智识和道德上的努力。
奥登的自我反思和修正态度,表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人。他对自身“不忠实”的指控,恰恰体现了他对自我的一种伦理检视。同样的反思,也出现在他对亲密伙伴、社会共同体、人类大家园以及艺术创作的深度省察。在这一点上,奥登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对自我的最大道德在于是否诚实地面对自己,尤其是身处异化力量日益猖獗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守住本心、不忘初心。
多年来,奥登一直相信,“诚”与“真”的最高形式是践行,也就是说,阅读、思考和写作,都要落实到具体可感的生活里。他曾借用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的话写道:“艺术并非魔术,也就是说,它不是艺术家传导情感、或在他人心中激起同感的手段,而是一面镜子,其中映射着人们真正的情感:确切说来,艺术的功用事实上是祛魅。”后期奥登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当中撤退,不再书写有违艺术正直的作品,也坚决抵制宣泄艺术冲动的诱惑,走上了一条强调“灵感论”和“技艺论”有机结合的创作路径,赋予诗人捍卫语言、追求“语文学夫人”、构建“语言的社群”的重任,同时赋予诗歌“见证真相”的职责——“与人类的行为一样,人类创作的诗歌也无法免除道德判断的约束,但两者的道德标准不同。诗歌的责任之一是见证真相。道德的见证者会尽最大能力说出真实的证词,因此法庭(或者读者)才能更好地公平断案”。
奥登的诗歌观,事实上是将诗歌扎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写道:“‘我64岁时该写什么?’这的确是个问题,/而自问‘1971年我该写什么’就很愚蠢了。”他深信诗歌的题材和主题、语言和风格都必须要与他本人的实际生活同步——“如果一个作品匮乏‘现在性’,也就意味着缺失了生活。”正如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门德尔松教授(Edward Mendelson)在为中译本《奥登诗选》撰写的前言中指出的,奥登认为他自己不需要刻意迎合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代环境,而要“持续不断地发现适合其年龄的新的写作方式”。作为生活的存在主义者、思想的实用主义者、诗歌艺术的孜孜探索者,奥登终其一生都专注于钟爱之事。
好友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曾谈及晚年再一次见到奥登时的情形,认为奥登的生活“一直保持着目标的一致性”:“他只专注于一个目标——写诗,而他所有的发展都在这个目标之内。当然,他的生活并非完全没有受到非文学事务的扰攘,但这些扰攘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其他人(包括我自己)都深陷于生活的各种事务中——工作、婚姻、孩子、战争等——与当初相比,我们大家都像是变了个人……奥登也在变化,但始终是同一个人。”用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梅利尔(James Merrill)的话来说,奥登主动选择了一种文学性的生活。由于始终铭记自己的独特面孔,他每走一步,都不是白费,而是积累。他不仅仅积累经验,也积累智慧。关于这一点,黄灿然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奥登不仅提供了一条成功的途径,而且提供了一条哪怕不成功,也仍然可以活得自足、自在、自信,从而免受外部力量左右的途径。”小径多分叉,许多时候无关对错,却关乎本心。
“以有限的能力,做一件通往无限的事情”
多年来,我这个“INFJ型”的人,一直以笨拙而执着的方式慢慢地靠近“INTJ型”的奥登。只因青春懵懂时偶然读到了他的一首诗,此后便义无反顾地学他、写他、译他,随着《奥登诗选》(上下卷)《“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奥登诗歌批评本》相继出版,《奥登诗集》(修订版三卷)和《奥登传》将在奥登逝世五十周年(2023年9月)之际隆重推出,以及《诗人之舌:奥登文选》将在2024年初面世,我希望自己是在以有限的能力,做一件通往无限的事情。
奥登宣称:“尽管过去的伟大艺术家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只有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才能够与死者分食面包,而如果离开了与死者的交流,就不会有完整的人类生活。”希尼(Seamus Heaney)在新世纪创作的《奥登风》一诗中借用了这个概念:“再一次像奥登说的,好诗人需要/这么做:去咬,去分死者的面包。”现在,我们每一位普通读者,也可以尽情地享用奥登留下的“面包”,因为他说过,他的作品是以独特的视角传达了他对人类普遍处境的看法。然而,要接近像奥登这样的崇尚持续发展的诗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批评家杰弗里·格里格森(Geoffrey Grigson)曾说奥登是英语诗坛鲜见的“有能力的庞然怪物”,学者雷纳·埃米格(Rainer Emig)沿用了他对奥登的界定,在《威·休·奥登:走向后现代主义诗艺》一书里戏称自己是在“驯服庞然怪物”。但对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言,奥登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驯服”的“庞然怪物”。有时候,他精心准备的文字盛宴过于晦涩难懂;有时候,他的文字符码和语词矩阵里似乎藏匿了另一张面孔;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跨越大西洋的小歌德”(《创作的洞穴》)才有可能具备的博闻多识。我们只有借助于更多的细节和信息才能揭开语言的面纱。
汉弗莱·卡彭特坦言,出于对奥登诗作“无与伦比的热爱”,他“试图呈现这些作品在他彼时彼刻的生活处境中的生成机缘,并尝试解读他的创作主旨和思想观点”。他的《奥登传》详细梳理了奥登的成长阶段、创作经历和思想演变轨迹,对他的性向选择、移居美国、皈依基督教等争议性问题都有深入的剖析和清晰的论述,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从事奥登诗歌研读必备的案头书。
我起念翻译《奥登传》,要追溯到十年前,但真正落实了版权动手翻译,是近两年的事情。在翻译的过程中,奥登的生命画卷随作者细腻的笔触缓缓铺展,时代的惊涛骇浪和个人的暗流汹涌泼洒了深深浅浅的独特印记。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我这些年来研译奥登诗歌时在各种文献资料里接触过、推敲过的细节。童蒙时期的“那个堆满书籍的房间”,奠定了奥登广博的阅读兴趣和兼收并蓄的思想内核。青少年时代的公学生活,让他在之后的岁月里始终对权威保持一份警惕,并且尽量避免自己沦为某种“权威”的代言人。成年之后渴望以“灵性之爱”抵御人世浮沉中的种种诱惑与磨难,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把爱的信仰浇灌到日常生活里,不管伴侣“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诋毁它、遗弃它、/对它抱以冷眼与怀疑”,他都“永不弃绝”。在体验了成长的欢愉、创作的激情、思想的交锋之后,衰老不期而至。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曾赞叹,奥登的脸是“深深的犁沟”、“横贯田野的犁沟”。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这就好像“生命本身细致地勾绘了一种面部景观,借以展现‘内心无形的愠怒’”。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说,四面八方的皱纹纠缠在奥登的双眼之间,形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地图。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则不无抱怨地指出,为了看清楚奥登的模样,须得熨平他的脸。最生动的描述来自奥登本人——“我的脸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被雨水打湿的婚礼蛋糕”。奥登的脸就像是他留给我们的一张上了锁的私人面孔,而《奥登传》无疑是一把适配的钥匙,借此可以敞开他盎然的诗意人生。
译文:
“有关作家的传记,”W.H.奥登宣称,“一般都废话连篇,格调也经常低俗。作家是一位创造者,而非实干家。当然,有些作品,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作品,都源于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但是,了解这些原生态的素材,并不能帮助读者从作家精心准备的文字盛宴中品尝出其独特风味。除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朋友,作家的私人生活与任何人无关,而且也不应该产生关联。”
奥登在人生暮年写了上述文字,这其实是他多年来一直秉持的观点。他甚至提出,大多数作家宁愿匿名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读者就不得不专注于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家。他尤其反对出版或引用已逝作家的书信内容,声称这种行为并不光彩,无异于趁当事人不在房间时偷阅他的私人信件。至于文学传记作家,他公然给他们贴上了“自称为学者的八卦作家和偷窥狂”的标签。
基于此,这件事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奥登于1973年9月离世后,他的文学遗产受托人公布了他的生前诉求,要求他的朋友“看完”他的信件后,烧毁手中可能留存的任何来自他的信件,并且绝不向任何人展示这些信件。奥登本人曾在去世前不久与其中一位文学遗产受托人解释过原因,表示这是为了“杜绝传记的产生”。
在奥登离世后的几个月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烧毁了他的一两封信,大多数朋友选择保留手中的信件,有些人将信件捐赠或售卖给了公共机构收藏。与此同时,他的许多朋友非但没有采取措施阻止有关他生平的书写,反而纷纷撰写了与他有关的回忆性文字(出现在各类书籍和报刊上),这为传记作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乍一看,他们似乎横加践踏了奥登的遗愿。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奥登实际上对此采取了一种教条式的态度,这种武断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往往不会反映出他的全部观点,有时候甚至会自相矛盾。
诚然,他经常抨击文学传记的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出现了一些例外情况。他几乎总是充满热情地品读此类作品,为自己的毫无原则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他说过,我们需要一本蒲柏的传记,因为他的许多诗作都源自特定的事件,只能仰赖于传记来答疑解惑;我们需要了解特罗洛普的生平,因为他的自传遗漏了很多讯息;我们需要知晓瓦格纳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怪胎;至于阅读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传记,那是因为他与艺术之间存在一种跌宕起伏的浪漫关系。换言之,奥登的“杜绝传记”之原则,恰如他的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所言,“灵活机动,随时可以放弃”。
同理,他对作家书信的态度亦如此。他通常以友好的方式评论已出版的作家书信集,只有当这些书信里的私人性内容仅仅关乎作家个人,而对理解其作品无甚帮助的时候,他才会提出批评。他自己编辑出版了梵·高的书信集,要不是别人抢先一步的话,他可能会出版西德尼·史密斯的书信集。至于他自己的信件,他生前已经允许人们在学术书籍以及类似的作品中进行大量引用。
事实上,他还留下了很多自传性作品。他曾宣称:“任何诗人都不应该写自传。”然而,他的不少作品里都带有个人生活的印记。在他的诗歌作品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自传性段落,还可以发现有些诗(包括他最长的两首诗《致拜伦勋爵的信》和《新年书简》)大体上就是自传性书写。在他的散文作品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他对生活中的各类重要事件的评述。到了晚年,他允许记者前往他的纽约寓所和奥地利的消夏宅院拜访他,准许他们发表那些显而易见地透露了他的生活细节的采访稿。
这些都为传记作家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那么,奥登到底会不会同意有关他的传记诞生?
或许可以如此解读,由于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生活本就丰富多彩,值得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是他接受传记的理由,不过,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一位艺术家的生活如果足够有趣,那么他的传记也是可以存在的,”他写道,“前提是传记作家及其读者能够意识到此类叙述与艺术家的作品毫无关系。”
当然,这一点让我们回到了奥登对作家传记的不敢苟同。但是,他曾补充道:“相反,我倒剑走偏锋地相信,他的作品或许映射了他的生活。”
——选自《奥登与传记》,此文是汉弗莱·卡彭特为《奥登传》写的序言,蔡海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