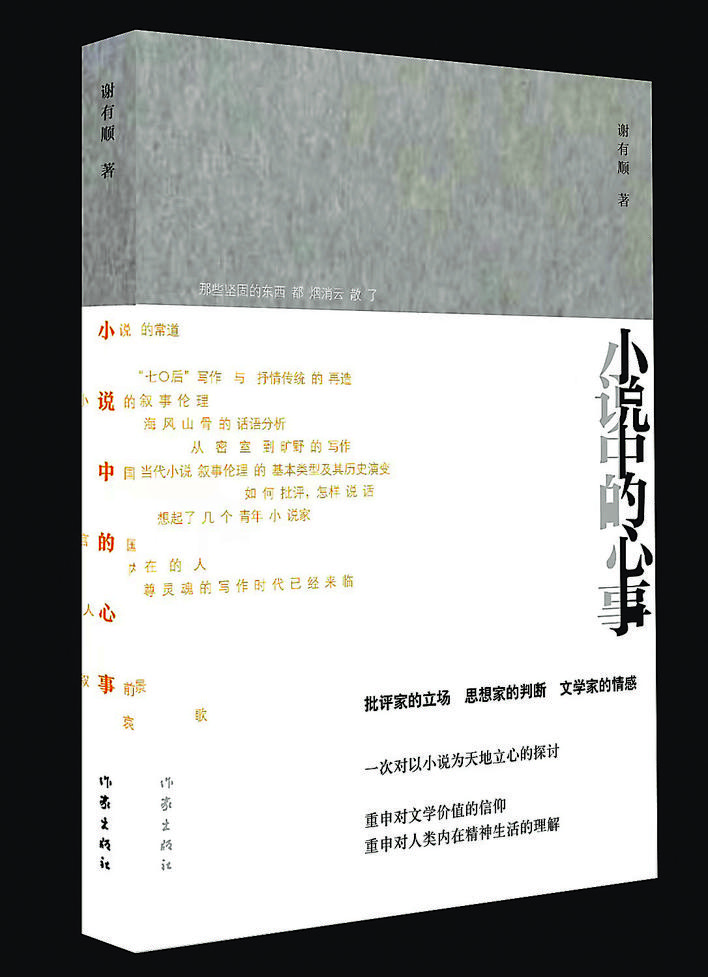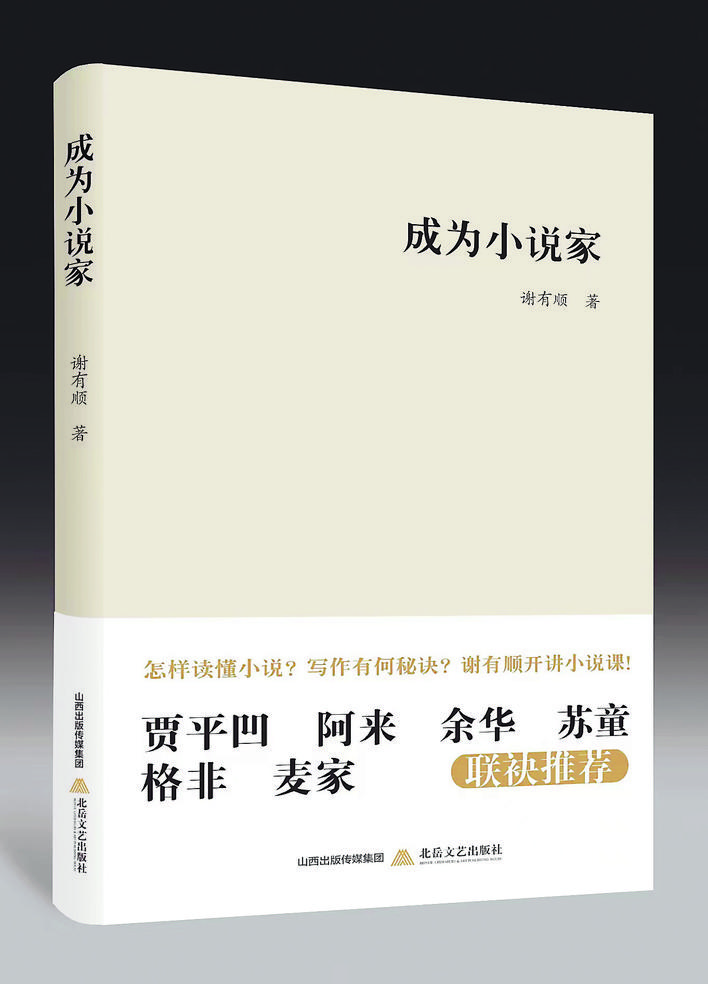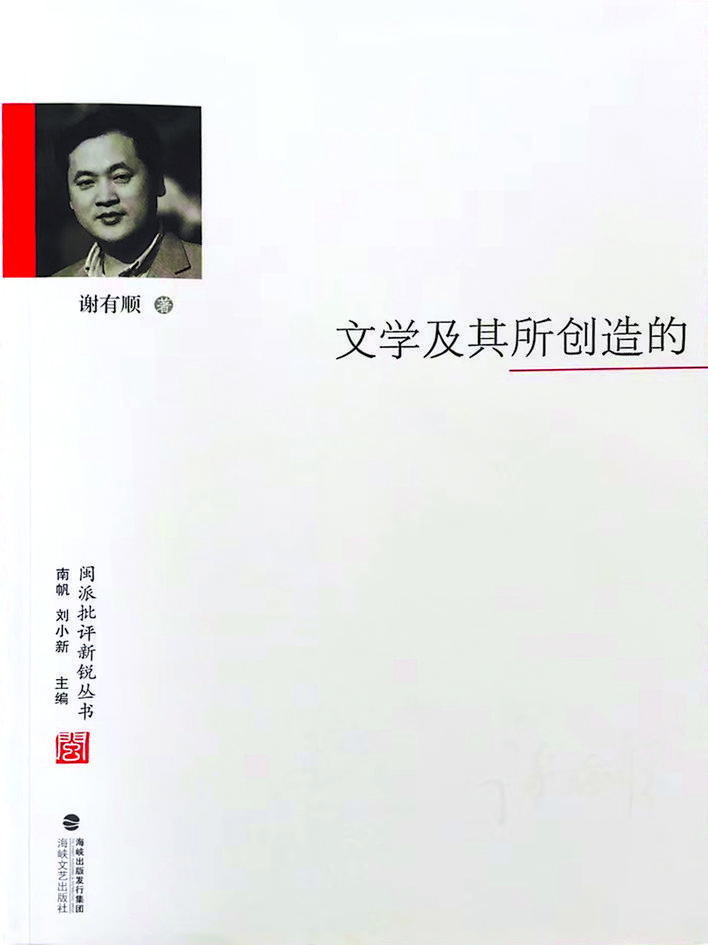最高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学问,文学也是各种生命情状的述说
唐诗人:新学期又开始了,谢老师一直很看重自己作为老师的身份,重视课堂和育人,您见到新生,会首先强调读书与学问之道吗?
谢有顺:不,我会首先告诉他们要精神成人,把人立起来,人立而后凡事举。我最近深感无正确的人,难做正确的事。记得开学初有学生来找我,一开口就问,怎样才能做好学术研究,我马上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曾经也有学生问陈三立,怎样才能把诗写好?陈三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们青年人,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他的儿子陈衡恪,就是陈师曾,一个很好的画家,秉承了其父陈三立之风,认为文人画要有四大要素,首推的也是“人品”:“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将“做人”与“人品”挺在最前面,以前会觉得是陈词滥调,现在我不这样看了。我越发觉出了这件事情之于写作和研究的重要性。
唐诗人:的确,强调人品、做人,容易被年轻人视为无趣。如今的大学教育,逐渐走向职业化、技能化。学生求学是为了毕业求职,不觉得“成为人”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教师方面,有的老师只关心学生的论文,目的是能让学生顺利毕业。至于一个学生在人格上的成长,更多是潜移默化,师生间直接以此为命题的探讨,已经很少。
谢有顺:只是做点学问,写几篇论文,如果没有诚实与人品做根基,不过是巧言令色而已。中国文论说千道万,还是脱不开《易经》的那句话,“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最高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学问,文学也是各种生命情状的述说,没有诚实的感受,如何能写出光明磊落的人生、如何塑造至大至刚的人格?朱熹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句话时说,“其曰修辞,岂作文之谓哉?”中国古人把为人、为文统起来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章学诚特别重视“论文德”,他在《文史通义》中说:“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陆机、苏辙、韩愈等人论文心、文气,“愈推而愈精”,章学诚对此是不满意的,“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其实,“文德”难论,将此议题形诸文字的人很少,但我发现,在大家的潜意识里,还是有一个“文德”的尺度,就是人的尺度。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无“格”,说得越多、写得越多,就越让人厌倦。
唐诗人:“文如其人”说法历史悠久,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不能因人废言,坚称要把人与文分开来看。
谢有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学作品、学术文章毕竟不同于科技发明、技术创造,它有人心与精神的维度,它不仅是“艺”和“术”,也是“道”,它的背后藏着一个人,这也是人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地方。我最近偶尔写毛笔字,不妨举书法为例,像蔡京、秦桧、严嵩、和珅这些奸臣的字,仅就书法而言,都是造诣不凡的,可书法界为何没人临摹他们的字?即便有所借鉴,也没人愿意被说成是师出他们。在多数人看来,人破败至此,字也就无足观了。字如其人。“世鄙者书工却不贵”,岂是字“不贵”么?是无贵重的人格。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用笔并不工整,但那是颜真卿抱着侄子的头颅写下的草稿,真情流露,满纸血泪,此悲愤底色才是艺术真正的“贵”之所在。评判艺术,尤其是像书法这种艺术,不懂“文德”这道潜流,终归是外行。
唐诗人:谈到书法,您每年春节回到乡下老家,都会写一两百副春联送给亲友,成为乡村的一道文化景观。我听朋友说,当地很多人拿到后,都舍不得贴在门上,想裱起来收藏。
谢有顺:我只是写着玩的。写字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写春联是练字的好机会,速度要快,又要通俗易懂,这很能锻炼一个人的写字能力。有些书法家会写几笔字,就各种摆架子、讲价格,写副春联都各种扭捏,真是俗不可耐。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艺术如果失了日常性、日用性,它就失了魂。前段和一个艺术家论及山水画,此公出语不凡,什么“山水,大物也”,什么“穷神变,测幽微”,其实不过是俗论。郭熙、张彦远的时代,山水是他们的基本经验,是人行走于天地间的世界观,如今山水元气尽失,画家天天固守书斋,还想大块假我以文章?今日的山水画,只是一种艺术题材而已。
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书法尤其强调日用性。那些一味标新立异、剑走偏锋的书法家,不理解日用性之于书法的意义,下笔都是出格、破格之作,故作奇崛,或线条如烂草拖泥,枯涩、躁动,从头到尾用强用狠,满纸霸蛮之气,失了静气、庄严气,也就没有文气了。心里专注,笔下才有定力,这就好比文学写作,“放笔直干”的只能是杂文,而杂文更多是小品、点缀,惟有引而不发的诗歌、小说、散文,才是文学的主流。书法也是如此。先贤传诸后世的字,王羲之、黄庭坚、苏东坡、王铎,无不中正大气,没有烂笔,没有刀锋,沉着笃定,刚健有力。书法最好的展厅,永远是朋友的客厅、办公室,甚至会所、饭馆、官衙,古代可是没有美术馆、展览厅的。古人的展厅就是日常生活的空间。假如你亲戚、朋友的客厅都不想挂你那种剑走偏锋的字,你的字只适合用来办展览,那还有何艺术可言?
好的艺术,是可以日用的,无日用,就无中国艺术。王羲之的字,既是书法,也可用来记账;一件瓷器,既可用来欣赏,也可用来插鸡毛掸子;一把紫砂壶,既可把玩,也可泡茶。这就是中国的艺术哲学。所以钱穆才说,世俗即道义,道义即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异处。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立起来的精神,都是假的,任何思想都要经历“道成肉身”的过程,才显得真实可信。
保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对知识分子而言十分重要
唐诗人: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日常生活的道德,也就是说,作家、学者还是要有现实感,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现实中人,不能只活在一种艺术的、知识的幻觉里。有些人在文字里充满热情、精神高蹈,现实生活中却冷漠决绝,毫无道德担当,这种分裂也势必影响我们对一个人作品的看法。
谢有顺:以大家比较熟悉的海德格尔为例。希特勒上台不久,海德格尔就与纳粹合作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尽管不到一年他就离任了,但战后对他的争论从未停止。海德格尔的弟子马尔库塞曾三次写信给他,希望他所敬重的老师能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表示忏悔,他不希望自己的老师在思想史上留下擦不去的污点。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无辜的,有罪的不过是他的政治行为,他希望海德格尔借着忏悔,从一个有政治缺陷的日常的人向伟大的哲学家回归。但海德格尔拒绝忏悔,而且在回信中极力为自己辩护,这让马尔库塞极其沮丧、失望,从此师徒反目,再无交往。试想,当年海德格尔如果接受学生的劝告,发表一个忏悔声明,修复自己在日常人格上的缺陷,他的哲学形象肯定会更加有力。艺术和学术都是精神的事业,是呈现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以及见证人类灵魂的美和力量,以此为志业的人,读者不可能不对他们提道德上的要求。
再以我们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教授为例。他何以一直被视为学术精神、自由人格的典范?其实并没有几个人读得懂他的书,多数人对他的学问也所知甚少,但自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风行以来,陈寅恪的道德形象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他的学术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出,学界从未轻视人格和道德的力量。
唐诗人:多数人对陈寅恪的认识,只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而已,这句话的影响肯定比他的学术著作的影响大。但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毕竟少,文化史上经得起追问的、真正文如其人的人物也不多。人心比山川还要深险,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复杂性,人与文的一致恐怕也只是一个理想,很难企及。
谢有顺: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而且也知道很多人都不认同文如其人的观点。钱锺书就不认同,他说,文章写得纯正古雅,不见得本人就是正人君子,文章写得绮艳华丽,也不能说作者一定就是轻浮的人。大奸大恶的人也可能作出令人惊叹的文章来。但我作为老师,总不能因为知道人与文很难一致,就去教导学生写作是一套、做人是一套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要让学生在追求纯正学术的同时,充分展示出自己的道德勇气。只有后者能保证他成为这个社会真正积极、健康的力量。我现在对知识的信任度越来越低,无知固然可怕,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例子也不少。多少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毫无见识,思维之简陋令人吃惊,他们关于专业的知识很多,但关于历史和道义的知识太少了。他们有专业知识而来的事实判断力,缺乏一个读书人应有的价值判断力。
前一段读乐黛云的《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一文,她谈到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季羡林等几位北大前辈后说:“大凡一个人,或拘泥于某种具体学问,或汲汲于事功,就很难超然物外,纵观全局,保持清醒的头脑……知识分子应保留一点创造性的不满的火星、一点批判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我越来越觉得,能否保持一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真是太重要了。任何学问,终归是要回到社会中去的,学问中人也迟早要以真面目示人,尤其是做老师的,自己的言行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影响到周边的人,假若你的人格破产,你的存在无益于世,那就会像一个学者所说的那样,终其一生所行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是苟且有术,行路坎坷也不过是苟且无门。暑假我到福州,有人送我一本关于宋代诗人刘彝的书,刘彝是福州闽县人,他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可见古代除了讲文人的德与学,最终目的还是要措之天下、润泽斯民,即所谓的“经世致用”。至于《中庸》所言“尊德性而道问学”,倒更像是为了“经世”而做的酝酿与个人修习,只是现在想“经世”的人,连这种准备工作都不做了。没有德与学为基础,其言其行日益鄙陋,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诗人:大学在很多人眼中,是象牙塔,会比较清高和自尊,可事实好像也未必如此。这些年高校爆出的诸多事象,都和大家的想象大相径庭。为此,我能够理解您的隐忧,也许您看到了根本,人如果溃败了,显现在外面的言与事就是虚伪的、令人失望的。我个人成为大学老师之后的这些年,也遇到很多感觉沮丧的事情,写作和做事的热情经常被一些无聊之事耗尽,这与我当年作为学生时对大学老师生活的想象完全不同。想问一下谢老师您对当前高校生态的看法。
谢有顺:我当然能理解一个大学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压力,但无论处境如何艰难,我们读了一堆书,仰视过一堆先贤,总归还是要有一点读书人的骄傲和自尊吧?有些话是绝对不能说,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即便有再大的利益诱惑在前头,也不能失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你想要什么荣誉,可以努力,可以争取,这没什么,但在学术形象的建构上,总还是要让人看到你的精神和追求吧?包括现在很多学者聚在一起,没有多少观点交流,更缺少学术争鸣,所谈论的话题,基本上都是谁拿了什么项目,谁评上了奖,谁又在权威刊物上发文了。在一些人眼里,学问除了这些,没有别的。
我在学术界算是无能者,常常无法参与这样的话题讨论。但我年龄渐大,多了很多宽容,看到学者们妥协于世俗规则,心里是理解的,只是觉得一些人以此为夸耀就没有必要了。君子不器。鲁迅说,“从来如此,便对么?”古人也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富贵时该如何行事,患难时该如何说话,心里都要有准则的,不能乱来。尤其是写文章,白纸黑字,留存在纸上之后,你想刮都刮不掉了,能乱写么?这话我是对自己说的,旨在不断地提醒自己,以免失了基本的警觉。
唐诗人:这种约束和自省,极其重要。我读您的文章,感触最深的正是这种为人的清醒和为文的警醒。人很容易被潮流卷着走,也很容易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当然,我们身处其中,常常也不能免俗。您对自己有高要求,对我们作为学生的“俗”却又能包容体谅。这我想起您以前的文章,曾引用梁漱溟的一段话:“我对人类生命有了解,觉得实在可悲悯,可同情,所以对人的过错,口里虽然责备,而心里责备的意思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对别人可以原谅,对自己终究还是要有更高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可以走得更远。这种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尤其现在我也指导学生,就经常拿这话来提醒自己。
谢有顺:最近我倒是经常想起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里的话,他说:“如果没有什么向我呈现,如果我不热爱,如果存在着的东西不因我热爱而向我展开,如果我不在存在的东西里完成我自身,那么我就终于只落得是一个像一切物质材料那样可以消逝的实存。”确实,对于那些我们所读到、所向往的精神和价值,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热爱,并力图在这种热爱中完成自我,假如人生不与这些更长久的“存在”结盟,就只是一堆稍纵即逝的“物质材料”而已。
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看明这个真相之后,你就会放平心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反思能让一个人快乐,它意味着你洞悉了另一种真相。活在幻觉里,或者端着一种姿态活着,都是很累的,必须提醒自己,你没有那么重要,你写的文字也没有那么重要,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我带学生很多年了,但我一直和学生说,你们一毕业,大家就是亦师亦友了,我没能力做你们一辈子的老师。我深感教师这门职业,或许可以解些惑,传道已几无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数人,不过是在做份工作而已,“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但老师做久了,学生多了,学生出息了,各种人环绕在你身边,不警醒的话,老师也会飘的。还是鲁迅说得好:“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
唐诗人:其实,您的自省与觉悟,一直是作为一种“师道”影响着我们。高校之外,文学界也是各种喧嚣,沉潜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少。如果大家都能多一些这种自省和反思就好了,至少能让写作纯粹一些。
谢有顺:文学的价值语境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而真正要警惕的是,大家正在习惯这种改变。我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少有名的作家,会突然改变自己的写作趣味和写作风格,去迎合市场、读者或奖项,还有些作家把获奖当作写作的终极目标,这是令人费解的。作家如果没有了孤傲和自尊作为精神底色,那他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作家吗?作家要反思,我们文学批评家也要反思。不能光在那里空谈作品,还是要重新引入人品、人格、价值信念等观察维度,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今天的中国文学。
唐诗人:感觉现在无论名家还是刚出道的青年,有些人什么都想得到,常常突破底线。重新引入人品、人格,似乎也很无力,倘若没有信念,就剩下无孔不入的利益。
谢有顺:就我们今天的写作水平而言,我觉得多数作家、学者得到的东西都太多了。包括我自己。我们并没有写出什么惊世之作,但动静却不小,各种扶持、各种奖励,一鱼多吃,志得意满。愿意为写作、为学问受苦的人很少了,甚至连这种受苦的心志都几乎没有了。我很多年都不敢报项目、报奖了,出本书都不敢在朋友圈里转别人评论我的文章,更别说自己去组织宣传、约写文章了,总觉得就我那些无足轻重的文字,得到的已经太多了。这是真话。我一直记得孟子的一句话,“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外面的名声超过了自己的才德,是令人羞耻的事情。你的才学如果不枯竭,进一日有进一日的欢喜,像水从源泉里日夜不停地流出,它把低凹不平的地方填满之后,就会继续流向大海。而靠下暴雨灌满的大小沟渠,因为没有活水源泉,很快就会枯竭的。这是孟子的比喻,道理浅显却是至理。
唐诗人:道理浅显,实践却难。很多人觉得不去争,不去宣传,不去做流量,就会被淹没,就必然失败。
谢有顺:所以要学会接受失败,学会在失败的时候还有笑容。人生总是有两个方面的,有欢乐与悲痛。尼采要求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欢笑。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仅在欢乐时能发笑,在失败、痛苦时,在面对悲剧时也能发笑,才是具备了酒神精神。写作者还是要有一点酒神精神的。海明威也说,“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但现在很多作家、学者好像都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看得太重了,稍有失落就笑不起来了,而我们真正要思考的一个严肃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再笑?为什么不再思考?其实就是表明我们的精神日益萎缩、内心没有力量了。
唐诗人:可也有人会说,他失败了、受了委屈,还笑得起来么?
谢有顺:那也应该笑起来,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么,我积我的德,他造他的孽。不要被一种不好的风习所劫持,还是要相信善的力量。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钱穆曾说,善是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我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说法。中国过去的学术,无非是心学与史学两大类,都是向“善”之学,没有那些善言善行,我们在典籍里所读到的中国和中国人就是另一种模样了。
唐诗人:您试图以人来重新立论,重提人的主体构造,并以人格、生命为尺度来判断一种写作和研究的未来,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一种认知。需要重新来思考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文学的尊严是什么这些古老的话题。我很感谢您这样的提醒,不然很容易随波逐流,失了本心。
谢有顺:之所以聊及这个话题,从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写作的现状,并观察世界的变化,就在于今天出现的问题,在我看来都是人的问题。人这个主体失去了精神光辉,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文化创造?漠视人格的力量,就会以为写作和研究不过是聪明人的游戏,其实不是的。小聪明不过玩一时,有重量的灵魂才能走得远。我想起多年前读王元化和林毓生的通信,当他们谈到关于文化的衰败和人的精神素质下降,我就认同了他们的感叹:“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别看文学话题迭出,写作花样翻新,热闹是很热闹,但真正令人敬佩的人格却越来越少。
今天看一个作家的成就,以小说家为例,主要还是看这个作家是否塑造了能被人记住、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所有的技巧、所有的精神关怀,都要凝聚在人物身上,才能把一种写作落实,并让一种精神站立起来。人是一切艺术和学术的灵魂。如果到处都是卑琐、逐利、斤斤计较的灵魂,哪里会有什么好的文学、好的学术?要改变文学生态、学术生态,首先要改变人的精神生态。与之相比,一些写作技巧的争论,一些学术材料的辨析,其实都是小节,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重要。在我看来,今天的文化界,再去寻求细枝末节的小变化已经意思不大了,写作变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道德勇气的确立和理想信念的重铸,写作的最终成果是创造人格、更新生命。有必要重申,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