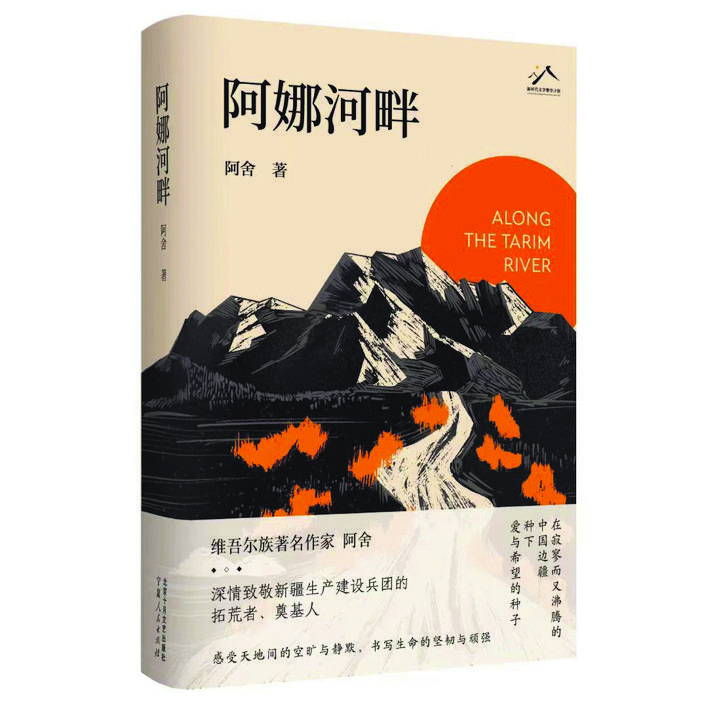在阿舍的小说《阿娜河畔》中,明双全一家见证了茂盛农场的变迁。他的到来和离开,主导着一个家族的落地、率领一群人的扎根。明家是山东移民,阿娜河畔即将见证一项由外来者协同成就的伟大事业。小说细述明家三代人以不同方式参与戈壁建设的过程,明双全务农、明中启任教、石昭美行医、明千安经商、明珠学农、明丽从业财经。阿舍以明家为基点,从农商医教等多层面呈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史。小说中的明双全和明珠形成呼应,喻示着农垦人从土地出发又回归土地的命运。
塔里木河是阿娜河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阿娜的维吾尔语含义是母亲,它迎接四面八方的青年人汇集新疆屯垦戍边。他们保留自身携带的地方文化,一方面追求个体自身的理想,一方推动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小说《阿娜河畔》有两个亮点。一是表达了农垦人与时代始终同步。建设者明知外面世界的精彩,却从不自怨自艾,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主动追踪最新的技术、最好的教育、最优的经营理念,石昭美自学成为一名医生,明中启主持一次次教改,明双全认同被新人取代。因此,茂盛农场有条件有准备地应对危机和把握机遇。二是作品妥当地处理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生动刻画湖南人、山东人、上海人、四川人、新疆人,如何逐步转化为拥有一个共同身份,即兵团人、农场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造出新质文化,它既是地域文化的集合,又是中华文化的合力,阿舍打造出中国故事的新典型,在当代文学里,阿娜河畔的兵团岁月成为独特的文学经验。
小说从现实与日常两端回溯历史,将传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写作从宏大创业史中卸力,转而深耕质朴的情感书写。作者记录三批“生产大军”分别从外来户变为本地人的过程,见证戈壁的日新月异。明中启,明家唯一没有在阿娜河畔出生的孩子,却成为最坚定的农场守护者,他从父辈经历中明白人生奥义,“命运就是时间、风、尘暴和四季,命运没有公平不公平和对错,也没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命运就是自然本身”。茂盛农场被夺走又回归,具体到知识、爱情、家庭、事业,所有人的得失是平衡的。以成信秀为例,她申请援疆,是初代知识分子代表,先后遭遇失家、断臂、丧夫,屡陷绝境也屡获劳动者无私帮扶。
很多长篇小说采取迂回策略描写爱情,而这部作品直接写“我爱”。明家是主线,石家是其重要支线,石昭美处于两个家族的连接点。明中启、石昭美、楼文君与成信秀、石永青、许寅然,两组情感故事联动且形成对比,共同诠释爱情、信仰和责任,尤其是明中启与楼文君,后者两次婚姻都刻意绕开对其一心一意的中启,皆情定上海同乡。小说没有武断地从薄情趋利的道德判断定性其选择,相反表达了对其行为的理解和尊重。应该说,这段爱情是作品里份量特别重的部分,它需要调度明家和石家,介入明中启的个人成长,刺穿石昭美的婚姻,更是折射一代上海知青的命运。“一个人不必非得热爱自己的故乡,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与前程,明中启当然清楚其中复杂的情感因素,以及掺杂的现实利益。”来来回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明中启从不责怪楼文君,他确对后者的屡次舍弃感到失落,然而坚守纯粹的爱已成其信念。小说揭示了另一重秘而不宣的真相。明中启尝试以知识去弥合自己与“知识青年”的距离,虽始终求知上进,但实际师承自母亲李秀琴与老师尤汪洋,他所接受的传统与现代教育是民间的、个人的、碎片的,眼界被限定于区域化(农场化)。基于历史语境和情境,“上海知青”的核心并不落于“知识”,而在其背后的环境与阶层,楼文君对“茂盛”没有归属感,“落地”初始,管一歌失踪事件就加深其对农场日子的疑虑,获得小学教职后,她事实上脱离了农垦生活。明中启一直在忽略她与土地的根本断裂,情动指向行动,上海左右着文君的情感,城市磁场消解着其爱情内驱力,因此中启一切的真情挽留必然是无效的。明中启的爱,只能在戈壁蓬勃生长,移植至城市会遭遇水土不服。如果一同回沪,楼文君的前路尚且一片茫然,何况明中启呢?
三百平方公里的农场,接纳他乡客且扶植本土新人。小说强化对戈壁教育的描写,它以一所学校、三位老师、一群孩子,聚焦基础教育,塑造明中启这一乡村教师典型,作品强调教育普及是新疆建设中的宝贵财富。1957年,只有14个娃娃的茂盛农场子弟小学成立。历任教师尤汪洋、明中启、楼文君,及编外人士李秀琴,都竭力为孩子们创设改变命运的条件。“真正的老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和讲解能力,还要有非同一般的耐心和奉献精神,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还要关怀他们的心灵。”尤汪洋的话,成为明中启一生的工作指南。由农场培养的“头茬娃娃”,在明知城市机遇更好的情况下,依然留在这里。
阿舍精准描绘故乡的30年之变。她并非将务实进行概念化悬置,而是扎实写下创业的步骤、举措和细节。改革线贯通文本,农垦人拥有不容置疑的赤诚,有时有效,有时莽撞,但他们永远保持主动出击。创建者明双全的梦想即为集体心声,“到处都是绿油油金灿灿的庄稼地,果园里的果实压弯了枝头,一筐筐的水果甜得当蜜吃,瓜田里的哈密瓜、西瓜不要钱分给职工,牛奶当水喝,食堂里天天磨豆腐、炸油条、宰猪烹鱼,灰土掩盖脚的马路上铺上沥青,又平又直,黑油油的,一直伸向戈壁滩的尽头……”改革创新彰显着三代人的实干精神,茂盛农场的发展不是改革和奋斗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的集力共建。
文字令新疆遥远的过去苏醒,也同时催动了蛰伏于阿娜河畔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这既是久违的人民创业史,又是新时代的一次创作攀登。即使农场面临整体搬迁,可茂盛只是个名字,农场是永恒故乡,不管它如何变化,都“像从前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会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上海/新疆、城市/乡村、旧人/新人的差异横亘在建设者之间,但农场从未排斥过谁,反倒是人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对其亲近或疏离。它以最原始的形态和最朴拙的情感向世界及人敞开,消化时代错误、人生厄运、自然惩罚。小说基本调性是求真向善,摆脱困厄循环,兵团人的传统是习惯为陌生人悲伤,而一再吞食自己的悲伤。阿舍虽设置了1957、1967、1977三个记忆旋钮,但她拧开的那一刻是悄无声息的,阅读未被节点打断,由时间之流驱动着径直向前。明中启对妻子石昭美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急着朝前赶,但是,也总是会有留下来守护一方天地的人。”阿舍用这部作品守护阿娜河畔的历史与文化,更重要的是守护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曾飞扬于此的无怨无悔的青春梦。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