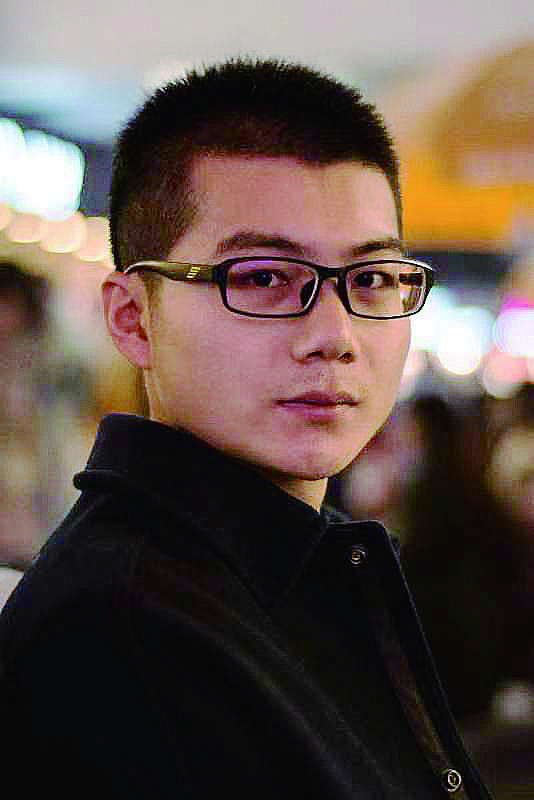成都的夜最先是从低洼处洇散的。趴在川西雪原上的霞光突然转身,一小坨黑猛地朝盆地底部砸了下去,不等有所反应,迅速炸裂开来,黏稠的暗影先于昏黄的灯柱攫住四处突奔的道路,继而一寸寸爬上玻璃幕墙,把夜挂上城市的末梢。这样的夜,生硬、凛冽,绝无故乡那般绵密熨帖。
当再次谈及故乡这座废置已久的矿藏时,底楼食客们的嘈杂声响正从咕咚冒泡的汤锅中溢出,叫嚷声切入耳郭,棱角分明,伴随车轮疾驰的唰唰声、货运专线沉闷的呜咽声、酒鬼们含混的谩骂声。有那么瞬间,我切实感觉到自己被一团灯影牢牢钉在墙壁上,思绪在光晕里晃荡;而书桌咫尺见方,静谧处布满折痕,从平面到立体,从单调到潦草凌乱,记忆的线头锁住黑夜脖颈,仿佛被囚进一座固体的苍穹。一扇窗兀自打开,所有声嚣悬空飘浮着。
乡村的黑夜史料般记载着大大小小诸多事宜,而乡村葬礼则完整刻录了寂静的形状、色泽和气味。外祖母出殡前,我曾做过一名守夜人。凌晨4点,阴阳师的锣鼓镲钹和喋喋不休的诵经声提醒着我这一事实,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熬了两个通宵,尽管那些喑哑的哭泣早已佐证不了新鲜的感情,尽管内心一盘散沙,我仍要跪立于棺木前,让我黑暗中的整体主义悲伤适应于局部的麻木。我不知如何松绑嘴里发涩的字词,它们被焊接得异常牢固,仿佛置身于自我中心,在穿堂风的吹拂下会像水流一样波动、战栗,甚至于那些锣鼓声和诵经声也是寂静的,唯一哽咽的事物似乎只剩下三对孜孜不倦的白烛、一对袅袅升起的佛香。
随着阴阳师有气无力的唱腔,不时往火盆里扔纸钱的我也是寂静的。瞬间引燃的纸张被气流的浮力烘托着昂扬向上,脱离束缚后,就连那些向死而生的灰烬也是寂静的。仿若一组慢镜头,飘扬的纸屑被火苗捉住,从一团团阴影退缩成一丝丝尘坌,再到一缕缕游丝,终究朝着无人认领的地带悠悠荡荡晃去。暗夜隐瞒了我们的不知所措,减弱了我们的慌乱与不安。
两个舅舅面无表情地窝进劣质沙发里,用与白天判若两人的僵硬表情点燃香烟,任由烟灰一截截有气无力地垂下身子。真让人死气沉沉!我仍旧跪在蒲团凹陷处,拳头大的坑刚好容下我酸软发麻的膝盖。院外隐隐传来猫头鹰短促的哀号,黑黢黢的夜色掩映着冷峻的青山,袭人的寒意拖着长长的魅影,种种境况都迫使我将手中的纸钱扔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更快一点,只有那样,我才能切实地感觉到温暖,一种炙热的疼痛,像刀片划破指尖。
作为夜色的一部分,棺盖上的外祖母散发着一股淡薄的艾草味,像经过一段荒废的歧途,脚上沾满了露珠和植物汁液。我凝望着那条分叉的小径,静谧被无限延伸,通往黝黑的隧道,一种铁钳般的钝力紧紧箍住我。“光消失之后,恐惧和迷信在不同程度上侵入了我们。我们被那诡异的黑暗所包围,而黑暗本身早已与我们内心深处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可预见的,这种中断和破坏还是如此令人不安”(《古人之夜:古代世界的夜间生活考》)。恐惧源于衰亡的不确定性,意识到这一点,我毅然推开被黄表纸密封的柴房,在手电筒的引领中抬起头,环视这间堆满农具与烟尘的小屋。松木横梁上的麻绳已被斩断,一把短柄木斧歪歪斜斜地钉在横梁正中,时间的标尺精准、深刻地丈量着她的一生。
母亲曾向我描述过这一梦境:外祖母侧躺在一张太师椅里,微闭着眼,发出细细的鼾声。母亲小心翼翼地喊她,晃动椅子,没有回应,试图拉起她的手,却发现原本富态丰盈的外祖母竟如泄了气的气球,只剩一张皱巴巴的皮。说这话时,母亲正手持火钳,在火盆里百无聊赖地翻找着,笃定外祖母是想通过梦境向她传达些什么。
葬礼结束后,为避免睹物思人,外祖父重新在堂屋支起一只半米见方的铁皮炉,那间用来生火取暖的柴房,自此便被闲置了。空空荡荡的堂屋,空空荡荡的孤寂,投喂再多柴火也不能把大面积的寒冷养熟。多数时候,外祖父只能一个人温温吞吞地烘烤着干巴巴的自己,以及无尽绵延的时间。
长夜将尽,阴阳师叮嘱我点燃院坝里那堆码放整齐的柴垛。此时星辰尚未被夜空擦拭干净,远远望去,一盆将熄的炭火掩埋着几粒灰蒙蒙的火星。不知道天上的火种,是否能引燃人间的遗物?朦胧冷清的乡野中,裂帛般的狗吠最先勘察到空气中细微的波动,浸满水气的槐木显然被这突然而至的声嚣怔住了,驱使着浓烟往堂屋逃窜。舅舅提起一桶汽油猛地泼了下去,扭捏的火光受到惊吓,顿时蹿出一条一人多高的火舌,一并发出脆烈的噼啪声响。那是篝火在挣扎,在炸裂,在呼救,黑白世界渐变成了暖色,一个巨大的夜的窟窿亟待形成。而我的外祖母就如残瓦碎砾,躺在那一团氤氲的雾霭中,躺在那一圈圈萦绕的经文密语中,她身体里丢失的成分太多了,为了从自我角色中脱身而出。肥硕的衣物将她装点得越发庄重,像是正在进行一场杀青仪式的谢幕演员。那时祷词已近乎呓语,我们追随着阴阳师,阴阳师围绕着篝火,篝火固执地冲天直上,映照着我们酡红的脸颊。
这并非我第一次在冬夜送别亲人。乡野传闻中,熬过寒冬的老人便可以再吃一年人间饭,于是冬天便成为分水岭。他们用属相冲克来淘洗谶言,用猫头鹰的叫声趋避利害,用老鸹的啼哭占卜命运递来的暗语,面对病痛折磨却显得异常隐忍克制;他们说服自己囤积苦难、折磨和一切与己为敌的事物,相信苦行僧般的虔诚里自有一座迷人深渊;他们掰着指头计算同病相怜的亲朋故友,以此作为肉身参照,在困顿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僵持。他们是我的亲人,也是我日渐执拗、坚硬、顽固的组成部分,代我在文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两点间划拉出一根最短的直线。我不断地游走在这根钢丝上,那些消逝的脸庞始终折射着碎片化的刺眼光芒,提醒我不要后退,服从脚下的路。
有段时间我疯狂迷恋骑着摩托在夜间漫游,我熟知村道的走势,就像熟知山坡上的每一处坟茔。村庄不会消亡,黑暗不会永恒,守夜人戴着他的面具,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时扬起一张瘦削的脸庞,大把大把的风擦亮了他填满眼角的光晕,只要继续向前,他就能看见新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