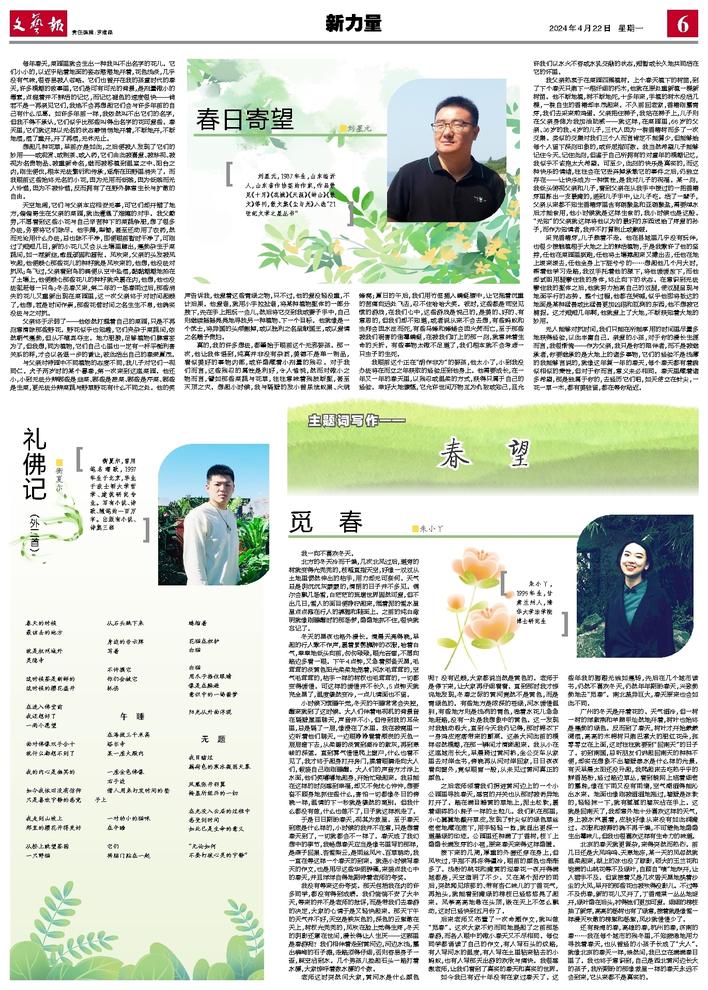我一向不喜欢冬天。
北方的冬天冷而干燥,几次北风过后,道旁的树就变得光秃秃的,枝桠直指天空,好像一双双从土地里愤然伸出的枯手,用力却无可奈何。天气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清朗的日子并不多见。偶尔会飘几场雪,白茫茫的琉璃世界固然可爱,但不出几日,雪人的面目便狰狞起来,混着泥的雪水星星点点溅在行人的裤脚和鞋面上。之前的纯白澈明就像刚睡醒时的那场梦,隐隐地抓不住,很快就忘记了。
冬天的黑夜也格外漫长。清晨天亮得晚,早起的行人默不作声,裹着累赘臃肿的衣服,哈着白气,窣窣地低头向前,匆匆碌碌,眼光吝啬,不愿向路边多看一眼。下午4点钟,又急着预备天黑,毛茸茸的淡黄色阳光柔柔地笼着,河水毛茸茸的,空气毛茸茸的,枯手一样的树杈也毛茸茸的,一切都变得缓慢。可这样的缓慢并不长久,5点钟天就完全黑了,温度骤然变冷,一点儿情面也不留。
小时候习惯睡午觉,冬天的午睡常常会失控,醒来就到了这时候。大人们伴着电视机的背景音在隔壁屋里聊天,声音并不小,但传到我的耳朵里,总是隔了一层,像浸在了水里。我在被窝里一边听着他们聊天,一边眼睁睁看着颓丧的天色一层层暗下去,从柔暖的淡黄到凝冷的紫灰,再到寒峻的深蓝。直到雾气慢慢爬上窗户,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才终于起身打开房门,揉着眼睛走向大人们,假装自己刚刚睡醒。大人们的声音方才浮上水面,他们笑嘻嘻地起身,开始忙碌起来。我总能在这样的时刻感到幸福,却又不免忧心忡忡,想要奋不顾身地抓住些什么,害怕一切都像冬日的傍晚一样,温情的下一秒就是骤然的离别。但我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也做不了,日子就这样流走了。
于是日日期盼春天,视其为救星。至于春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小时候的我并不在意,只是想着春天到了,一切就都会不一样了。春天成了我幻想中的季节,我畅想春天应当是像书里写的那样,是燕子回巢、杏雪梨云,是雨丝风片、百草萌动,我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春天的到来。就连小时候写春天的作文,也是用尽这些华丽辞藻,来装点我心中的春天,并且洋洋自得地期待着老师的夸奖。
我没有等来这份夸奖。那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都没有得到成绩。我们惴惴不安了大半天,等来的并不是老师的批评,而是带我们去春游的决定,大家的心情于是又轻快起来。那天下午的天气并不好,天空是铁灰色的,深色的云絮散在天上,树杈光秃秃的,风吹在脸上觉得生疼,冬天的阴影还罩在世间,漫长得让人生厌——这哪里是春游呢?我们相伴着走到黄河边,河边水浅,露出嶙峋的石子滩,走路须得仔细,否则容易身子一歪,踩空沾到水。几个男孩儿捡起石头一路打着水漂,大家惊呼着数水漂的个数。
老师这时突然问大家,黄河水是什么颜色呢?没有迟疑,大家都说当然是黄色的。老师于是停下来,让大家再仔细看看。直到那时我才惊诧地发现,冬春之际的黄河竟然不是黄色,而是青绿色的。有些地方是浓深的苍绿,河水缓慢温驯,有些地方则是浅冽的青色,卷着水花儿急急地赶路,没有一处是我想象中的黄色。这一发现对我触动极大,直到今天我仍记得,那时棉衣下一身鸡皮疙瘩带来的颤栗。这条大河此前的模样忽然模糊,在那一瞬间才清晰起来。我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早晨跨过黄河桥,坐公交车从家里去对岸念书,傍晚再从河对岸回家,日日夜夜看向窗外,竟似眼盲一般,从未见过黄河真正的颜色。
之后老师领着我们拐进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公园里寻找春天,感官的开关也从那时被奇异地打开了。踏在满目糙黄的草地上,泥土松软,裹着细碎的小珠子一样的土粒儿。我们趴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翻开草皮,发现了针尖似的绿色草丝密密地藏在底下,用手轻轻一捻,就显出更深一道墨绿的印迹。公园里还种满了丁香树,枝丫上隐隐长满发芽的小苞,原来春天来得这样隐匿。
接下来的几周,厚重的外套还穿在身上,但风吹过,手指不再冻得僵冷,眼前的颜色也渐渐多了。浅粉的桃花和嫩黄的迎春花一夜开得满城都是,天空澄明了不少。又在某个泥泞的雨后,突然闻见浓郁的、带有杏仁味儿的丁香花气,再抬头,就能看到嫩绿的柳枝已经悠悠晃了起来。风筝高高地悬在头顶,嵌在天上不怎么飘动,这时已经快到五月份了。
后来老师又布置了一次命题作文,就叫做“觅春”。这次大家不约而同地提起了之前那场春游,而各人眼中的微小春天又不尽相同。每位同学都诵读了自己的作文,有人写石头的纹路,有人写河水的温度,有人写在土里钻来钻去的小蚂蚁,也有人写那天出游的欢欣与痛快。我很感激老师,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春天和真实的世界。
如今我已有近十年没有在家过春天了。这些年我的脚跟无线如蓬转,先后在几个城市读书,仍然不喜欢冬天,仍然年年期盼春天,兴致勃勃地去“觅春”。南北差异巨大,春天原来也会如此不同。
广州的冬天是开着花的。天气湿冷,但一树一树的洋紫荆和羊蹄甲灿然地开着,树叶也始终是蓬勃的绿色。反而到了春天,树叶才开始簌簌凋落,高高的木棉树只剩巴掌大的肥红花朵,孤零零立在上面,这时往往就要到“回南天”的日子了。初到南国,总听朋友们讲起回南天的种种不便,却实在想象不出墙壁渗水是什么样的光景。有天早晨太阳还没升起,我爬起床去吃热乎乎的鲜香肠粉,经过路边草丛,看到蛛网上结着细密的露珠,像在下雨又没有雨滴,空气潮湿得能沁出水来。地面也像刚被湿湿地拖过,墙壁是冰软的,轻轻抹一下,就有腻腻的墙灰沾在手上。这就是回南天了,我却意外地十分喜欢这样的天气,身上被水汽裹着,皮肤好像从来没有如此润嫩过。衣服和被褥的确不再干燥,不可避免地隐隐生出霉味儿,但我也很喜欢这样有生命力的味道。
北京的春天就更复杂,来得突然而热烈。前几日还是大风呜呜、天寒地冻,某一天的风忽然就温柔起来,湖上的冰也没了踪影,硕大的玉兰花和饱满的山桃花等不及绿叶,自顾自“噗”地炸开,让人措手不及。但紧接着又是几次昏天黑地挟着沙尘的大风,早开的那些花也被吹得没影儿。不过等不及伤春,新的花儿又开了,丁香海棠一丛丛地绽开,绿叶隐在后头,衬得她们更加可爱。细细的柳枝抽了新芽,高高的杨树也有了绿意,接着就是像雪一样漫天吹散的柳絮和杨絮,风沙就慢慢少了。
还有珠海的春,高雄的春,杭州的春,济南的春……我在每个城市的残冬里,不知疲倦地用力寻找着春天,也从曾经的小孩子长成了“大人”。就像北京的春天一样,倏然间,我已立在满满春日里了。我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西北黄河边长大的孩子,我所期盼的那像救星一样的春天永远不会到来,它从来都不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