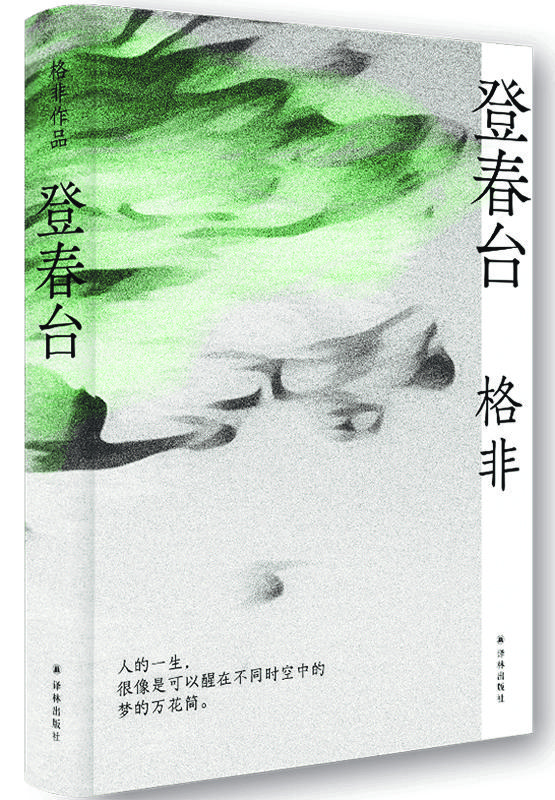□张 宇
格非新作《登春台》,以40余年时代变动为经,以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为纬,借由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生命故事,以素朴、抒情的诗性笔调编织起有关当代人的欲望、情感、关联、命运、生死、时间危机与生存困境的精神图景。惶惑与痛楚、创伤与救赎、自我与他者、自由与道德、存在与命运,这些宏大的哲学命题,都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细致叩问。格非将视线下沉,聚焦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于中开启生命的潜能与本真的意义,通达澄明的存在。
探讨关联、偶然与命运的复杂互动
格非擅长“将一件平常之事极力渲染为神奇命运的微妙暗示”,早年《敌人》等作品中那种似有若无的宿命气息与神秘意味,仍或多或少地盘踞在《登春台》小说文本的上空。在《登春台》中,格非醉心于探讨关联、偶然性、必然性与命运之间的复杂互动,不难看到其中受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影响。在存在主义视角下,个体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强调个体的选择和责任,不受外部必然性的束缚;而在现象学中,偶然性和必然性被视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要素。
在关系哲学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为客体性关系、主体性关系、主体间性关系,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存在于关联之中。小说以诗意的语言、晓畅的故事对于玄奥的关联进行阐发。《登春台》中,来自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城因偶然的联系聚在一起,最终又必然走向了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小说一再提及牛顿的神秘箴言“上帝是关联的声音”,以及洛伦兹的警句“世界上那些看似没有什么瓜葛的事物,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都提示了世界的本质。关联代表了宇宙的绝对运动,世界的必然逻辑,文明发展的轨迹,人类的生命意志。关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是隐藏、掩饰、还是逃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不可避免地与关联迎面相撞。而在“后人类”时代,技术空前入侵人类生活,算法、大数据、监控的幽灵实现了世界万物瞬时互联,任何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都随时能引起太平洋的风暴。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名字有着鲜明的隐喻意味,当它全面投入数字化运营的怀抱,也意味着整个神州都因为科技被联合在一起,成为世界命运中的一环。
尽管世界的运行朝向工具理性不断滑行,偶然性仍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没有偶然性的发酵,也就没有个人命运的奇诡,这便是命运的不可知性。在这一点上,格非与他最欣赏的作家博尔赫斯心意相通。博尔赫斯的《南方》中,主人公因为偶然的擦伤而丢掉了性命,而《登春台》小说里,所有人的命运浮沉,都被千丝万缕的偶然性蛛网系在一起。沈辛夷因母亲勒索式的亲情而与桑钦发生了生死纠缠;陈克明因为一趟雨夜出租,而与周振遐产生交集,并成为公司接班人;姚岑也仅仅是因为来自茯西村,便与蒋承泽、周振遐产生了一生的情感羁绊;蒋承泽一手打造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明夷社读书会,无意将所有人绑定在一起,他成为不在场的幽灵,影响着每个人……冥冥之中有限性的因子,经由偶然性的发酵,不相干的人事被纠缠在一起。在命运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的排列组合中,无限性溢出了理性王国的酒杯。
小说十字路口的回转,奏响人生的乐章
格非曾将小说作家分为文体家和思想家两类,前者以法语作家为标志,如福楼拜、纪德、普鲁斯特、格里耶;后者则以俄语作家、德语作家为代表,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穆齐尔等。如果说格非早年是着意于文体家的努力,在先锋小说浪潮中以“叙事迷宫”打造独特的个人风格,那么,近些年的格非,则有意朝思想家转向,实现小说十字路口的回转。他更加重视简约的力量,如周振遐一般精心修剪文字的花园,舍弃那些怪异、艰涩、枝蔓,塑成美丽的枝丫,朝向雷蒙·卡佛、海明威、博尔赫斯、福克纳,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折中里,用力开掘重回伟大的传统的道路,致力于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直抵本质的真实。
小说放弃了晦涩的叙事迷宫,以简洁、质朴、流畅的故事,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对命运进行追问和沉思,既避免了艰涩难懂,又绕开了平庸乏味,故事为哲思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而哲思赋予了故事深沉的内核。
在《登春台》中,格非再次展现了独特“格非经验”,也即“将视野之阔大和叙事之精微有效结合的经验”。作为学者型作家,格非对于小说的艺术有充分的自觉与审慎的克制。他的作品内容深邃、蕴含深厚、场面宏大,同时也充满了文体上的警觉。叠加态的社会进程,城乡生活的剧烈变动,阶级分化的巨大差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伦理的空前变化……一刻不停、永续变化的狂飙时代不允许人有喘息的机会,而格非以静制动,从细微之处观照时代的磅礴。从“江南三部曲”的大历史到《登春台》的小历史,格非一直保持着对于中国人精神史、思想史、情感史的敏锐观照。
格非酷爱音乐,音乐的抒情性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他醉心于博尔赫斯对于音乐的表述,“只要音乐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意义的”。音乐的幽光狂慧,给他带来了别样的人生体验,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表达。音乐给格非带来了克制的美德,句子长短错落,简约、干净而富于节奏美感,在抒情性的基调中,体察存在的本质。京剧《凤还巢》、评剧《花为媒》等音乐形式频频入文,成为推动叙事进展的重要动力,音乐的意象、歌词、形式、结构等元素都被有机地化用在文本之中,使文本表意变得更加丰厚,实现“跨媒介指涉”。在苏珊·朗格看来,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态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登春台》中,采用了“四声部”音乐结构方式。小说4个章节对应着4种叙事语调、叙事风格与叙事声音。声部的变换,造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四声部交替叙述,多重叙事声音共存互动,4个叙事视角相互补充,强化了故事的张力和叙事力度。四声部多而不杂,共同构成了人生乐章的和声,而这些通通指向一个命题,便是存在。沈辛夷是存在之痛,窦宝庆是存在之罪,陈克明是存在之欲,周振遐是存在之寂。由痛而罪而欲而寂,仿佛构成了人生的循环终章。
在存在与救赎中,实现相互守望
自“江南三部曲”以来,格非不断将视线下沉,不再拘泥于知识分子叙事,而是以同情与悲悯的眼光观照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与早年痴迷于死亡不同,格非如托尔斯泰一般,对普通人的生活倾注了充分的悲悯与尊重。他深知处在生存困境中的普通人,也正是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当他下笔时,倾注了无限深情。格非不动声色地呈现生活的残酷逻辑,而当审判的闸门开启,他又寄予一丝温暖和慰安,借助孤独与死亡的母题,探索人的存在与救赎。
雷蒙·威廉斯曾指出,孤绝的个体是高度密集的社会性网络的产物。小说也借此反思了关联带来的困境。格非自言,“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出于这种好静的心绪,格非难掩对麦尔维尔、穆齐尔、志贺直哉等人的偏爱。他们笔下的巴特比、乌尔里希、时任谦作,都是典型的拒世遁世、内心孤绝的“巴特比主义”者。在《登春台》中,同样有许多“巴特比主义”者。他们为社会性所困扰,被折磨得不堪,人与人之间过于繁杂的联系,成了他们痛苦的根源。桑钦有一种梭罗式的“寂静的绝望”,窦宝庆在杀人的罪恶之中陷入沉默的深渊。沈辛夷被性侵后,对于声音怀有普鲁斯特式的神经过敏。同样的,周振遐也长久地被邻居的噪音搅扰得痛不欲生,“稠密的人际关系”让他窒息,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群,让他厌恶。他毕生所要追求的,不过是“重新融入自然的心灵平静”。对于人群的厌弃,是他们的共通情绪。他们致力于在令人厌憎的现实世界之中,开拓一块飞地,实现“消极自由”。在“灵魂将尽”的时代,他们渴望以“隐世”的本能冲动,作为“自我保护”的策略,正如《老子》第二十章所言,“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对于内面的人来说,孤独能够建立一种真正的联系,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起一种马丁·布伯意义上的“我—你”的亲密关联。“我—你”关系存在于人与万物的关系中,它是深层次的、完整的、全面的、有爱的联系。尽管命运多舛,小说的最后,4个主人公有和解、有期望、有温柔、有坚守,他们重建了与世界的关联。
如果说遁世是无奈的逃离之路,那么直面死亡则是众人的解脱之途。书中的主人公们,都与死神打过照面。桑钦之死让沈辛夷陷入重度抑郁,姐姐之死让窦宝庆背负起复仇逃亡的宿命,蒋承泽之死让周振遐直面世界的复杂性,而周振遐的病重,则将所有人紧密围拢,让他们重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肉体消失的担忧,生命的无意义的焦虑如帘幕一般,遮蔽了现代人的心性,而去蔽,则成为通达澄明的存在之境的必经之路。正如纳博科夫所言,人的存在只是两团永恒黑暗之间,一道短暂的光隙。在这光隙之中,正是审查生命意义的契机。
当生命本身成了某种无根的虚浮之物,死亡的提前到来,为人生提供了出神的片刻,也成为他们思考、反省、探寻生命意义的真正开端。只有凝视死亡的深渊,才能将生命重新理解为一种“潜能”、一种“觉悟”、一种“开启”。“生命的最终完成,需要有一种觉悟。”小说中,周振遐以“沉默的劳作”来完成自我的救赎,花园中盛放的欧洲月季,光华灿烂,热烈秾丽,映照出生命的空旷,也温暖了他骨子里的冷寂。明亮而清澈的“现在”,允许他在场。这样的吉瞬,有如神启,人间的扰攘、在世的忧虑,徒劳的挣扎,都显得卑琐无聊,至此,周振遐可以在纯粹的意识中,把握自为的存在。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周振遐无惧死亡,接纳了生命中的伟大必然与最终归宿。
《登春台》聚焦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剧烈变动,从关联、偶然、命运入手,借助于素朴精妙的诗性叙事,打捞“浮泛无根的时代”的凡俗生活,探求存在、救赎的可能。格非以其独特的宏大与幽微,抵达了生命的澄明之境。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