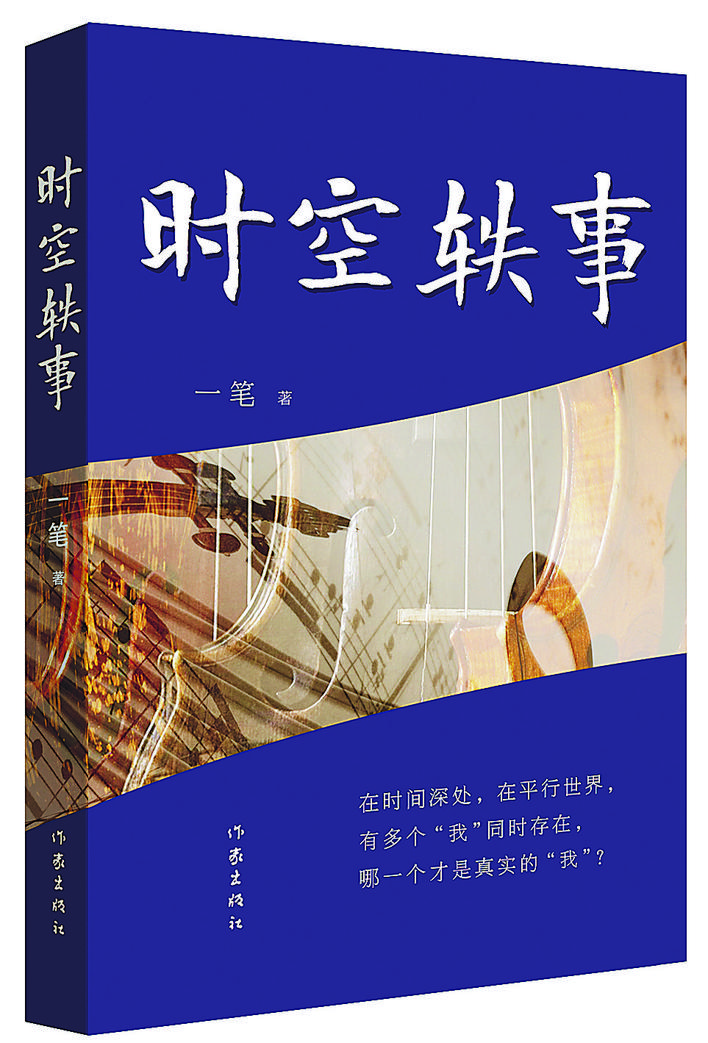□石华鹏
长篇小说《时空轶事》在开篇出现的一个意象让我印象深刻,它仿佛是引导我们走进和理解这部小说的一道光亮,或者一把钥匙。
“我把目光扫向一排又一排晾晒的白被单,看见一簇春光在上面不停地晃动。忽地,我在一张被单上看见,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那一簇碎碎的春光淬溅在我涌出的泪水里,光斑扩大,欧阳兰消失了”。
——春日晴朗的一天,在被当地人称为“疯人院”的海舟医院的晒台上,“我”和她面对面坐在一张石桌旁,周围挂满了晾晒的白色被单。“我们”聊天时,出现了以上这一个场景。
那簇“不停地晃动的春光”,犹如一个巨大的隐喻和象征,为整部小说定下了时空交错、叙事迷幻、人生似梦的艺术基调。白被单上晃动的春光,让我们想起电影银幕,以及银幕上虚幻与真实交织的光影故事。事实上也是如此,小说中,白被单上出现的注视“我”的一双眼睛和在光斑中消失的欧阳兰,暗示了那是另一个“我”。“我和她面对面坐在一张石桌旁”,实则是“我”和“我”面对面而坐,50岁的住在海舟“疯人院”的欧阳兰与9岁的来自川北362基地的欧阳兰面对面而坐。她们聊天,并发现一个秘密:“我看到了从前的我。是看到,不是想起。因为那个我还在那里。”
在那簇晃动的春光里,在时间的深处,有多个平行世界共存,有多个“我”同时存在着,她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这是《时空轶事》深层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对认识自我的一次复杂诘问。在对自我确认的游移不定中,小说的另一个诘问或者题旨随之而来:生活究竟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还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抑或是我们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当然,这不是穿越情节,也不是魔幻叙事。《时空轶事》是一部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果要给这种现实主义冠上名称的话,不妨称之为“轻逸现实主义”。说它“轻逸”,是因为其在叙事和题旨上所表现出的轻逸之感。小说叙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随主人公情绪和记忆的变化,在多重空间和时间中灵动切换,摆脱了叙事的繁复和冗长,直接与人物的精神世界勾连。另外,小说对自我与他我、记忆与存在等问题的探讨,是通过个案和感性的生活来完成,让深刻的心理问题探索有了一种灵动和确证之感。
围绕主人公欧阳兰,小说写了三个空间里的故事。其一,“走进红砖楼”,讲述欧阳兰少年时读书和成长的故事。欧阳兰随知识分子父母在川北大山深处的362基地(满足战备需求的能源试验场和后处理工程)生活,尽管物质匮乏,但常有小愿望得以满足的快乐。她结识了一生的好友许冬梅、周卫等,认识了敬业的草帽书记、邻居叔叔等人,也见识了家暴邻居和“女流氓”等。同时,处于成长期的少女欧阳兰身上,也浸染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如爱憎分明、道德洁癖、革命激情、善良纯粹等。其二,“风卷研究院”,这个故事开始时,欧阳兰已人到中年。她大学毕业后回到父母的家乡海舟,在江南应用物理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院长赵辉被“双规”,继而进了监狱,欧阳兰的精神也陷入“不可名状的焦虑”之中,“常常坠入虚无里,感觉自己一点点与时空脱节。我的内心一片空荡”。“我”的研究能力强,成了副院长,但在各种人事纠葛中,“我”的人生却陷入了某种绝望和无意义中。其三,“迷幻‘疯人院’”。过度的焦虑和绝望,以及院士丈夫出轨学生的谣言,让“我”住进了“疯人院”,“在这里住久了,我常常有种恍惚迷离的感觉,在那个未知的平行世界里,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和事,都在这里不断被并置发生,不断被重新上演”。住在医院的治疗过程依然是自我疗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迷幻”的,去见到过去的“我”,去与记忆中的那些人“告别”,然后找到“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的答案,找到“生活究竟是活过的日子还是记忆中重现的日子”的答案。
三个故事,也是三个隐喻:物质贫乏的纯净时代,物质丰富的倦怠时代,以及精神困顿的自我疗愈时代。第一个故事的叙事清晰、舒缓,细节丰富,充满温情;第二个故事的叙事跳跃,节奏加快,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温情消失,焦躁的情绪弥漫在叙事中;第三个故事的叙事混乱,人事来回挪移,清晰度消失,带有了“迷幻”色彩。所有的叙事情态和风格特点都是人物精神世界的写照,三种叙事风格塑造着欧阳兰的心灵成长史和变迁史。
“哪一个是真正的我?”“生活是我活过的日子还是记忆中重现的日子?”欧阳兰之所以发出灵魂深处的自我诘问,是因为她迷失了自我,在匆忙的、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中失去了意义,而自我诘问无疑是寻找和疗愈的方式之一。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的“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导致了一种过度疲劳和倦怠”,“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这一精神状态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质。韩炳哲对这种倦怠社会的病症开出的药方是,“人们应该对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闲冥想的成分”。无疑,自我诘问构成了“悠闲冥想”的重要部分。欧阳兰的自我诘问遍布“风卷研究院”和“迷幻‘疯人院’”两个部分的叙事中,尽管小说家给了我们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但答案是有的:那个纯净时代的“我”才是真正的“我”,那个时代中的“奉献者”草帽书记和“好人”邻居叔叔以及有成就的研究者“父亲”等等一批人,“他们总是重现在我的记忆里”,这才是“我”所珍惜和敬重的精神。
《时空轶事》是一部有着突出艺术想法的小说,它试图融合物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来进行叙事。三个故事开始之前都有一个简短的“引言”,“引言”涉及物理学和精神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有关人的幻想空间、宇宙中的平行世界、生活经历与记忆的复杂关系、第四维度的“命运之眼”,等等,这些知识并非突兀地“显示”,而是主人公欧阳兰——一位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研究员——对自己人生遭遇和命运的一种理论上的解释。这些知识既为小说的叙事想象力提供了合理性,也为欧阳兰的认识自我提供了学理上的解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时空轶事》在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上做到了紧密结合,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作了较为深入的勘探,尤其对倦怠社会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作了一种病理学上的呈现和阐释。
“见到你比我想象得还要好,你走出了焦虑的日子,非常好。”小说最后,过去的好友雯雯对欧阳兰说。“醒来时,我已经睡在海舟市理工大学我家里的床上,此刻是北京时间上午7∶02。阳光透过窗帘急不可耐倾泻进来……”
“那簇晃动的春光”变成了“倾泻进来的阳光”,一切似乎变得美好起来了。
(作者系《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