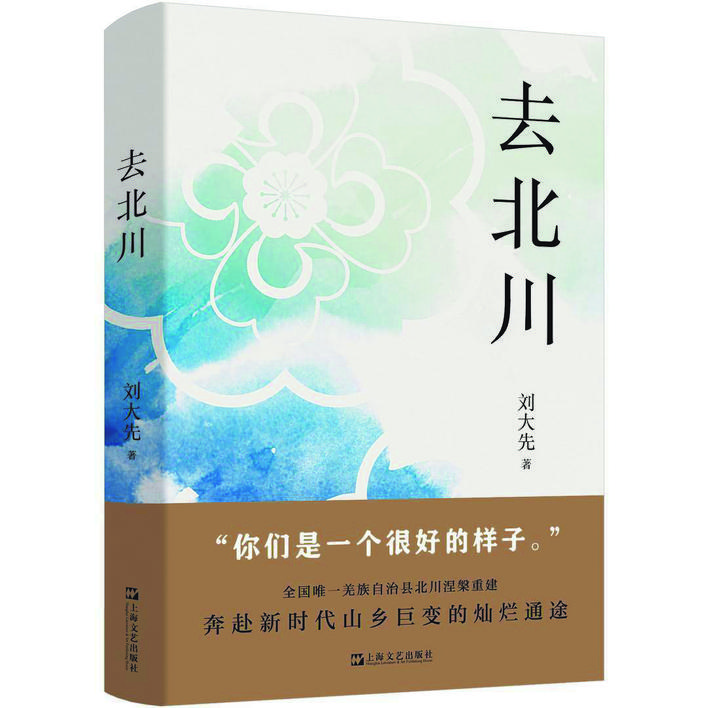初读大先《去北川》的序言,他说:“长期以来,北川似乎像无数县城一样默默无闻,直到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几个关键性的事件。2003年成立羌族自治县,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受灾,2018年7月31日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2月21日根据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进入到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途中。正是在此期间,我从北京来到了北川,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的讲述方式和他在北川的工作内容(比如他要打造一台实景禹羌文化演出、加大《少年禹传奇》城市超级IP应用和推广力度、办好《走北川》大型实体体验剧等),让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事,更是文字背后站立的那个人——这个人就是古代士阶层兼善天下情怀在当代知识分子的回响。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刘大先写作《去北川》的方法。可以说,他是用了一种不那么彻底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这毕竟不是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但这个方法使《去北川》与我们常见的“新山乡巨变”写作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人类学由于学科性质的规定性,它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位与客位研究、小传统与大传统研究等,应该说,这些方法在《去北川》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应用。作品开篇就是羌族古歌《尼萨》,在这个古歌里,我们发现,古代羌族是一个有敬畏的民族,人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人是由神管着,这一点非常重要。李泽厚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20世纪80年代一个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李泽厚未必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要害。他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说他是信神呢,有时候又不信,说他不信神呢,有时候又信。还是孔老夫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时候也就不想了,所以墨子说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对文学创作来说,对人的评价过高,是现代以来的事情。我们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定胜天,人是不可战胜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人的膨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现代工业化的急剧发展,人的贪婪欲望几乎难以遏制。人对自身过高的估计,使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终于自食了恶果。因此,当我们强调“文学是人学”的时候,首先要强调人的有限性,强调人失去敬畏之心是多么的可怕。
《去北川》的特别,我想大概有这样几点:首先是作者的亲历性。刘大先曾挂职北川副县长,分管文旅工作。工作性质使大先对北川的情况有了细致的了解。他的工作就是他田野调查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对文化人类学知识有专业训练的学者,他敏锐捕捉了羌族古歌《尼萨》、羌族英雄史诗《泽基格布》、羌族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羌族史诗《羌戈大战》、羌族民间故事《大禹王》《北川民歌》、羌族开咂酒曲子以及当下的招牌语等等。每个章节带有知识考古学的“题记”,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在这些或是典籍记载或是口口相传的地方性知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老的羌族时间里的沧海桑田,同时也在作者的发掘中看到了被遮蔽的羌族文化的发展延续以及它在中国文明大传统中的小传统。我想,如果不是对文化人类学有训练的学者,看北川、写北川是很难从这个角度展开的。
就讲述者的主体和它的对象来说,我们知道,任何事物一经叙事,必然会带着叙述主体的主观色彩或主体性。《去北川》的讲述者是刘大先,他讲述的是他的亲力亲为和目光所及。这种主体性里隐含着他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比如《尼萨》讲开天辟地的过程,“前两代人都在地壳的翻覆中毁灭,到了第三代才稳定下来。口头文学中还提到地壳稳定之后,地下还有一头牛,只要它动一动,就会发生地震。天神东巴协日用绳子将牛绑起来,但忘了捆耳朵,牛耳朵晃动的时候,还是会发生地震。”但是,生活依然在继续,“无常的遭际被当做平常之事而坦然接受”。刘大先说,这是“人民坚韧的情感结构”。从一曲羌族古歌看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情感结构”,这就是发现。汶川大地震没有把北川截然划分为震前、震后两半,重建后北川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看到举国援建的巨大力量;北川人内部的文化结构、精神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这种隐形力量只有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才能呈现出来。因此,刘大先用那么多羌族历史文化材料并不是对一种奇观的热衷或猎奇,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一个族群没有变化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称为精神文化结构。
此外,《去北川》有着丰富的生活细节。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最重要的就是发现细节,特别是对一个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的理解,没有细节几乎是难以进入的。于是我们看到,春节前某日,作者去马槽乡慰问时,一个生活中进退维谷的老太太“看见干部来了,就想多说说话、谈谈天。至于县里的干部能否教育好她的儿媳,倒在其次。”这让“这位干部”又羞愧又感动:“那一刻,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她对‘政府’的依赖,就像那种留守儿童或空巢老人见到归来的家人时候的感情……这个场景令我久久难忘。”他还讲了一位“母大爷”,这位“母大爷”的功劳是对石椅村的“文化恢复”。他热爱传统文化,长期致力于挖掘、收集,整理羌族民间文学,他口才极佳,羌文化修养深厚,对各种礼仪习俗了如指掌,2008年被认定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羌年”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母大爷的外在身份,同时,刘大先写出了这位耄耋老人的鲜活形象:“他身形高大,称得上虎背熊腰,穿着羌袍气场强大,更兼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出口成章,幽默风趣的话往往能让人开怀大笑,完全不像八十多岁的样子。”刘大先并没有过多写那些宏大的场面,而是通过具体的人、场景和氛围,将北川的当下生活写得活色生香跃然纸上。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最后一点就是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关系。书中第五章《少年禹的传说》,说的是羌族居住地石纽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生下三天会说话、三个月会走路,三岁就长成了一个壮实的汉子。这个传说来自羌族民间故事《大禹王》。北川要打造大禹故事品牌,要将传说作为文化资源为当下服务,这是许多地方都在实践的文化创意产业。有趣的是刘大先关于大禹故里和大禹存在方式的看法,他没有和一些学者争论,而是保持自己的观点——有两个大禹:一个在信仰与情感空间,一个在物理和历史空间。对民众而言,前者可能更为重要,刘大先认为,“过去”和“历史”的差别关乎当下与过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和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是两回事。无论真实与否,“过去”只有和大众建立情感关系才有力量。类似这样的真知灼见,没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是难以做出判断的。这章几乎就是一篇论文。还有《羌食志》,刘大先从聚会的酒席说起,通过不同民族祝酒歌的比较,认为羌族敬酒歌要委婉朴素得多。通过敬酒歌发现羌族的民族性格,这是一个学者的眼光和方法,也让我们从一个方面认识了羌族的温和善良。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无疑增添了《去北川》的文化含量和作品的分量。
在“回北川”一节中,刘大先说:“我在北川的一年,既没有春风得意,也没有失魂落魄,像一个平常又平庸的人一样工作与生活。这大约才是一切的根本,它会让一个人心平气和地欣赏、接受一切,既不会志得意满、忘乎所以,也不会心怀怨怼、牢骚满腹,这两种情形都会破坏真实的心境。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与平庸,他们构成了无比真诚又无比坚实的人生。他们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人生的体会,也是文学,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主位立场。我想,《去北川》之所以让人感动,重要的就在于真诚、诚恳,文如其人。当然,刘大先对北川历史文化书写的方法,也帮助他超越了那种主题写作的浮泛和肤浅。他的“在世界行走,为北川停留”,也就不是一句时尚的口号和轻浅的抒情。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