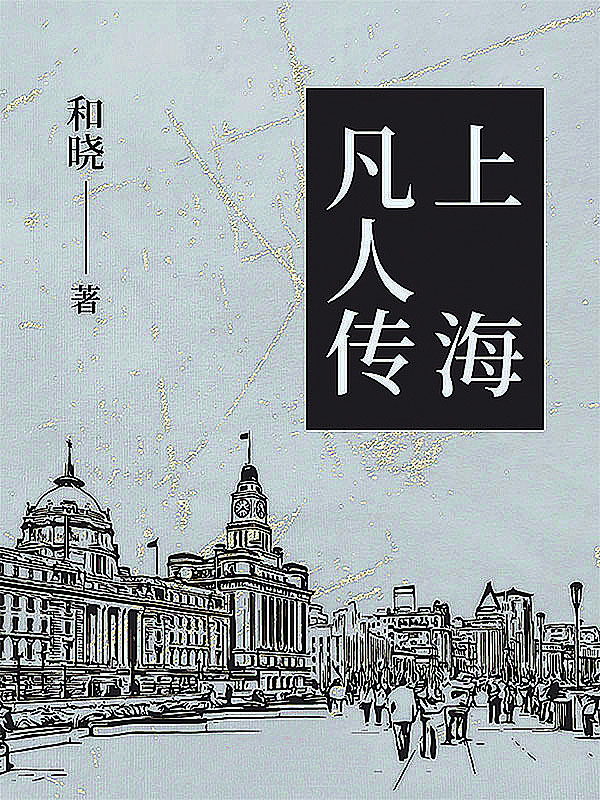□李林荣
《上海凡人传》以上世纪90年代初以降30年间历经沧桑巨变的上海为时空背景,显示着典型的“年代文”特征。贯穿故事首尾的男一号朱盛庸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有一个资质起点比他明显高一截的哥哥,这样的人设配置颇有几分取法《平凡的世界》的意味。通读之下,能感觉出故事框架和叙述方式都极具时下流行“年代文”特征的《上海凡人传》,其构思立意的初心起念,恰似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手稿上写下的原书名“普通人的道路”——要把时代的宏阔变迁具体而微地细化到普通平凡的人生道路上。
《上海凡人传》将时空背景放置在世所瞩目、众所周知的上海,既是讨巧,更是挑战。上海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和城市建设发展的标志性成就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属于铁板钉钉的史实,忽略过多则失实,虚构过甚则失真,而悉数照搬、一一罗列,则又容易流于冗赘,挤压人物和故事演绎。类似这样的虚实要素的取舍与匹配,实际上是以“普通人的道路”来印证大时代变迁,来细化社会发展的画卷脉络。
《上海凡人传》的解决之道是,从设置人物和铺排情节的层面发力。它以贴着城市风土人情、顺着时代潮流的方式,构建起故事框架,形成个人成长史、家庭变迁史和社会发展史三个层面、三条线索,既交叠又牵制。为这一画卷注入灵动神采的主人公和次要人物群像,尽管皆为虚构,却一概如实地依照社会心理传统中积淀的精明而务实的“上海人”气质和“上海人”做派。这不仅使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言行和观念,都突破了一般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人设”悬浮不落地、流于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局限,具备了直接切入社会现实和城市人文深层肌理的在地性和典型性。
主人公朱盛庸先是挖空心思争取赴美留学,后又因决心陪伴垂危的外公而转让出国机会,随后30年在家里家外、职场社会一路跌跌撞撞又峰回路转,每一步的向前迈进和变向转折,都在演绎着他作为普通上海人,也即“上海凡人”的不同侧面。开头争取出国留学是精明应变、紧随社会风尚的大流,后来突然放弃出国是质朴务实、执着孝道的常情,两者合起来正是凡庸克服凡庸的自我认命。
人如其名的朱盛庸,从蜗居筒子楼的双职工子弟,到职业技术学校外事文秘专业学生,再到青浦韩国现代电子公司的青年员工,随着公司被收购、合并,由青年步入了中年,不但没能像精英白领那样稳步上升,反倒遭遇了一连串变戏法似的被动变化。他终于渐渐觉醒,从被动变主动,从随波逐流变顺水推舟,选择了从脱落到被单位绑定、被工薪族生存模式边缘逃离,转而跃入通过精心炒股所得的经济收益,来维系自己的身心体面和安稳小日子。
与此同时,人生轨迹高开低走的哥哥朱盛中,接受了朱盛庸转让的留学名额、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李礼刚,眼界短浅、结局也并不差的美貌前妻冯嫣,原籍安徽的新上海人、现任妻子周画白……都各得其所、各安其命地沉浸于岁月静好的状态,在朱盛庸的身边演绎着“上海凡人”貌似参差、实则齐一的生命群像。即使是在快速发展和变迁的上海,仍然是凡人最多见,凡人的活法最普遍,凡人的道路最寻常。
就这样,在主人公担纲的故事主线之外,群像式“凡人”列传同时展开,《上海凡人传》为时代大潮中流转的凡人生活,凿出了条理致密的立体纹脉,镀上了层层叠加的鲜亮暖色。其效果无声胜似有声,不是赞美而胜似赞美。就文学叙述伦理来讲,聚焦本身就意味着重视,持续聚焦往往意味着深度的理解和认同,得到被叙述和自叙的机会,就意味着赢得了认同和自我证明的机会。
正如笔墨饱满的人物塑造,让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初期10年大背景,在《平凡的世界》里变成农家子弟孙少平及其亲友生活选择和思想道路的舞台,《上海凡人传》绵密的人物描写也为“上海凡人”朱盛庸们,在上海纵深步入改革开放快车道的发展史册上,争取到了充分表现他们与时俱进、精明务实生活风范的一方大舞台。
通读全书,《上海凡人传》也显露着网络小说常见的一些不足。如故事推进手法单调,过度倚重人物对话,以联翩堆集的对话代替、湮没或抑制心理活动和环境氛围的描写。尤其后半部,灌水式的对话渐多,语句浅白冗赘,模糊了人物的个性差异,冲淡了文学色彩。另外,人物定型过早,开篇不久主要人物性格似乎就停止了发展,此后际遇一路向前向上,只是在反复印证已定型的性格特质。这些可能都属于因袭幻想类网文写人写事陈规俗套的惯性表现,亟待加以更新和改进。对于主要人物关键时刻取舍进退的行为突转背后的心理起因,也存在充实和深化的余地。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