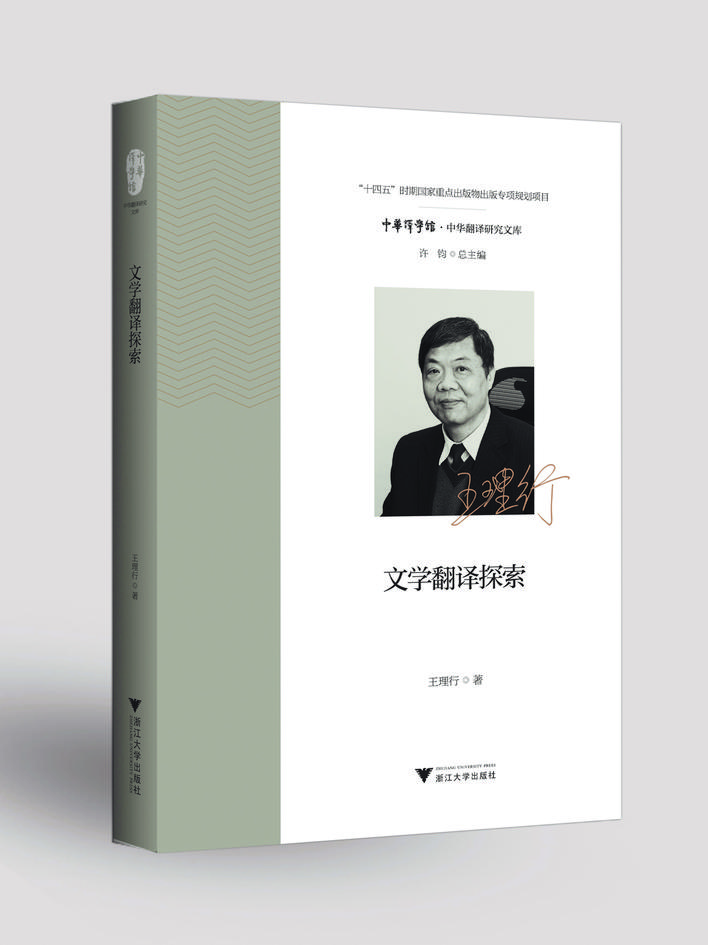王理行,1964年2月生于浙江义乌,1985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并获硕士、博士学位。一直从事外国文学书刊编辑工作,曾任《译林》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译林出版社编审,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迄今共发表中外文学、翻译、出版等方向各类文章近三百篇,有译著《金银岛》《专使》等多部,《文学翻译探索》是其最新著作
“成为杂家、专家和翻译家”
我对文学翻译的思考与探索,始于我的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的开端。
1985年夏,我从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分配到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编辑部(译林出版社的前身),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外国文学书刊编辑出版工作。我在编辑外国文学译稿时,常常萦绕心头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翻译?什么样的外国文学作品值得翻译过来?文学翻译该怎么做?什么样的译作是好的译作?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要发表或出版,最起码要达到什么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我心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尺度: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要发表或出版,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有两点:一、对原作的理解基本没有问题;二、译文基本通顺。之所以用了两个“基本”,一是因为任何译者,哪怕本事再大,外语水平再高,要想对一部异国人用异国语写的,尤其是个人风格和地域特色较为明显的长篇作品理解得滴水不漏毫无差错,是不可能的,二是因为不论持什么翻译标准或用什么翻译理论(甚或有人宣称不用任何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不论译者汉语和文学修养有多好、翻译经验有多丰富,译者自认为很通顺流畅的译文中,总会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让他人感到不太顺畅甚至别扭之处。
1986年春天,在无锡,美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施咸荣先生言简意赅地告诉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国文学编辑,必须努力使自己同时成为杂家、专家和翻译家。从那时起,尽管很难,我还是一直在朝这“三家”的方向努力。
我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从事一定的翻译实践,翻译了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亨利· 詹姆斯的《专使》等著作。有了一定的外国文学编辑和翻译实践后,我渐渐认识到:一般说来,毫无文学翻译实践经历的人,不大可能成为出色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因为他们很可能对翻译中因主、客观因素导致的局限性把握失准。
由于工作需要,我一直与许多高校外语院系的专家学者有联系,还与其中的一些老师成为了长期的朋友。他们不仅在编辑工作上与我紧密合作,成了我的译者或作者,还在学术交流和研究方面给了我各种各样的鼓励、帮助和机会,比如,请我去参加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旨发言或对学者们的发言进行点评,请我去给师生们做讲座,请我去参加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等。这些都促使我在编辑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翻译生涯中的良师益友
在文学翻译探索方面乃至我至今的人生中,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是许钧教授。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1987年秋在他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我们一见如故。近40年来,他是我的师与兄,无论在工作、学术还是生活上,我有任何问题,第一个想到去请教并肯定会得到教益的,就是许钧先生。他作为栏目设计者和对话者,我作为编辑,我们一起从1998年开始紧密合作连续三年整,在《译林》杂志“翻译漫谈”栏目上,刊出了他与季羡林、萧乾、叶君健、草婴、许渊冲、杨苡、李文俊、郭宏安等20多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老一辈翻译家,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就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畅谈各自的独到经验、体会和见解。随后,这些对话又结集成《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一书,堪称某种程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做了一次梳理与总结,为文学翻译实践的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切实可行的经验,为以后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许钧先生一直鼓励、鞭策我在工作之余要坚持多看书、多写文章、多做翻译,尤其在人生的低谷期更要坚持不懈。他每有新的翻译理论专著问世,我总是第一时间拜读,总是受益匪浅,并写过多篇书评,把我对他的最新专著印象最深的感想与学界同仁分享。
我在译林出版社退休前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促成八卷本“许钧翻译论丛”的出版,并担任其中《翻译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等书的责任编辑。在文学翻译研究方面,许钧先生及其著述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在文学翻译方面的许多观点都与许钧先生的观点相近。当然,由于两人成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工作经历和个性脾气都有较大的不同,我们就文学翻译的论述,也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和差异。他一直在专门从事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硕果累累,是当今中国翻译界最杰出的代表,而我只是业余时间偶尔就文学翻译有感而发。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专门搞学术研究的,而只是学术的票友,只是高兴时扯几嗓子而已。
1980年代后期,也就是我外国文学书刊编辑工作的初期,我编辑外国文学译稿时,都是拿原版书和译稿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对照审读校改的。当年编辑孙致礼教授重译的《傲慢与偏见》译稿时,我拿原版书、孙致礼译稿和王科一先生的译本同时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审读校改。刚开始,我这个刚出校门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小心翼翼地给当时在文学翻译上已有所成就的中年译者孙致礼先生写了封信,在信中列举了我编辑他译稿开头部分中的十个例子。每个例子都包含原文、孙译文、王译文,并说明了我对两种译文的想法、疑虑或改进的建议。在信的最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我是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本科毕业生。如果孙老师觉得我信中说的还有点道理或有值得参考的地方,那么请孙老师对我提到的译文做适当的调整或修改。如果孙老师觉得我是不知天高地厚尽在胡说八道,那么我就不再给孙老师写这种信了。不久,我收到了孙老师热情洋溢的回信。他首先肯定了我信中所说都很有道理,对他改进译文质量很有启发和帮助。他对我提的十个例子中的九个例子中的译文进行了修改,保留了其中一个例子的译文并作出了说明。在信的最后,孙老师感谢我如此认真细致又严谨地对待他的译稿,并鼓励我说:希望我不要有任何顾虑,对他的译文有任何想法和建议,发现有任何问题,都要直截了当地及时告诉他,他一定及时给我反馈。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推出一个尽可能好的新译本。他还感慨说:“看来,一代新的外国文学编辑正在成长中。”此后,我便不断地把我编辑他的译稿时的想法告诉他,他总是非常及时地给我回信。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本于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出版,得到了翻译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与好评。孙教授对我的肯定和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外国文学编辑的决心和信心。拿原版书、孙致礼译稿和王科一先生的译本同时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审读校改,与孙教授就其译稿的频繁书信交流,则相当于我在文学翻译上强化学习、提高的过程。孙致礼教授后来成为了国内屈指可数的著名英语文学翻译家,而《傲慢与偏见》则是孙教授的文学翻译代表作。前些年我忽然想到,当年我收到的孙致礼教授关于《傲慢与偏见》翻译的回信共有好几百页,我就此写给孙教授的信的篇幅,应该不下于此。如果把我和孙教授就《傲慢与偏见》的通信合集出版,无论是对后来的文学翻译实践者还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抑或是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各类读者,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当听闻孙教授身体不适,我就请其儿媳、洛阳外国语学院的石平萍教授方便时就此问问孙教授,可惜结果是,孙教授说,我写给孙教授的那些信已经找不到了。
何谓“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
1990年代初以来,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过八九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其中,1999年《找译者难》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响强烈,该报因此开辟有关“优秀译者何以难找?”的问题讨论,陆谷孙、林少华等一些著名学者、翻译家和许多普通读者纷纷加入讨论,进而引发全国范围内长达大半年的关于文学翻译质量问题的讨论。该报当时的主编褚钰泉先生嘱我把长期以来对文学翻译的思考写成一篇长文,不料我构思好准备动笔时,他却离开了主编的岗位。
郭英剑教授长期以来是我工作和学术研究中的合作者,并一直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英剑兄邀我就文学翻译问题去他当时所在的大学作讲座,促使我在1999年国庆长假期间写出了《忠实是文学翻译的目标和标准——论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的长文作为讲座的底稿。此文即褚钰泉先生嘱我写的我多年来对文学翻译的思考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此后不久,李德恩先生说了句“好文章还怕长吗”,把此文刊载于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多年来,我曾以此文作为讲座底稿,在多所大学做讲座,在与师生们的不断交流中丰富并深化了自己对文学翻译方面的思考。此文的标题,后来也改为了“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一言以蔽之,即译者应尽可能把一部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全面忠实地再现于译作之中。“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逐渐成为我文学翻译研究的标志性观点,而我后来写的多篇文学翻译方面的文章,都源于此文中的某一论点或段落。拙文《出色的译作:既经得起读,又经得起对》曾被郭英剑、谷羽、陆永昌、王金凯等教授在不同场合论及、引用或指定为文学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必读的文献。曾经教我第二外语法语的张新木教授,在一次翻译研讨会上听完我论及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的主旨发言后在微信上对我说:他在重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女囚》时,基本上按我说的原则在做。他的汉译版本,改文采式翻译为批评式翻译,争取在文字、形象、音韵、蕴含、审美、思维方式等方面达到全面的忠实。郭英剑教授还曾与我合作撰写了《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及其界定》一文。我在文学翻译的编辑与实践中遇到疑难点,也常常会与他商量,向他请教。
曾艳钰教授是曾邀请我去其工作的大学做讲座或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做大会主旨发言次数最多的朋友。她有时让我自己随意选择讲什么,有时则给我指定讲座或发言的主题,这其实是在不断督促我对外国文学和翻译方面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收入本书的《文学翻译还需要忠实吗》《论文学翻译批评——以〈红与黑〉和〈堂吉诃德〉的汉译批评为例》《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等文,便源自最早在她工作的大学里的讲座或大会发言。
在多年来的文学翻译编辑工作中,我已养成一个习惯:在编辑一个自己新接触的译者的译稿时,我会先仔仔细细地把译稿的一小部分与原文进行对照,以便把握译文的大致情况,了解译者的翻译特色、倾向或存在的问题,然后可能会就此与译者进行电话或当面交流。21世纪初,郭国良教授的一部译稿到了我手上,我一如既往地把译稿的一部分与原文进行了对照,结果惊喜地发现,在我二十来年中接触并与原文对照过译稿的不计其数的译者中,郭国良教授在译作中的追求与我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是最接近的!七八年后,郭国良教授主持了我与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就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进行的交流。他在讲座最后的总结点评中说,我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把他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的追求,都表达展现出来了。我多年前首次接触他的译作时的感受,和他后来首次听完我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的感受,竟如此惊人地重合。这是否可以说,在文学翻译上,我们两个是心心相印的呢?也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在文学翻译与研究中也是说得通的。郭国良教授是浙江东阳人,我是浙江义乌人,他老家与我的老家相距仅几十公里,我们共同的朋友吴其尧教授也是东阳人,前面提到的许钧教授则是浙江龙游人,我们这几个从小生活在山清水秀中的浙江人对文学翻译的基本看法都比较接近。吴其尧教授每次与我谈起文学翻译,我们相互都有知音之感。有一次,吴教授在谈到编辑和译者的关系时对我说:“我的第一部译著美国作家约翰·巴思的《曾经沧海》最初也是理行兄审读了部分文字的,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我从此也建立起了全面忠实的文学翻译观(包括对原著中的标点符号不轻易改动),所以说编辑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好的编辑提供的意见可以奠定一个译者的翻译理念。”
谢天振教授从《东方翻译》创刊起长期担任该刊的执行主编。他曾对我说,该刊不欢迎“面目可憎,空洞无物、难以卒读的学术八股文”,提倡生动活泼地探讨翻译学术的文章。从2013年到2020年,我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写出来的或长或短的文章,先后在《东方翻译》上发表了五篇。据谢先生手下的一位青年编辑说,有一次,谢先生拿着我投稿的一篇短文说:你们看看,学术文章还可以这样写!谢先生在收到拙文《“献给薛庆国”——阿多尼斯中国题材长诗〈桂花〉献词历险记》一文后,很快就在微信里给我回复说: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要知道,我和谢先生对关于翻译的有些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比如,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次文学翻译会议上,谢先生听了我的发言后曾针对我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明确的异议。与此同时,他却又在他自己主编的期刊上一再发表我写的文章,还不吝溢美之词。他的这种雅量与对自己观点不尽相同的后辈的提携,令我一直心怀钦佩与感激。
是工作,也是乐趣
微信群和朋友圈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交流。不知不觉间,微信上的交流催生了我的好几篇文章。远在澳大利亚的崔少元先生对外国文学与翻译的热情一直不减,经常会就相关问题或想法在微信上与我交流。《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怎么译?》一文,主要就是根据他与我在微信上就此交流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关于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与授奖词的翻译》一文里的部分内容,则录自当年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布后与外国语言、文学和翻译相关的一些微信群和朋友圈里的热烈讨论。《den是什么?》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微信上与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同学和朋友们探讨的记录。
由于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我与翻译界的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过接触,对其中有一定了解、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萧乾、文洁若、叶君健、赵瑞蕻、杨苡、戈宝权、施咸荣、李文俊、梅绍武、朱炯强、张柏然、许钧诸位先生,我对他们的为人为文分别做过点点滴滴的记录。
有一种说法是:你的朋友圈决定了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近40年来,我一直就是个外国文学书刊的编辑,但因为在学术界交了一批好朋友,不知是一直被他们往学术圈里拽,还是我天性就容易被学术圈所吸引,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一直在做一些与学术相关的事情,也写了些学术性的文章或论文,那都是有感而发,完全是兴之所至,想写了才写,写了有快感,有乐趣。
(本文系《文学翻译探索》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