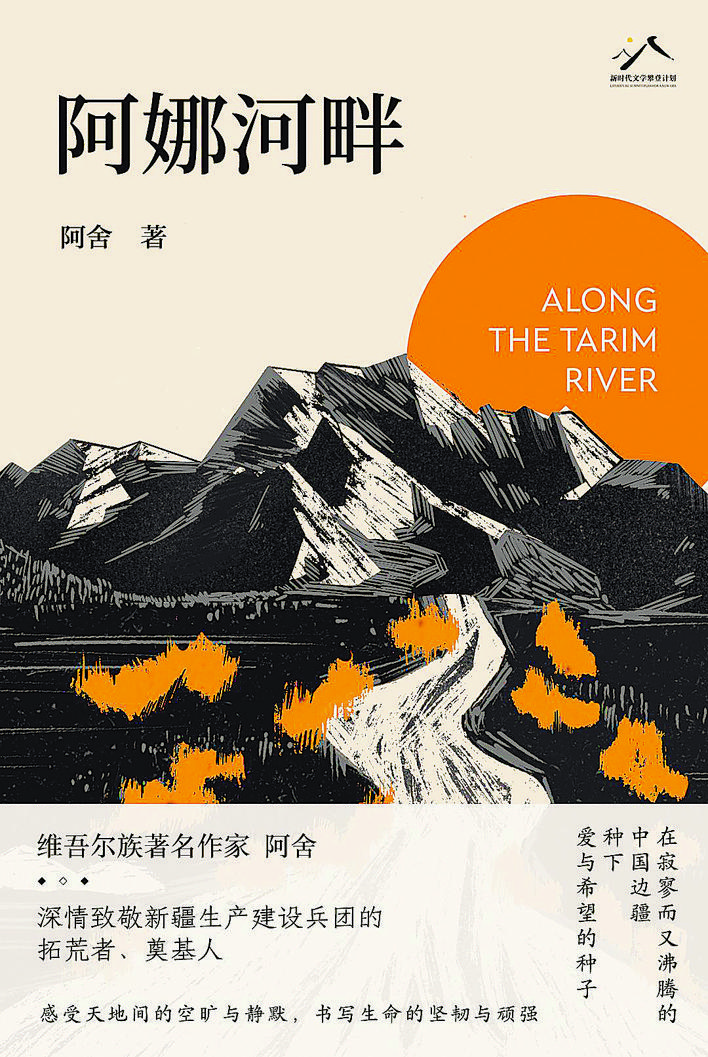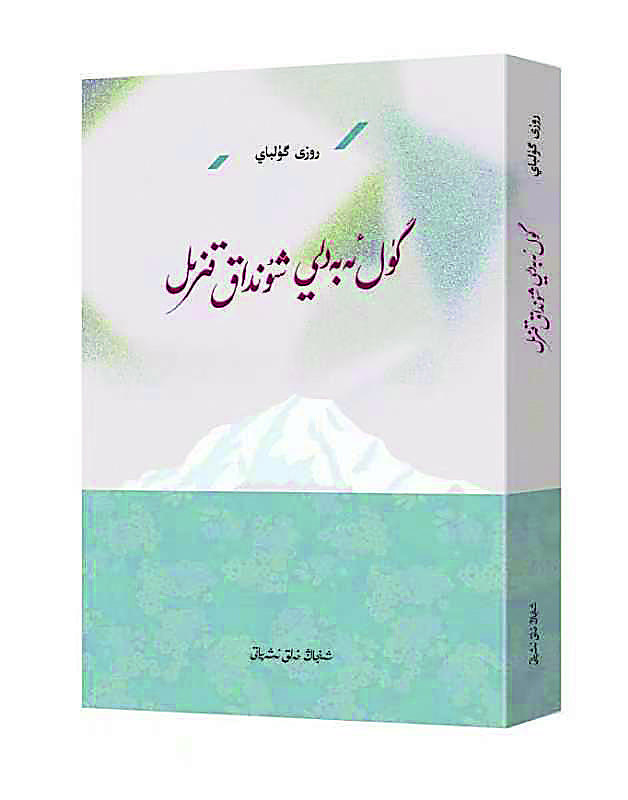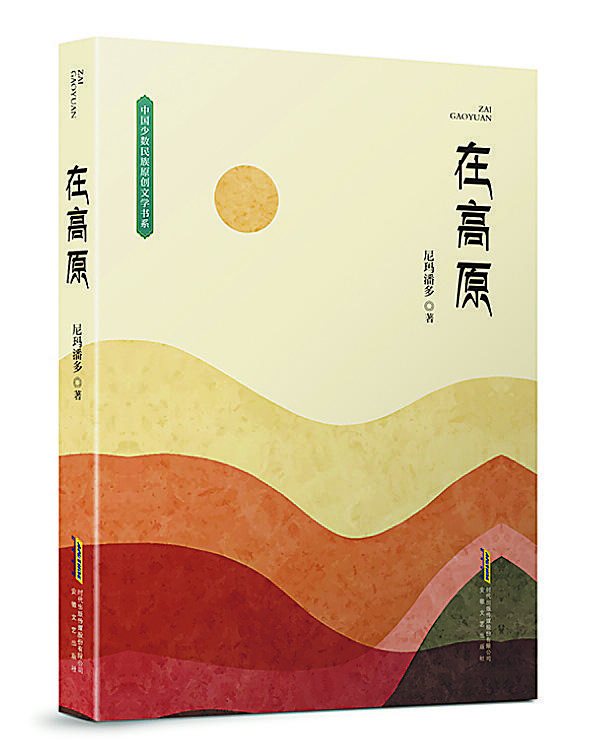《大医》,马伯庸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12月
□李 静
纵览参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百余部长篇小说,不难发现其中形成的几种主流叙事模式:或以个人奋斗、家族传承、地域发展为缩影,以线性之轴推演“成长史”,展示历史的沧桑变幻;或深描特定时空的民族文化,细剖多种文化的交织互动,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互中展开自己的故事;或立足于当代视野,勾勒崭新时代境遇下文化转型与交融的进程。当然,也存在跳脱民族题材的多元故事。综而观之,可谓丰富、开阔且充满当代气息。以最终获奖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烟雨漫漓江》《大医》《在高原》等为例,可以更具体、更典型地观察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另一部获奖作品《花儿永远这样红》以维吾尔文写成,受限于语言能力,本文暂时无法涉及。但毋庸置疑,这五部获奖作品提示我们应当以高度开放的视野,去努力拥抱当代中国文学共生共和的辽阔版图。
上述四部获奖作品当然各具风格,但若合而观之,也存在共通的创作特色与美学追求,显示出讲述当代中国故事的趋势与特点。具体来说,可以在“大与小”“虚与实”“古与今”这三重辩证关系中加以考量。对这三重关系的处理,无疑考验着作家的认知能力与写作功力。
第一,大与小的辩证。以文学书写抵达宏大叙事,实现个人与集体、审美与历史的辩证。这四部获奖作品的共同点是既具备跨越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历史纵深,又丰盈着灵动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从而避免了口号化、公式化的创作陷阱。作为兵团二代,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创作《阿娜河畔》的动力源于故乡的消逝(兵团农场合并)。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中是母亲的意思。小说正是以生命源头的记忆打底,创造出“茂盛农场”这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缩影与典型,书写出建设者们自20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的生活历程,以家庭叙事与大历史实现共振。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也持有相近构思,以一家四代人的经历,映照西藏近百年的社会发展历程,在家族叙事中揉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动态历史。与阿娜河温情注视着的兵团故事类似,瑶族作家光盘的《烟雨漫漓江》是一曲动人的漓江儿女生活史、情感史,他们的命运在城乡结构、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徐徐展开。这类作品着重描绘亲情、友情、爱情,以此“叠印”大历史之于个体的影响,既具备足够的心理与情感深度,又能将之放入大历史中加以形塑与拓延。
满族作家马伯庸的《大医》则相对跳脱出作家的实际生活经验。他的创作可以追溯至2017年参观上海华山医院校史馆的经历,最终由《日出篇》与《破晓篇》上下两部构成。这一共计80万字的鸿篇巨制写出20世纪前半叶医疗史的宏阔图景,“大医”之名,取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其所代表的爱国情操、人道情怀与理想主义信仰,具体落实在三位主人公(方三响、孙希、姚英子)身上,更散落在星云璀璨的人物群像之上。三位主人公各具典型性,分别代表穷小子、海外精英与富家千金三种人物类型,他们正是在接连不断的历史大事件中互相扶持、救死扶伤,最终成长为一代大医。
可以说,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无不可亲、可感,作家为他们付出了全部的爱意与热忱。历史与现实中那些活生生的人,那些在大历史中容易被遮蔽和遗忘的普通人,正是作家们的心之所系。马伯庸自述信仰人民史观,正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而尼玛潘多自《紫青稞》以来的创作,也被评论家指认出鲜明的女性特色,女性在她的作品中是充满能动性、有着自身成长线索的历史主体。这些都体现出文学创作在个体视角与宏大历史之间勾连转圜的独特价值。
第二,虚与实的辩证。发扬文史互动的文化传统,以历史经验激活文学的创造能量。这四部小说的写作均有不小的难度,作家们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根据阿舍的创作谈,她自2016年起就开始专门搜集与兵团有关的资料,包括兵团教育、兵团水利、解放新疆史料、早期妇女进疆史料、知青进疆史料等,还包括各团场史志丛书、个人口述史以及专题论文,等等。同时,她还有意识地采访家乡亲友。这一认知扩充的过程,使得她对兵团的追忆“不再是自我的、碎片化的、怀旧式的、图解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阿舍语),而是在浩大的生命旅途与时代印痕中铺展为更广阔的画卷。马伯庸则大量涉猎上海华山医院院史、上海《申报》、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总会历史资料和近代医疗史等专业文献,甚至每天翻阅《申报》以便全身心地浸润于彼时的海派文化。光盘怀抱为漓江立传的宏愿,设计了深入漓江流域的采风计划,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定点采风,与当地村民、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深度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
记者出身的尼玛潘多有着对于新闻事实的敏感,但如她所说,文学相比而言有着更为细致的生活底色。作家们最核心的能量爆发于虚构与再造之中,他们以高度自觉的艺术选择(包括结构、节奏、语言、人物等)去点滴建造出那个可信、可感、可读的文学世界。阿舍特意选择朴素的现实主义策略去匹配硬朗坚毅的兵团历史,以“万川归海式”的叙述结构(谢尚发语)去传递兵团人的精气神。小说沉稳明净的叙述语态,仿佛在应和着阿娜河的波流。在小说人物成信秀的眼中,“阿娜河静静流淌,夕阳金红色的光芒越过河对岸浅金色的芦苇丛,斜洒在河面上,照得宽阔的河面一片金光闪烁……苍茫、宁静,一种于地老天荒之后仍立于不败之地的朴素,没有悲伤,更没有浮华,只有令人心绪澎湃的辉煌”。朴素,辉煌,一如文字的腔调。《大医》延续了马伯庸“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三明治写作法”确保了历史观念与生活细节的真实性,而在历史的空白处则大加发挥,敷衍成篇。《大医》虚构的三位主人公,牵引出三线并进的高密度叙事结构,充满戏剧性与画面感,并以限时的时间结构与迥异的空间经验催生出故事的紧迫感。《在高原》使用了双线叙事来扩充历史容量,在呈现西藏当代日常生活方面,则选取了朴拙却又充满意蕴的语言,还经常调用民间俗语来烘托故事的烟火气。《烟雨漫漓江》由“春绿柳”“水流夏”“风动秋”“冬日暖”四个篇章推演而成,与其生态小说的定位相得益彰。在环环相扣的叙事节奏中,小说从容地生成了四季流转、生生不息的漓江故事。
第三,古与今的辩证。以当代关怀激活历史脉络,承担着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与美学追求。《阿娜河畔》不只是献给父辈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年历史的致敬之作,同时也是带有当下问题意识的文学启示录——“人必将置身于自己的时代,必将被风浪所裹挟,然而作为个体的你将怎么办?你将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便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场徒劳,你又该怎么办?所以,我所渴望的是——通过书写一个两代建设者的故事来呈现并保护住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阿舍语)反思当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与极端的个人主义,是阿舍压在纸背的关切。《大医》以医疗史为入口,唤起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的无数读者的共鸣,马伯庸非常善于提炼古与今之间的精神共性,将历史引渡进当代大众生活之中。《在高原》突破了先锋化、景观化、神秘化的西藏书写,致力于写出“原生态”的、当下的西藏。尼玛潘多对此是高度自觉的:“在众多表现西藏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西藏或是神话和玄奥的产生地,或是探险和猎奇的代名词,唯独缺少对西藏现实及普通人的关注,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外衣,以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烟雨漫漓江》对于城乡结构与新乡土生活的思考,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追问,对于自然生态的神圣性的开掘,也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的“时代之问”。
上述作品从辽阔的戈壁写到风雪交杂的高原,再到烟雨弥漫的漓江,甚至抵达《大医》所构建的全球视野,一座座“文学地标”拔地而起,一处处“文学地理”变化万端。其中所涉及的大与小、虚与实、古与今的三重辩证关系,既彰显出创作的难度,又体现出最新的创作水平。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将在文学观、历史观、审美创造力等多重维度继续突围,在与时代相伴而行的过程中推陈出新,为多元一体的文学图景持续绘就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