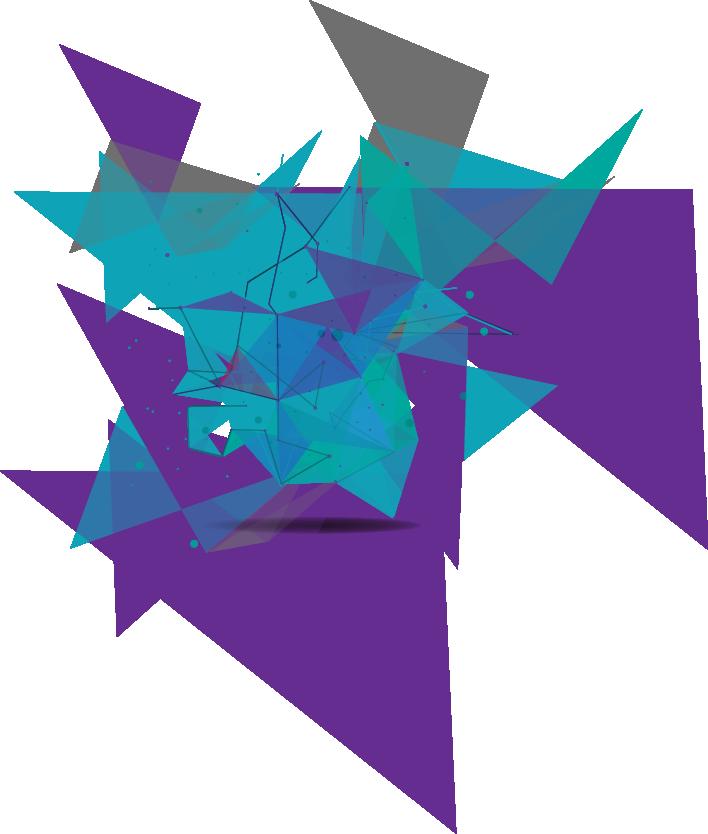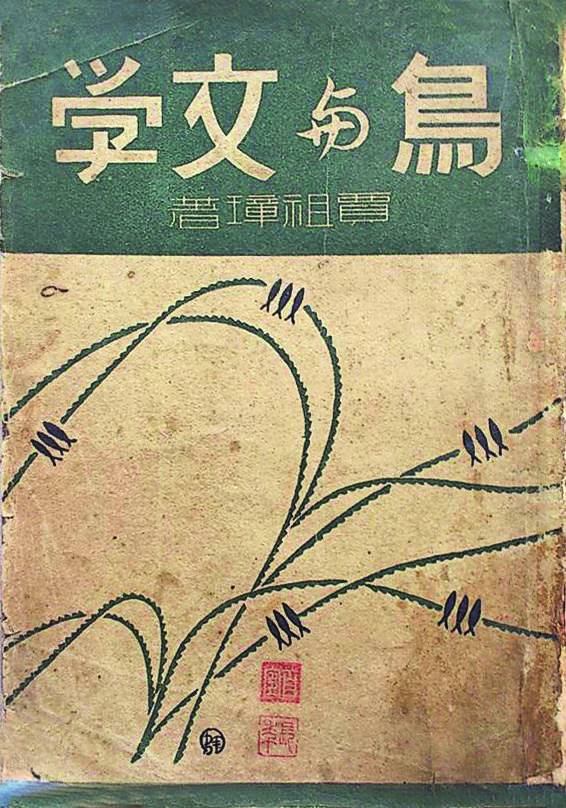科学研究领域,科学普及工作和科普写作者,比起精英科学家较少受到科学史家的关注。而在文学领域,近些年科幻文学持续升温。科幻文学及其IP衍生文化产业受到热烈关注。与之相较,科普文学的文学边界则相对模糊。某种意义上说,科普文学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它应该属于更大领域的科学写作。在世界范围内,科学写作有其历史。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教育与“心智培养”等信念联系在一起。及至今天倡导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时代,在人文关怀的背景下,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性重提且愈加重要。因此,研究科普文学,跨学科本身产生的多维度的话语交会也是自然而然的途径和方法。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科学写作的历史和前景。一是,以科普的编史学方法耙梳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专业人士进入科普写作领域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范式。二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物传统,发现“博物”学的认识方式和精神对于科普写作的启发。三是,从当代科普写作现场讨论科普写作的跨学科趋势及对虚构写作的激活。
从科普的编史学方法来说, 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成为活跃的科学普及者。1862年维多利亚时期科普作家托马斯·赫胥黎做的“关于生命世界成因的知识”系列演讲,被称为物种起源的“平民化解释”。达尔文在给他的信中称:“它们可以广泛激发公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指出“一部杰出的论著只有用来培养博物学家才是真正服务科学”。赫胥黎在职业生涯后期越来越多参与到科普活动中,他在《生物学和地质学讲演录》坦言将精确和普及性融合在一起,对科学和文学素养都有极高的要求。
因近年我的写作和研究与女性议题有关,我注意到女性科普作家的写作及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女作家创造出一种“亲切写作模式” (采用书信和对话的“亲切文体”写作)。19世纪中叶前,女性在植物学领域获得更多文化认可。到19世纪晚期,她们发展了概括性综述的潜能,当她们进入到文学领域,作品中对自然的关爱不仅指向科学知识,也指向了道德启蒙。
据此,能够发现科普写作中的文学维度由来已久,且形成不同的叙事手法和进化论史诗的样板,以至于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科普写作。科普写作叙事手法中的文学尝试包括亲切写作模式、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借鉴博物学的奇闻逸事、借鉴旅行文学或自然漫步等。不仅如此,在虚构的文学维度则有更多修辞方法和文本征用。比如常见的拟人化手法赋予自然说话的能力,比如将诗歌和文学融入作品中(浪漫植物志引用浪漫主义诗歌、描述与树木相关的历史文学话题),等等。
《剑桥19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主编吉莲·比尔1990年指出,科学写作应当超越“通过文学呈现科学”单向交流,科学和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彼此重叠或相互渗透。可以观察到的是,科学话语正在重新激活跨学科研究场域。科学和文学如何在文学批评里“重叠”,文学中蕴含的科学元素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仍然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为例,比如《维多利亚文学、能量和生态想象》以热力学定律视角,分析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能量表现形式;再比如说《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从光学及视觉理论展开对幻觉故事和侦探小说叙事技巧的研究。
通过简单的梳理,我们发现赋予科学写作的文学性是科学写作的世界传统,而文学研究的科学维度则激活了文学研究的能量;与此同时,文学性的科学写作则对科学“普及”大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写作接引文学,从一开始是基于传播和普及的实用性考量,但就其结果而言,则在世界文学地图中形成了科普文学的疆域。
回到现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思想启蒙设定的两大时代议题。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科普文学的文体建制已经比较成熟,比如1934年陈望道《太白》半月刊“科学小品”专栏。从《百年百篇经典科普》可观察到以“科学小品”存在的科普文章,类同叶永烈主编的《科海拾贝》。但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视野里,科普文学基本等同于少儿读物,如《十万个为什么》《动脑筋爷爷》《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等。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发育出体制完备的科学写作。接续世界科学写作传统,以及科学写作激活文学,都是近年的事。这意味着科普写作和科普文学将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学生长点。这些新的文学生长点意味着新的文学可能。
梳理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文津图书奖、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作品作者构成,能够发现,有专业科学工作者的写作,比如郑永春《火星叔叔太空课堂》和袁岚峰《量子信息简话》等;有专业的科普作者,比如张辰亮《海错图笔记·青少版》。这些写作会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目的和兴趣以及科普出版的全环节。此外,还有“科学松鼠会”这种科普团队的写作,比如《一百种尾巴或一千张叶子》和《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等。相比较而言,我更多地注意到科普文学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写作的可能性。
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物传统,可以发现“博物”学的认识方式和精神对于科普写作的启发。中国现代文学的“科普小品”之所以有可能向丰富处发展,因由传统经典先“物理”而后“人情”也敞开了这类科普写作成为“有情的文学”可能性。其实,这类科普文学,我们有相当优秀的作家和成熟的文本,比如生于1901年的贾祖璋先生。贾祖璋是《太白》“科普小品”主要撰稿人,他从《鸟与文学》(1931)到《花与文学》(1989)开拓了“博物”的散文传统。《鸟与文学》将鸟的名称、种类、习性,与鸟有关的诗、词、童谣、民间故事、神话等糅合形成文学的科学写作。植物书写如《荷花》,既讲形态风姿与植物知识,又对《尔雅》中的荷花各部分的赋名作现代解释,且引《诗经》、屈子的诗歌与民歌讨论其生长地理。在植物书写中征用农书、医书、经书、类书,或者专书所见,兼具科学与文化意味。贾祖璋所承继的传统甚至可追至郦道元《水经注》,以地理环境、历史人文、文献记载、亲历经验相互融合。《洛阳伽蓝记》也记载洛阳城内外佛寺的地理及建筑,以及相关史实风俗、人物传说,兼具文化史与文学价值。
狭义的“博物”观念是通过对《诗经》《尔雅》的注释文献而建构起来的。孔子论述学诗(《诗经》)的功用之一是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钱穆《论语新解》从诗教传统阐释“多识”的意义:“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科学写作的文学实践体现社会结构及其对知识的塑造。在当下,贾祖璋“博物”的散文可以扩张到博物学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视野。约翰·V·皮克斯通在《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提出用博物的方式认识世界是研究19世纪科学的一个关键元素,提出与科学并行发展文化认知的重要性。科学史上,博物学传统是与数理传统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只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渐没落,而在今日提倡一种了解世界的博物学态度,或许是打破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壁垒的一种方式。以充满想象的方法探究博物学,这涉及科普的修辞上非虚构的征用。博物强调体验,鼓励人亲历辨识事物,突出情感经验和价值观,以对万物的好奇激发对科学的兴趣,就像果壳网主编徐来所言,对自然鸟兽知识的了解和探究,是一种将普通人带入科学领域的有效方法。基于个人田野调查的科普写作,如沈书枝、杜梨的写作,皆因个人的情感和好奇,而进入“从技术细节入手,理解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的序列。
从当代科普文学写作的一些趋势讨论科普写作的跨学科写作及对虚构写作的激活。《花神的女儿》以跨学科的视野关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参与植物科普的工作,更关注早期女性写作的多样性,和家庭史、科学体制化及性别意识形态发展的联系;《改变人类历史的植物》从农学角度观察大航海时代不同大陆之间以及岛屿与大陆之间的植物迁移现象,综合科学经济和社会学的知识信息;《万物有文》联系植物形态构造研究与装饰艺术创造过程;《过敏的真相》《看尽天下鸟》则是科普与家族故事勾连的叙事模式(非虚构)。科普写作扩张的不仅仅是非虚构写作领域,在近年徐来的《想象中的动物》、盛文强《海怪简史》和朱琺的《安南想象》等的虚构写作中,都可以观察到科普文学对虚构写作的激活。这两个方向或许是科普文学对整个文学拓殖的未来前景。
(作者系青年作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