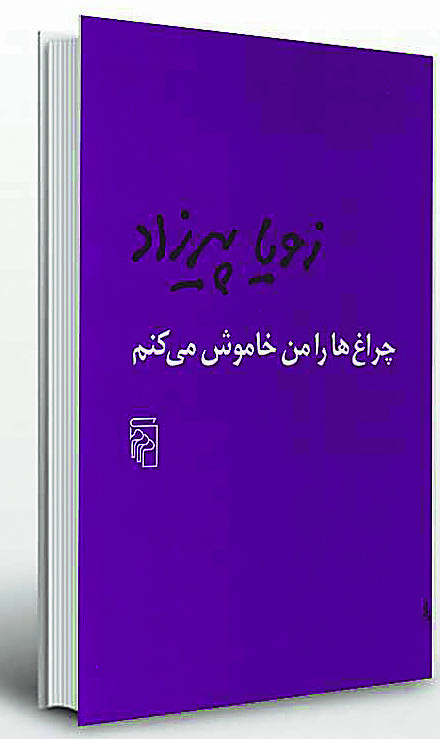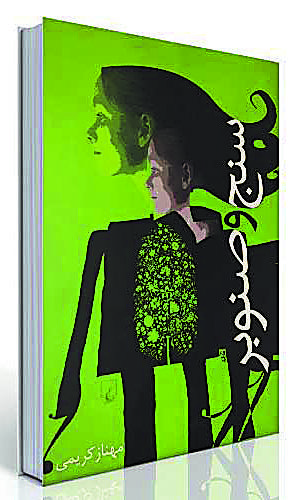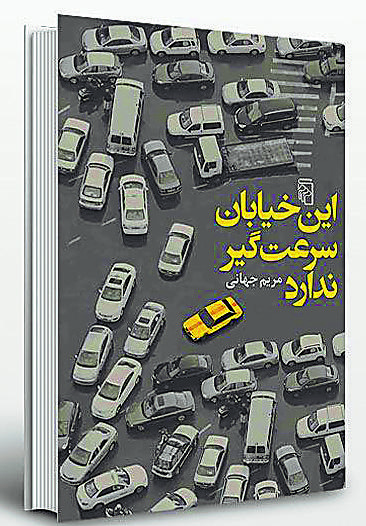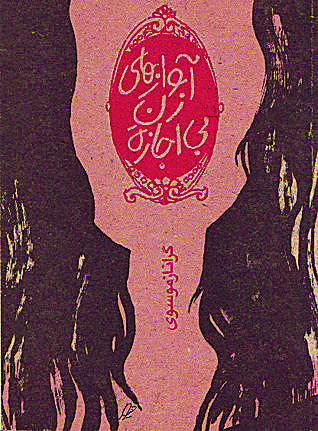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爱莲·萧华特将女性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在时间较长的第一阶段,女作家模仿主流文学的流行模式,并吸收其艺术标准和社会角色观点。第二阶段开始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并为女作家的权利、价值、自主的要求进行辩护。最后则是自我发现的阶段,即不再依靠对立面,而是向内转,转向寻求自我的同一。
回顾和梳理伊朗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以西敏·达内西瓦尔(Simin Daneshvar,1921—2012)为代表的第一代女作家属于伊朗女性文学的第一阶段,作品中作为绝对主角的女主人公几乎完全是处于男性价值体系中的;以沙赫尔努希·帕尔西普尔(Shahrnush Parsipur,1946—)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属于女性文学的第二阶段,其作品主题是对男性价值认识体系的反叛,在与之对立中凸显女性文学自身的价值。
在帕尔西普尔之后成长的新一代女作家在对女性权益的思考上更进一步。这代女作家与上一代女作家在两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上一代女作家绝对数量不是很多,大多出自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家世优越,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新世纪女作家大多来自新生的中产阶级家庭,相对优裕的生活和时间,使她们热衷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创作,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这代女作家在数量上明显多于上一代,并且是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同台竞技。这使得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女性作家群体成为伊朗当代文坛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新世纪伊朗文坛大放光彩。她们不再专注于性别问题,不再关注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对立,乃至对抗,她们几乎完全超越了爱莲·萧华特所说的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即在作品中更加关注女性自我意识的书写。
新世纪伊朗文坛上,几乎每年各大文学奖项都有女作家的身影,不少女作家的作品已经走出伊朗,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在创作思想上,新世纪登上文坛的女作家比上一代接受传统教育的女作家更关注女性自身的内心世界,因此作品中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同时,她们的作品更加向内转,更多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而非外部周遭的社会问题。归纳起来,新世纪伊朗女性文学的自我意识书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专注于女性的自我实现
第一类是描写女性的自强不息。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的大幅度提升,职业女性在伊朗社会中越来越普遍。描述女性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世纪伊朗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这类作品以法尔红黛·阿高依(Farkhondeh Aghaei,1956—)的长篇小说《学习撒旦并焚毁》(2006)为代表。女主人公瓦尔加是一位知识女性,她是伊朗亚美尼亚裔人,信仰基督教,爱上了一位穆斯林小伙子。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这份爱情遭到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但是,瓦尔加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不惜与家人断绝关系,与爱人结婚。婚后瓦尔加始终无法融入进丈夫的家庭,这其中既有宗教信仰的差异,也有家庭琐事,而丈夫也始终不能给瓦尔加提供任何支持和保护。面对这样的境遇,瓦尔加勇敢地选择离开,儿子的抚养权也被剥夺。但她凭借教育优势,辗转于各个公共图书馆,既打工挣钱,又将图书馆作为栖身之地,以此作为改变命运的途径。经过挣扎与奋斗,她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她把日常生活记录在编好的日记中,小说即是女主人公日记的展示。该小说堪称是描写伊朗女性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优秀之作。在伊朗传统社会意识中,只有家庭、父亲、丈夫才是女性的避风港湾,女性仿佛不是一个独立性的存在。而小说主人公瓦尔加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瓦尔加的人生遭遇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女性的缩影。有相当多的伊朗知识女性,在婚后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然而,她们已经有足够的分辨能力——这只是家庭角色的选择需要,并不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必然丧失。
2017年获得第十届贾拉勒·阿勒·阿赫玛德文学奖的玛丽娅姆·贾汉尼(Maryam Jahani,1986—)的长篇小说《这条街道没有减速带》(2016)中,主人公舒赫蕾是伊朗社会中另一类女性的代表。她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婚后小家庭的经济条件比较拮据。为了补贴家用,她们会做一些兼职工作,舒赫蕾选择较少女性从事的出租车司机,这对她是巨大挑战。或许这是作家的一个写作策略,以此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识在作品中得到最充分的彰显。小说在写作构思方面的高超之处,在于作家并没有刻意利用外部环境的困难来“凸显”女主人公的顽强自我奋斗。舒赫蕾的自我奋斗源自内心深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要靠努力工作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她没有把自己定位于依靠丈夫有限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家庭妇女,而是主动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不顾及外界异样的眼光,积极主动谋划如何做好工作。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21世纪伊朗女作家的一个明显倾向是,不再将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而专注于女性自我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既是创作上的飞跃,更是思想上的飞跃。
关心婚姻中的情感诉求
第二类是描写女性在婚姻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诉求和觉醒。在爱的激情褪去之后,大多数的婚姻生活归于琐碎和平淡。在这种琐碎平淡的婚姻(而非不幸婚姻)中的女性最容易迷失自我。新世纪伊朗女性文学中反响最大的两部作品,正书写了这样的主题。
佐娅·皮尔扎德(Zuya Pirzad,1952—)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灯,我来熄灭》正是凭借婚姻主题横扫当年伊朗各项文学大奖,并迅速被翻译成各大语言,2012年还出版了中译本。《灯,我来熄灭》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伊朗南部石油大城市阿巴丹,小说描写了中年女性的情感危机,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渲染,含蓄委婉,宁静致远,温馨中带着一丝伤感,很具有东方韵味。
法丽芭·瓦菲(Fariba Vafi,1963—)的类似题材的小说《我的鸟儿》(2002),深受评论家和读者的喜爱,获得了2002年度最佳小说奖,第二届“冬至文学奖”,并于2003年获第三届“胡尚格·古尔希里文学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故事以一位已婚妇女的自述展开,讲述了女人平淡无味的日常婚姻生活,丈夫没有不忠,也不乏体贴,但是缺乏温情,更没有激情。女主人公没有名字,似乎在日常生活的压抑和隐忍中失去了自我,然而心中的那只鸟儿是她们自我意识不灭的象征,小说直叩很多中年女性的心扉。法丽芭·瓦菲以小说《西藏之梦》再获2006年第六届胡尚格·古尔希里文学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如果说,《我的鸟儿》的女主人公在无爱的婚姻中表现出对飞翔的渴望,那么,《西藏之梦》的女主角喜娃则是更加主动地、勇敢走出无爱的婚姻生活,从中也可见伊朗当代女性对情感生活的主宰程度。
《灯,我来熄灭》《我的鸟儿》《西藏之梦》充分表现出已婚中年女性共同的生活困境和情感诉求,袒露出女性内心欲说还休的细腻情愫,引起女性群体的共鸣和大众关注,使她们不再被忽视和淹没在日常生活之中。此类题材的小说在新世纪伊始相继获奖与热销,说明对女性权益的关注重心已从“对立反抗”的重大问题转移至婚姻生活的普通小事,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本质,显示出伊朗女作家创作走向内倾化。
描写成功女性的迷惘
第三类是描写成功女性的迷惘。这体现出作家更深层次的思考:女性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功是否意味着真正实现了独立的“自我”。
获得2014年梅赫尔甘文学奖的喜娃·阿尔斯图依(Shiva Arstuyi,1961—)的小说《恐惧》塑造了一位职场成功女性。女主人公席黛是一位作家,在文坛具有良好声誉,是无数普通伊朗女性仰慕的对象。但是,她的内心却充满了恐惧和孤独,陷入一种成功之后的患得患失境地,成功如同漂浮在水面的水泡,会闪光,但是转眼即逝。席黛在寻求自我塑造与社会环境的裹挟这两者之间挣扎。小说充分彰显出现代知识女性在面对生活和未知压力时的迷惘。小说没有简单地把“事业成功”与“独立的自我”之间划等号,显示出新世纪的伊朗女作家在自我意识上有了新的超越。
马赫纳兹·卡丽米(Mahnaz Karimi,1960—)的长篇小说《铜镲与冷杉》(2003)获得“胡尚格·古尔希里文学奖”提名和“伊斯法罕文学奖”最佳小说奖。小说讲的是一个侨居国外的单身伊朗裔女人,在手术中接受了一个黑人男孩的输血后,欲收养这个孩子。为此,她必须建立真正的家庭,寻找能够做丈夫的男人。她回到伊朗,回忆起年轻时的几段恋情,每一段恋情都是她生活的一个侧面,每一段恋情的开始与结束都是她的自我选择,贯穿着女主人公的自我主体意识。然而,萦绕在这样一个独立女性内心深处的是深深的孤独感。小说提出一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女性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她的“真正完整”究竟是什么?
关注“自我”的丧失与压抑
第四类是描写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新世纪的伊朗女作家的关注重心已经不再是“性别”,而是“自我”。这正是伊朗新世纪女性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最大差异。
获得2005年第七届梅赫尔甘文学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马哈布贝·米尔·盖迪里(Mahbube Mir Ghadiri,1958—)的小说《其他人》塑造了一位典型的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女主人公没有名字,内心有很多想说的话,却从来没有表达自己的勇气。久而久之,她陷入自我封闭,恐惧和孤独由内而外贯穿了女主人公的整个存在。小说中并没有明显的外在力量——父亲、兄长、丈夫或左邻右舍——的压迫,女主人公是在长期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中失去自我。这既是社会传统对女性的碾压,同时也是女性本身对自己的碾压。此类作品在新世纪的伊朗文学中并不少见,如还有费蕾西苔·艾哈迈迪(Fereshtah Ahmadi,1972—)的小说《健忘的仙子》(2007)等。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超脱
第五类是书写女性对自我意识的压抑。此类作品与上一类的区别在于,作品中的女性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却迫于周遭环境不得不压抑。
其中以葛拉娜兹·穆萨维(Granaz Moussavi,1976—)的诗歌作品为代表。葛拉娜兹于199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在夜晚写生》;2000年出版诗集《赤脚到黎明》,赢得良好反响,于2001年获得伊朗非官方最高诗歌奖“卡尔纳梅奖”;2003年出版诗集《被禁止的女人之歌》,奠定了她在伊朗诗坛的地位,该诗集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语言,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出版。2010年后,葛拉娜兹·穆萨维同时活跃在诗歌界和电影界,2012年出版诗集《红色记忆》,2014年出版诗集《不,你在我皮肤上的吻无法追踪》,2020年出版诗集《乌鸦和涂鸦》等。葛拉娜兹·穆萨维获得过欧美多个诗歌奖项,多次参加巡回诗歌朗诵或讲座、访谈,在国际诗歌节朗诵自己的诗歌,是新世纪伊朗女诗人的杰出代表。
新世纪的伊朗文坛是第三代女性小说家崛起的时代,葛拉娜兹的出现使得伊朗新世纪的女性诗歌同样绽放出绚丽的光彩。葛拉娜兹的诗歌把女性刻意压制的自我意识、女性那种“欲说还休”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在《阐释》中写道:“我即使在你双眸植入蜂蜜/我依然会充满咖啡的苦涩/在你我之间,所谓故事/那从头经历过的,只是我/一个奇怪的女人在你的梦中被阐释。”该诗隐晦地书写了男女爱情中,女性的自我意识被刻意压抑了,在男人梦中被阐释的女人并非真实的“自我”。《故事》中写道:“你每一次看我/我的细胞就会彼此拥抱/我的胸膜下方就发烧/挣扎/爱恋上死神/银河把我身体遗产/在充满魔鬼的天空/播撒/请看着我!/这个奇遇之乌鸦/永远不会抵达它的巢。”该诗书写了处于“爱而不得”中的女性只能压制激情,陷入爱情的绝望中。葛拉娜兹的诗歌情感含蓄而意象新颖出奇,如《衬衣》写道:“条状衬衣/却没有一条路可走/就那样在无路的荒野溜达/直到碎裂成片。”以“条状衬衣”暗含的“路”的喻象与“无路可走”的喻意联系在一起,传递出女性的压抑、绝望的情感。
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宗旨都是让人自由地发现个人创造的新世界。要享有这一权利,首先必须得到存在的自由。女人所受的教养至今仍限制着她,使她难以把握外在的世界,为在人世上给自己找到位置而奋斗实在太艰辛了,要想从其中超脱出来又谈何容易。倘若她要再次尝试把握外在的世界,她首先应当挣脱它的束缚,跃入独立自主的境地。这就是说,女人首先应该痛苦而骄傲地学会放弃和超越,从做一个自由的人起步。”超越单纯的性别分野的狭隘性,是新世纪伊朗女性文学的一个明显倾向,伊朗的女作家不再将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而是从女性自身的特点去建构和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表现出对“女性”文学的一定程度的超越,尝试探索和建构女性作为“人”的真正“完整性”。
[穆宏燕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宋华(Narges Tabari Shahandasht)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