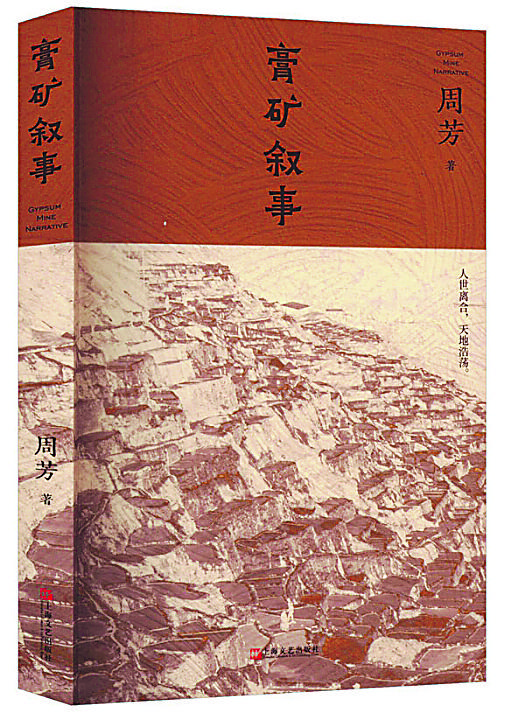周芳一直在写非虚构,《重症监护者》《在精神病院》《我亦是行人》等连续多部非虚构作品都获得良好的反响。但这回她写的是长篇小说《膏矿叙事》,这部长篇小说同她以前写的非虚构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都是写人的;其次写的都是作者自己身边的普通人和小人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周芳无论是写非虚构还是写小说,她对所写的人物不仅很熟悉,而且很友爱,她是怀着温暖的善意去写他们的。
《膏矿叙事》写的是一座开采石膏矿的国有企业里的众生相。我猜想这里曾是周芳生活过的地方,她所写的人物说不定就是曾经在一起生活的伙伴、邻居、亲友们,我从字里行间都能读出来她同这些人物之间饱满的亲情和友情。这本来对周芳来说是非常合适的非虚构题材,但她决定要写一部小说,显然是要挑战自己的叙述能力。她相信,自己的文字不仅能够真实记录下现实中的所见所闻,而且也能够生动描绘出以想象建立起来的虚构世界。
还在进行非虚构写作时,周芳就对采访的记者说过:她觉得,作家选择什么样的体裁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文学真实性的说法很好。周芳的写作中不缺真实性,尤其是她以前写的非虚构,完全是将生活的真实还原给读者的。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周芳严格遵循这一写作伦理进行写作。现在她写小说,虽不必执着于是否与生活真实紧密嵌合,但又给自己的小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忠诚于文学真实性。我理解周芳所说的文学真实性,就是指不仅要有生活的真实感,而且还要有情感的真实、心态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膏矿叙事》就是一部浸满文学真实性的小说。
这是对一代人青春的真实书写。周芳写了特殊的一代人,这代人曾经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时代特点在膏矿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膏矿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宠儿”。那时候,中国的普通百姓还不知道汽水是什么,膏矿竟然“家家户户汽水当白水喝”。当地有三宝,其中一宝就是石膏矿。膏矿的年轻人挥霍着他们的青春,他们是潇洒倜傥的“青石帮”,“井下挖膏,井上喝酒”,在井下“流大汗,出苦力”,常常“喝些没头没脑的酒,打些莫名其妙的架”。
这群年轻人处在非常特殊的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即将落幕,国有企业由“宠儿”变成了“弃儿”,他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不能理解,有疑惑,也有愤怒。他们要做国家的矿工,决不做资本家的矿工,要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抗争。矿工黄大安干活时一个顶仨,为了能保住自己干活的权利,竟闯进矿长的办公室,逼着秦矿长给他一个官职,因为当了官才能免除下岗的危险。黄大安一家三代都是矿工,他们的命运故事又何曾不是中国当代工人生活的缩影?周芳写膏矿年轻人的青春,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青春能化作一团火,也能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
这是对一代人情义的真诚缅怀。周芳忘不了当年膏矿的那些伙伴,他们一起笑过骂过,有着各自的故事。最让周芳难以忘怀的,还是大家身上那股重情重义、有情有义的劲儿。周芳写膏矿的一群年轻人,难得地生活在一个天地里,他们的“青石帮”真有点江湖味道,这也许是他们那时候都喜欢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的缘故。但“江湖有道,情义无价”,周芳用大量笔墨讲述了情义的动人之处。小说分别以八个人物(有一章是两个人物)作为章节的标题,他们自然是各个章节的主要角色,但有些章节其实讲述的是众多人物的故事。周芳之所以要用人物为标题,是因为这八个人物所释放的情义最浓烈。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矿工,有着各自的弱点和缺陷,但只要遇到朋友有难、善行受阻这类事情,在情义的驱动下,他们便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情义在平常日子里如同涓涓细流,但在非凡时刻,情义也可以惊天动地。
贺建斌只是邮政所里的一名普通职工,若不是有情有义,他又怎么能在投递信件时发现余莉芳内心的忧伤。贺建斌的初恋就是上学时靠相互通信萌发出来的,他懂得信件在爱情中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悄悄跑到武汉的医院去谴责一个负情郎,会代替余莉芳的恋人悄悄给她写信。当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最终他把自己写成了余莉芳的丈夫。这是一个情义得到回报的故事。情与义相互纠缠、纷乱如麻,一个人要把它理出头绪来是很不容易的。充满阳刚气的邱红兵爱上了白莲花,但白莲花偏偏爱上了文弱的老六子。邱红兵潇洒出走,挣了钱回来人人都羡慕,但他憋屈在心里的爱终究放不下,只好主动去找精神病院把他收下。大情大义最终解脱了邱红兵,他在膏矿建起一个矿业博物馆,把情义和胸怀都装了进去。
这还是一部向文学致敬的小说。小说的第一章写的就是一位膏矿的诗人贺小果,足见文学在周芳心目中的分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都有同感,文学在年轻人心中是神圣无比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每个青年都是文学青年,爱读文学作品,不少青年除了读,还跃跃欲试自己写。如果既不读也不写,至少也要对文学表示极其诚恳的尊重和敬佩。这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
膏矿的年轻人已经来到了这个时代的尾声。贺小果热爱文学达到了痴心地步,常常会做出反常的事情,“青石帮”的伙计们虽然跟不上他的思维,却愿意接纳文学带给他的奇思异想。当人们都为春天来了而欢呼时,他却认为春天总有一些悲伤的事情要发生。贺小果的文学种子正在酝酿破土生长,可是这个过程是多么艰难。他蒙冤入狱,从膏矿消失,但他忘不了膏矿。他被扼杀的文学理想就埋葬在这里,哪怕不写诗了,也要匿名在膏矿建一座富丽堂皇的良宵会大讲堂,“把膏矿弄得像个文艺圣地”。
膏矿出了一位大作家,他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装车工陈栋梁。当年有大仙之称的刘青松给陈栋梁算的卦就是“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陈栋梁后来成为了大作家,但他宁愿从热闹中逃出来,逃回旧时间的膏矿去,因为他的文学之根就扎在这里。陈栋梁身上或许有作者周芳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是,周芳以陈栋梁的口吻来诉说,这样才能更真诚地表达她对文学和对生活的敬意。
膏矿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象征,也是一代人的象征。周芳以深情回忆的笔调讲述了一段逝去的青春和一群有情有义的年轻人,他们定格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折射出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内涵。周芳说,她的写作是要为那个时代、那群青年留下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并不巍峨高大,但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令我们肃然起敬。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