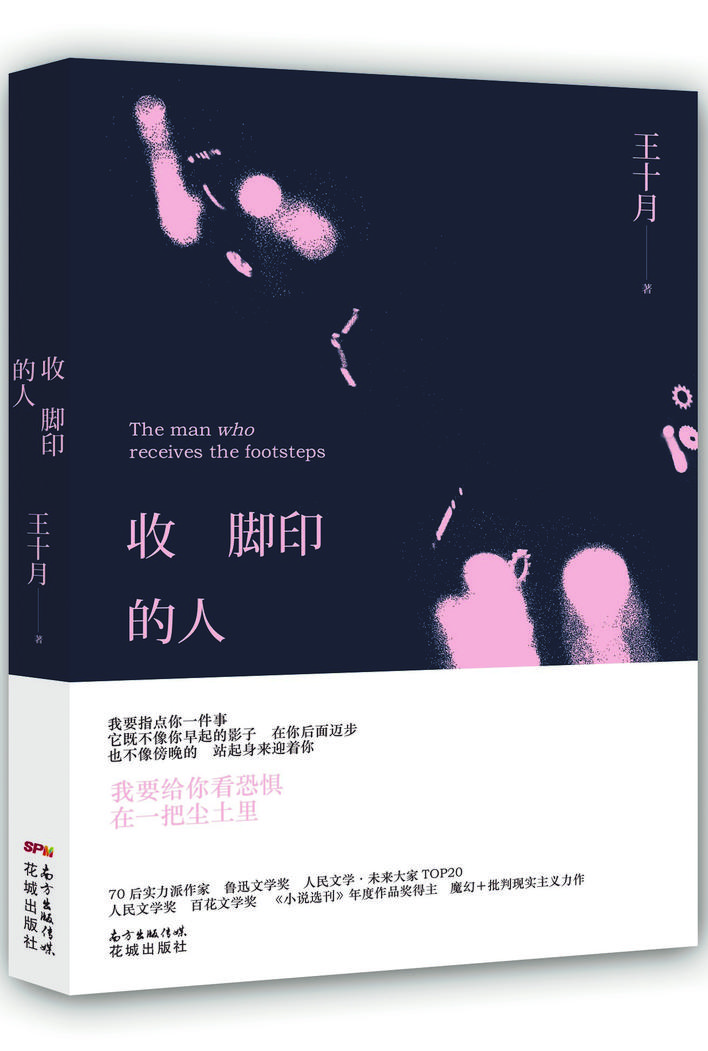近些年我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也决定了我在这部书中的取舍
鲍 十:十月你好,首先对你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表示真诚的祝贺。我是在新书首发式的前一天读完这部作品的,我把作品下载到电脑上,从下午两点钟左右开始读,一直读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吃过早饭后才去睡觉。我是一点一点被拉进作品的,直到欲罢不能。
王十月:非常感谢,那天新书发布会上您发言之前我很紧张,您是我看重的作家,也是我敬重的兄长,我很担心您“被迫营业”,站在台上说言不由衷的话,如果这样,将是对您极大的不敬重。当您说读了一个通宵很感慨时,我悬着的心就放下了。我记得您当时连说了几个“很感慨”,似乎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最终停顿了一会儿后结束了发言。
鲍 十:是的,任何优秀的小说都会形成一个自己的场,《不舍昼夜》就形成了自己的场。读完作品之后,我内心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很感动,也联想到了许多问题。
王十月:当时匆匆忙忙,未来得及细聊,因此当《文艺报》约这个对话时,我就想到您。因为我也想知道,您这一言难尽背后的未尽之言。
鲍 十:在我看来,《不舍昼夜》是一部厚重、独特、有深入思考、能撼动人心的好作品。这也是你沉潜多年之后推出的一部心血之作。我看见有读者写文章说,读《不舍昼夜》时曾几度落泪,其实我也如此。我想了解一下,在写这部作品之初,或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哪些思考促使你创作了这部作品?
王十月:想写一部新书由来已久,上部作品《如果末日无期》完稿后,我就在琢磨新书。《如果末日无期》探究的是如果人类获得了永生,我们何以度过如此漫长的一生。这是人类的千年大梦,据说不久的将来,人类的这个大梦将得以实现。但这个大梦肯定与我无关了。这几年身体出了些问题,几乎是机能全方位的溃败,比较麻烦的是颈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肝纤维化、肾脏功能损伤……朋友们见到我,都说你看上去很健康啊,壮壮的。其实都是人前硬撑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几年每年都有文友离世,我保留着这些离世文友的联系方式,会隔段时间翻看他们的微信朋友圈,有些微信朋友圈永久沉默了,有些微信朋友圈则是他们的亲人在打点,会发些有关他们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这几年,朋友的离去似乎在加速,名单越来越长。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于是有了想将这些年的所思所想写在一部书里做一个总结陈词的想法。一直没动笔,思绪太复杂、太纷乱,理不出头绪,也没找到转换成小说的切入点。2020年,有了较多自由的时间,于是想,不管那么多,先写了再说。有了这种心态,写作时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一些过去重视的东西突然变得不重要了,而一些过去不看重的东西,在我心里变得重要了起来。也就是说,我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也决定了我在这部书中的取舍,和我选取的叙事策略。动笔之前并没有想得太明白,只是想写一个人的一生,他的一生都在思考,我可以通过他的一生,来安置我的思考,利用这个人物,来代我面对困境。有些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终极难题,我找不到答案,从阅读中也没有找到答案,我想,答案可能在每个人不同的生命体验里,抱定边写边整理思路的主意,一旦动笔,许多想法纷至沓来,有些问题越想越清晰,有些问题越想越纷乱。我想,那么,很好,我就直面这种清晰与纷乱,真实地呈现此时此刻我的思考即可。
我之所以追光,是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光
鲍 十:《不舍昼夜》整体是现实主义的,又适当地运用了一些现代派文学技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端午的脑袋里住着他的弟弟,实际上是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动,有魔幻的色彩,也有超现实的色彩。尽管所占篇幅不多,却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说起来我就是在读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心头一震,一下子提起了精神的。活在王端午身体里的年仅四岁就意外身亡的弟弟,也可视作王端午最本真的生命意识的存在。
王十月:我其实并没有过多考虑这部作品是现实主义,还是什么主义的问题。所有的技法都是服务于内容的工具。但对于我来说,动笔写这部书,还要面临一个问题,这部书将要调动的生活,有很大一块是我当年的打工经历,而这一段经历,我曾经写进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也在长篇小说《无碑》中有过较充分的书写,如何处理这一生活经验而不重复?当王端午的脑子里住进王中秋,我知道,我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你可以认为,王端午脑中的王中秋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也可以认为,王中秋是王端午的第二人格,即您所说的本真的生命意识。我因此搜集了许多有关第二人格的资料。这个小说写了八稿,其中有一稿大量地写了第二人格的真实案例。事实上,我所写的王端午不只有第二人格,他是多重人格的集合体。在小说中,他换了很多次名字,每换一次名字,就换了一重人格。但后来我将这一设计否定了,将有关多重人格的书写全部删除,也弱化了王中秋作为第二人格的戏份,因为我不想写成一部多重人格争夺肉身的类型小说,不想让多重人格喧宾夺主。另外,王中秋住进王端午的脑子里,为后面的叙事开启了方便之门,如果我们要写一个人内心中的痛苦、犹疑、拉扯、拧巴,只是处理成单纯的心理活动,会显得乏味,有了另外一个灵魂,相当于是两个人物,人物有了对手戏,你来我往的,将心理活动处理成两个灵魂对话会有趣很多。
鲍 十:除此,作品中还有意识地引入了卡门、卡夫卡、西西弗斯神话等意象,客观上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王十月:引入卡门、卡夫卡、西西弗斯神话等意象,基于两点:第一,我的生命体验告诉我,作为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之所以会对生命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产生追问,是因为我通过阅读和那些伟大的灵魂产生了交集,他们影响了我。我在书中说,王端午发现他之所以堕落、痛苦,是因为他很长时间没有阅读,是因为他远离了那些伟大的灵魂。这是我的生活经验,我想分享给读者。另外,当时我的想法,我要在书中对他们表达敬意与感恩,是他们点亮了我的心智之光。文友李瑄评论我,说王十月是个追光的作家,无论我所写的生活多么苦难。我想,我之所以追光,是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光。《不舍昼夜》六个章节,分别致敬了六本书,也暗含了我要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雄心。而从写作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些作品的引入,诚如您所言,起到了互文的效果,比如第二章“铁架床上的卡夫卡”,铁架床是典型的打工生活的符号,生活在上世纪90年代南中国的王端午,面临着和卡夫卡笔下的K相似的问题,他想进入深圳市内,但他想尽办法也无法进入,这自会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于是,南头关和城堡就产生了奇特的关联,从而如您所言,客观上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立足于自己的生活,是我一直以来践行的写作信条
鲍 十: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作品主人公王端午的人生脉络,与你的个人生活履历的重合度似乎很高。所以我感觉,《不舍昼夜》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凡是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自己的生活,从自己的视点出发,进而与社会和时代发生广泛的联系,反映时代的风貌,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另一个特点是真实,尤其是细节方面的真实,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须知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除非亲身经历过,否则便无从得知。
王十月:立足于自己的生活,是我一直以来践行的写作信条,哪怕我写被归为科幻小说的《如果末日无期》,里面的人其实同样立足于我的精神世界。另外,您所说的“从自己的视点出发”,我是这样看的,这是我们人类的局限,我们观察世界、思考生活,永远只能“从自己的视点出发”,我不可能写出真正从您的视点出发的任何文字,我们小说家在书中依凭的任何一个人物,他所思所看,说到底,都是作者所思所看。当我们说我们理解另外一个人,事实上,那个人“只能是我们理解的那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作家的自传。当然,我们会在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经历,从而增加作品的生活质感和可信度。这时,如果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脉络和作者贴得近,如您所说带有自传色彩,处理起来会得心应手许多。这也是我选取近乎自传的叙事策略的缘故。
鲍 十:另外我注意到,中外许多优秀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与作家本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都带有自传的色彩,或者说,都会回到自身。比如曹雪芹与《红楼梦》,普鲁斯特与《追忆似水年华》,萧红与《呼兰河传》。包括前几年获得诺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她作品的自传色彩非常浓厚。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的说法?
王十月:我完全同意您的这个说法,因为这样会让作家在写作时变得更有底气,更自信。
鲍 十:作品中的王端午,与你个人生活的重合度有多高?
王十月:我是有意让读者认为王端午就是王十月,有意让读者将这部书当我的自传来看,这也是写作策略。事实上,重叠度最高的,是我和王端午的生命大轨迹,比如我们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比如都是初中毕业走上社会,都是先务农后打工,都爱阅读……就是说,二者生活的场景是高度重叠的,这样能保证我在写作时,大到当时的社会风貌,小到生活细节的把握会更准确。至于王端午干过的具体的事,只有割芦苇和被卖猪仔是我真实的体验。但王端午这个人的内心就是我的内心,王端午所有的不安与不甘就是我的不安与不甘,他的灵魂拉锯,就是我的灵魂拉锯。因此也可以说,王端午就是我。
鲍 十: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王端午这个人物形象。不用说,王端午是一个具有新鲜身份的人物,他是当年千万打工者的一个缩影或一个代表。而且,你写出了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写出了一个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发展史(权且这么说),这非常难得。
王十月:感谢您这样看,其实书出来后,收到的评价是两极的,有些人会说王端午塑造得很真实,甚至有读者说他就是王端午;也有人说王端午这个人太奇怪了,显得矫情而且虚假。我就想到,当年陀翁写《白痴》时,也有许多人批评梅什金公爵太过完美,但是陀翁说,他正是看到了俄罗斯的灵魂中缺失了梅什金公爵,于是才塑造出这样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来拯救俄罗斯的灵魂。
鲍 十: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王端午的成长,看到了他的懵懂、困惑、彷徨、挣扎、负罪感、流浪、痛苦、绝望、希望、倔强、不屈服等等。就像前边说的,这些基本都来自你本人的亲身体验。而这样的生活体验,是很多作家所没有的。所幸你没有回避自己的生活,将其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单从这一点来说,就非常有价值。我想请你讲一讲,在塑造王端午这个人物时,你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
王十月:很奇怪,过去我写小说,会被小说中的人物带着走,跟着一起大悲大喜,但写这部书时,内心格外平静,但写到伤心处,我会悲伤,会流泪,不过我的情绪很稳定。对王端午也好,对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也好,我心里怀着的是巨大的爱。这是从前写作中所没有的。我也不知道,将来的写作中,是否还能找到这样独特的心境。
鲍 十:这部作品写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有近五十年的时间跨度。应该说,这五十年的生活非常丰富,非常富有戏剧性,可说是前所未见的。包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前几年有朋友送给我一本书叫《八十年代》,是一本访谈录,共同的话题是谈论自己对上世纪80年代的印象和感受,但是每个人的看法又不尽相同。这就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便是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人,在面对同一事物时,也会因为各种因素,比如个人立场、认知能力、所处的地位、从事的职业、观察的角度、内心的企图等等不同,产生不同的看法,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就好比作家如何认识和书写生活,以及如何认识和书写历史。这样,也使得作家的写作有了分野。就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你的见解。
王十月:其实在写这部书时,我并没有特别去写这半个世纪中的社会变迁,或者说,我有意淡化这五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只是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草蛇灰线,偶尔点上一两笔。这与我写这部书的初衷相关,我并不想将这部书写成一部宏大的社会发展简史,不想将这部书写成中国近五十年来社会发展大事记,不想将这部书写成时代众生相和百科全书,也不想仅仅是通过这部书来唤醒人们的记忆……当然,很多作家在这样做,而且,这样的写作有重大的意义,也出现了一些好作品。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书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执念。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的确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绝对是人类社会的奇迹,而这一奇迹背后有太多可供书写的空间。中国作家想正面强攻这个时代,从而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不仅中国作家,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也是这一类的写作,通过一个人物带出一群人物的命运,写出伊斯坦布尔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沧海桑田。我写这部书,一是自觉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份雄心和心力来完成如此宏伟的作品,二是并不想用不多的时间来做这样的记录,因为这样的记录并不是非我不可的,别的作家也可以做。80年代固然重要,可以说,是80年代塑造了我的价值观。但正如您所说的,同样的一个客观的80年代摆在那里,我们并不能真正做到客观书写80年代。而且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一个真正客观的世界,从量子物理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因为观察者的存在而存在的。同样的80年代,鲍十老师您的80年代,不能等同于我的80年代,也不能等同于您同龄人的80年代。这正是您前面所说的,所有的书写“都是从自己的视点出发的”。但我在这部书中依然写了80年代、写了打工、写了下岗,写了一个人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这是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建筑一座大厦所用的砖、石、水泥、钢筋、玻璃……但我写这部书,并不是为了展示这些砖、石、水泥、钢筋、玻璃,而是借助这些材料来构建我的大厦。我想,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小说家写生活,要指向灵魂才有意义
鲍 十:在《不舍昼夜》中,你写到了很多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日常生活中,这是自然现象,但在文学作品中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是被作者寄予了某种意义,或者说,一定是作者想借此表达些什么。你能谈一下这个问题么?
王十月:感谢您透过砖、石、水泥、钢筋、玻璃,谈到了大厦。这部书的大厦,或者说我写作这部书的意图,我真正在这部书里尽全力而为之的一件事,又或者说,我真正留给这个世界的,并不是时代变迁、打工浪潮,我所想写的,在“后记或序章”中有提到。因此,我特别想和您分享我在“后记或序章”中隐藏着的秘密。这短短千余字,我并没有依惯例叫“后记”,因为后记代表结束,而我用了“后记或序章”,隐含着结束并不是结束,结束是新的开始;死也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死,死可能是新的开端。“后记或序章”最后两句是:“所有过往,皆为序章。生死死生,不舍昼夜。”我还引用了《权力的游戏》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凡人皆有一死,凡人皆须侍奉。”是的,因为我真切感受到了“凡人皆有一死”,于是,我想用我的文字,来侍奉这些平凡的人。这部书,写的就是两个字,一个字叫“死”,一个字叫“生”。或者说,我写的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生而为人,我们如何成为人。成为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活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成为人。而人的悖论是,人只有在死后才能确认他这辈子是否成为人。我们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说,活在当下、眼前、这一刻,我们是个人,但谁也不能保证,明天我们不会异化为兽。王端午在没偷李文艳的钱包与证件之前,他以为他是人,当他将罪恶之手伸向李文艳时,作为人的王端午死了。他没有成为人,但他后来继续活着,依然有可能成为人,他终于在临死之前,完成了成为人的仪式。因此,这部书是王端午成为人的历史。但这成为人的历史是何其艰难,就像不断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这部书就写了两个字,一个字是“死”,另一个字是“生”,那么,这本书如此郑重庄严地写死,只是为了写亡吗?当然不是。孔夫子说,未知死,焉知生?写死只是手段,写生才是目的。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写的是既然人生而会死,我们该如何生。于是我塑造了王端午这样一个不彻底的人,让他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让他穷其一生,引领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鲍 十:讲得非常好。我想我理解了你的想法。我现在忽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直面生活。我觉得,《不舍昼夜》就直面了许多东西,不管怎么说,文学有它的根本,这个根本没有丢,这个根本也不能丢。
王十月:直面人生,不能是大而不当的空话,不能是半天云里的务虚,真正的哲学,一定是既直指心灵,又依托俗世的。我记得谢有顺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就叫《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小说家写生活,要指向灵魂才有意义,写灵魂,必得依托实在的人生,才有说服力。我想,这就是您所说的根本。这是文学的根本,也是做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