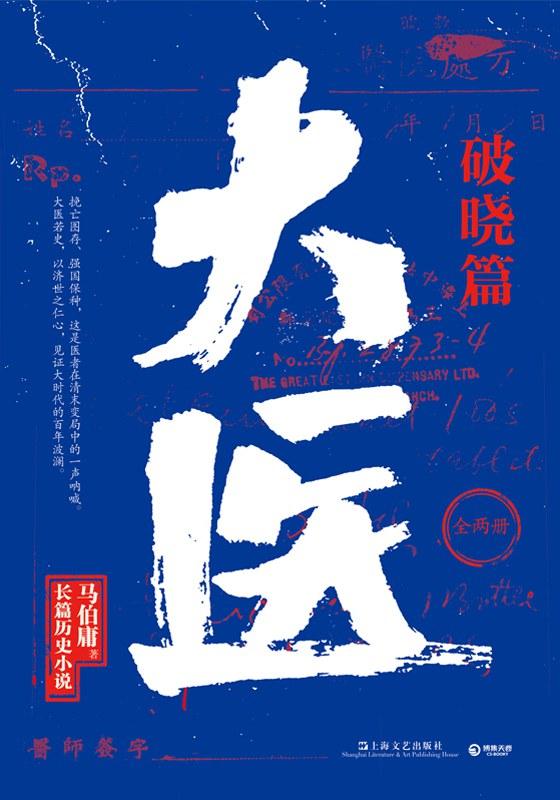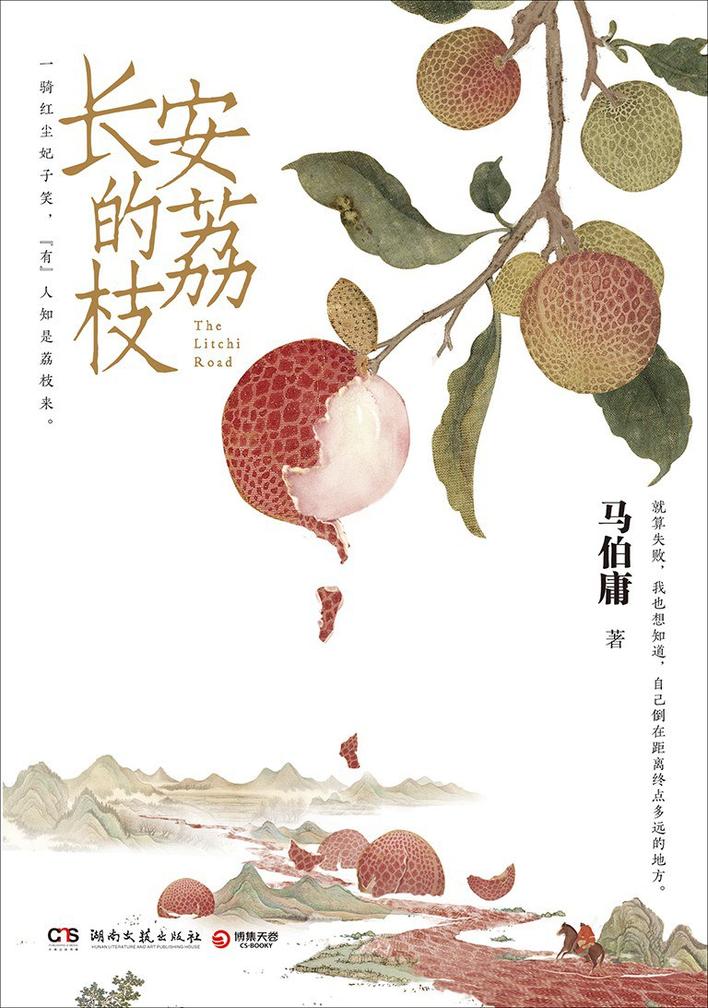满族作家马伯庸擅长以微观的历史视角重新架构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历史的裂隙中寻惊雷、见温度。2024年,他的长篇小说《大医》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虽然这部小说在题材和写法上,看似与他在《风起陇西》《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等作品中惯常偏爱的古代题材和悬疑风格不同,但却可以说更鲜明地整合和总结了他在此前创作中形成的文学价值观,那就是不仅仅徘徊于时间、地理、族属等表面向度,更在平等的叙事视野中拉平个体与宏大叙事之间的价值鸿沟,在日常生命体验中重构宏大叙事。从《风起陇西》《长安十二时辰》到《大医》,再到新作《食南之徒》,我们可以对马伯庸的整体创作风格、文化特征和文学史观进行一次全面梳理。
文化乡愁和人性底色:民族融合的内在驱动力
纵观马伯庸的历史题材创作,可以发现他最擅长写民族大融合时期。从《风起陇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的天宝大唐,再到《食南之徒》的汉武帝时期,他对民族大融合的内在逻辑有其独到的观察视角和叙事切入点。
《食南之徒》看似在写一个“吃货”因美食阴差阳错化解朝堂阴谋的故事,实则是从“同食同种”这一最本能性的角度,解答了中华民族缘何成为一个共同体,对民族融合的内在驱动力进行了重新叙述。《食南之徒》的故事基础来自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讲的是汉武帝收复南越国的故事。而写作这个故事的“由头”,来自博物馆里的一次意外发现:他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看到两枚从南越王宫水井里出土的竹简,上书“壶枣一木”,但南方不产枣树,枣从哪里来呢?原来南越王赵佗本是北方人,秦末大乱时南渡立国,后思乡心切,于是在南方种植北方家乡的枣树,以解乡愁。食物是最公共也最私密的事情,相同的饮食基础、趋同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故乡的食物满足的不仅是口腹之欲,更联结着过去和未来。食物的乡愁,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根、最初的源。
事实上,赵佗一生一心向汉,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收复南越,吃货唐蒙通过“蜀枸酱”探破赵佗被害背后的秘辛只是文本的偶然,背后中原与南越之间无法割舍的情感勾连、共通的生活方式和恒久的文化乡愁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向心力,才是历史的必然。
从《长安的荔枝》到《食南之徒》,马伯庸写食物,归根结底写的是文化乡愁,是人性最本真层面的相通性。无论是万人之上的太子朱瞻基,还是长安末流小吏李善德,甚至是已经成仙的太白金星李长庚,面对他们天殊地别的身份差异,作者有一双善于发现其共通的生命处境的眼睛。尤其是在处理历史大进程冲突点时,马伯庸从未粗暴地归因于差异性和仇恨对立,而是在不同族别的共同遭遇中发现和珍视其共通性——随着《长安十二时辰》中袭击长安城的阴谋被层层拨开,读者发现张小敬、突厥狼卫曹破延、“蚍蜉”首领龙波的命运和经历竟然如此相似,他们的悲剧都共同捆绑于边境无休止的战争之上。当十二时辰落幕,原本处于对立的这些人物在精神空间上却完成了一场惺惺相惜的相互救赎,而他们人性深处的情感底色和对和平的共同追求,正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
微观历史视角下的共同价值书写
马伯庸的作品擅长以独特新奇的视角重构一段熟悉的历史叙事,从而打破常识性的认知。无论是从太白金星视角重新理解《西游记》的《太白金星有点烦》,还是从底层小卒视角重新审视大唐盛衰转变的《长安十二时辰》,“去中心化”的视角一直贯穿着马伯庸的创作。他似乎一直在试图解构某种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在《两京十五日》中,这种对二元对立的解构被推向极致,大明太子朱瞻基在一场阴错阳差之下不得不隐身于普通人中完成一场千里狂奔,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大运河上的纤夫二者间的视角被拉平,皇权与民意、崇高与卑微、宏大与日常,都被置于一个公允的文本空间之中。与《明朝那些事儿》不同的是,历史人物在《两京十五日》中并没有获得比虚构人物更大的文本优先级,反而是朱瞻基常常受制于主观成见,或被现实迷雾所蒙蔽。与那些虚构的小人物相比,他反而成为了历史的近视者或盲视者。马伯庸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去除了很多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书写普遍存在的“虚构焦虑”,当然也没有沦为“戏说”,最终又回到了历史主线上。
《大医》与其说是“去中心化”,不如称其为对“多中心化”叙述视角的一种尝试。马伯庸几乎彻底抛开历史大事件的中心人物,故事中没有绝对的主角,只从人“向死而生”的本能出发,珍视每一个小人物,经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最终抵达人性的深处。
虽然马伯庸的创作一直以来并没有浓烈的民族风格,但他擅长从边缘突入、“去中心化”的叙述视角,或许与他的身份意识和独特的民族视角分不开。在文学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写湘西的沈从文,还是写《正红旗下》的老舍,等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似乎对不同形态故事背后普遍和共同的人性更有感知力,更有可能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深入探索和展现人类最深层次的共通情感和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作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挖掘既是独到深刻的,又是极具总体性和普遍性的。
纵观《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三大史诗,其中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早已超越了族别差异,可见民族文学从其本源上就是紧紧围绕着天下、仁爱、责任这些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而衍生的。这种对人类普遍情感的深刻洞察,在《大医》中得到了集中呈现。红十字会医生“人道、公正、中立”、不分阵营、一体救护的原则,正是人类共同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正是有赖于此,大医们才得以守护了国运走向,守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大医》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文学,超越了族别、国别和人种的差异,成为观照人类共同命运的寓言诗,这正是《大医》最可贵之处。
而到了《食南之徒》,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又通过“食物”这一更日常的视角得以呈现——从生命到生活,在超越特定的民族性之后,反而更加深入地抵达了中华民族总体性的共同记忆和共同价值。
个体与民族、文学与生命的辩证互动
《大医》并不是马伯庸第一次触及医者主题,出版于2017年的《白蛇闻疾录》虽然基于玄幻想象,但“医者—瘟疫—苍生”的关系却是对社会关系的投射,构建消弭瘟疫、人妖和谐的幻想世界,事实上也是一种隐喻。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叙述中,医者常常与“救国”“济世”的宏大理想紧密联系,传统医学也不仅仅是治疗之“术”,而是涵盖中国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死观的综合之“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和救死扶伤的身份想象,使得“医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自然地承担起了匡时救世的“英雄”隐喻。尤其是晚清以来,面对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文学叙述更加强化了对医者的政治和社会期待,将其作为承载中国传统“上医治国”理想的化身。晚清刘鹗的《老残游记》便将诊断千疮百孔的古老中国的“病相”和“病因”的使命赋予了主人公游医老残,他代表了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现代文明审视和改造中国的期待;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中,领导了东北鼠疫防控、使人类避免了一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的伍连德,也同样遏制了日俄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此呈现了其“国医”的双重身份和使命。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中,医者所诊治的对象既是具体的,更是象征性、寓言性和文化性的。
《大医》是马伯庸首次触及晚清民国这一时段的历史。在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等作家“弃医从文”的故事太过为人熟知,因此他们“从文”之前的救国理想常常为文学史所忽略,《大医》填补的恰恰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空白。文学与医学最根本的关注点都在于人和生命,二者底层逻辑的共通性正是其常常被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不少人认为鲁迅从“择医”到“从文”的过程似乎暗含了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实则不然,医学在生命政治层面对民族的现代性转型意义重大,精神与肉体的现代性也必然是同源同构的。鲁迅从未否认过医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必要性,更何况后者的本体性地位无可取代——“家国”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由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方三响、孙希、姚英子这三个出身各异的青年医生的成长史,正是对从晚清到新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成长史的一种隐喻。
文学中的疾病叙事常常与民族的自新时刻相联系,薄伽丘的《十日谈》、笛福的《瘟疫年记事》、加缪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都诞生于人类与未知的死亡恐惧相抗衡的语境之下,动荡背景下的瘟疫和疾病正是民族苦难和时代恶涛汹涌的隐喻。然而疾病、瘟疫、战争这些毁灭性的语境,也正是重新积蓄“生”的力量的出口。
可以说,医者与社会之间见微知著的隐喻关系,完美契合了马伯庸一贯善用的微观视角,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显微镜下的大明》。何为“显微镜”?即是“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找到去除基层社会积弊的关键所在”——正是在一次次对历史的“显微”中,一个个小人物承载起民族自新的政治与文化使命,文本得以从对个体生命的观照抵达宏大叙事,最终实现了个体与民族、文学与生命的辩证与互动。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