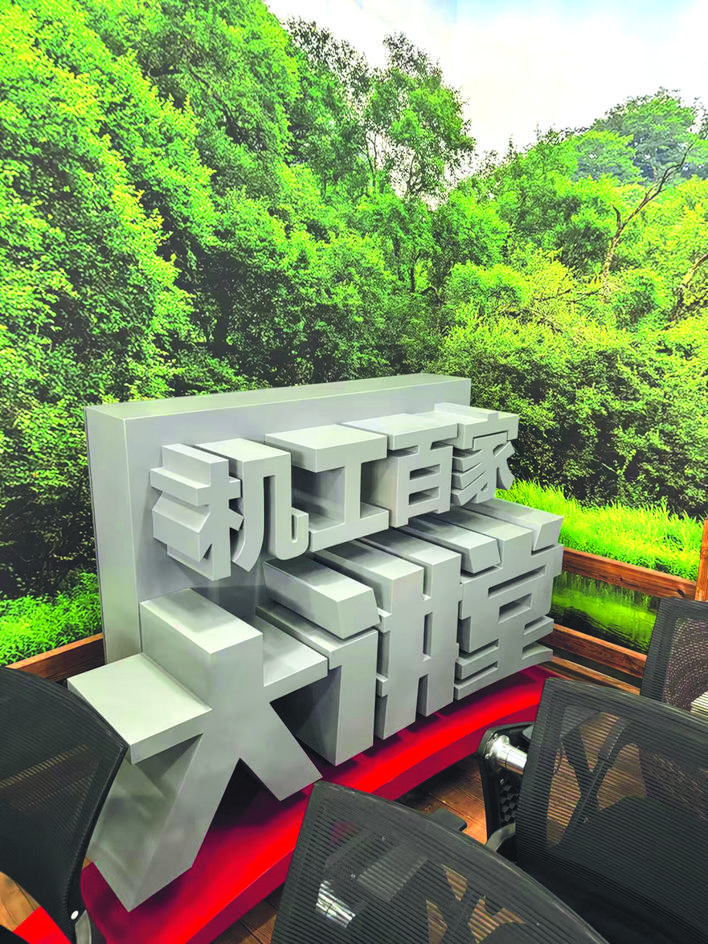2024年的出版形势略显不好,6至8月,我这个很少外出调研的人陆续到北京、浙江、山东、上海等地进行调研。其实我以前不太喜欢调研,总以为自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从这三个月的调研经历和结果来看,这个想法暴露了我的自大。
我喜欢悄悄地来去,不喜欢大张旗鼓地发函、接站、制定接待方案,只想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来获得其他出版单位的宝贵经验。另外,我组织的调研通常只带上一到两人,最多不超过三人。因为我觉得,人数众多的调研向来都是浪费时间的行为艺术:一行人跑到别的单位去,双方一本正经地在自己对应的席卡前坐下,照本宣科地朗读本单位早已准备好的书面材料。只要是能形成书面资料的“经验”和“做法”,“秀才”必定在万里之外都知道,不如不去。而我则喜欢走遍调研单位的每一个角落,走进每一个编辑部,目光无漏地观察一片纸、一件物,与大部分新老朋友面对面无障碍地长谈。不过,我很担心本文在《文艺报》发表后,今后如想到别的出版单位“调研”,极有可能存在被拒的“风险”。
调研第一站:
凤凰汉竹、凤凰含章和紫云文心
6月初,我与凤凰科技出版社原总编辑郁宝平决定对三家民营公司性质的单位进行调研,一家是凤凰含章,一家是凤凰汉竹(这两家都是凤凰科技出版社的子公司),另一家则是曾和我过去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进行过长期合作的紫云文心公司。调研的目的是想看看民营文化公司究竟如何看待目前的出版形势,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克服目前的困难。这三家公司做的图书质量精良,市场化能力很强。经过与他们的深入交流,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他们对于目前的出版现状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市场增长困难,但三家公司本身都还在进步和发展。
第二,他们认为无论是整个出版市场还是他们自己推出的新书都在变少。三家公司的三位老总都非常专业,眼光独特,一致认为新书变少是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第三,一大批出版单位都在老书新做,尤其在大量出版公版书,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图书的价格。因为减少了10%左右的版税,于是价格较低,版本众多。出版者的竞争变成了价格竞争。2024年8月,我曾到山东参加第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看到好多出版单位都在以8元、10元一本地低价卖书。低价公版书使价格战似乎没了底线。
第四,前两年靠抖音等众多新媒体平台拉动销量的方式,如今也变得疲软。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一点,但乐观地认为将来会有新的渠道出现,因为图书的文化消费需求不可能急剧下降,而现在的无序和低价竞争不过是一时的混乱。
我在凤凰传媒曾经反复强调,现在的形势是图书印刷之前的逻辑没有变,而图书一旦离开印刷厂之后的逻辑完全变了,变得我们无法认识、无法适应。出版的尾端——渠道不断发生变革,而这几年引导变革的是抖音等,但其实抖音等平台的影响力也在衰减。
第五,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对凤凰所做不足的批评,略去不表。
第六,凤凰科技出版社的两家子公司都表示,他们之所以做得好,在于其母公司凤凰科技出版社的管理与品牌。我十分奇怪的是,凤凰传媒在北京设立的公司好像都不太好,但凤凰汉竹和凤凰含章是两个例外。他们感叹,在凤凰科技出版社的领导和管理下,公司才得以获得稳定发展。
调研第二站: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7月,我和译林出版社的姚燚到中信出版集团进行调研,与中信出版集团的执行总编辑楚尘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进行了一次关于出版的长谈,这次我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中信出版发展不错。中信出版的长项在于过去所出版的政治经济图书持续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等。这几年虽然也面临一些困难,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经营能力和管理机制,根本在选题的局限——中信出版集团那些年曾推出的轰轰烈烈的图书,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第二,中信出版做了一大批精品图书,特别令我惊叹的是中信童书的推出。中信几年前迅速进入童书市场,势头发展迅猛,他们认为,童书是图书出版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值得未来大力开拓的新板块。
第三,中信在做书的同时,大力从事知识服务、知识生产。中信对公共企业、公共单位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他们以中信出版为品牌,带动头部产品的销售和头部作者的运营,能够将知识服务迅速推向政府和企业。在我看来,阅读中信图书的人,大多都是有思想的人,其中一部分集中在党政机关和优势企业里。中信将名家名人著作“推送”给企业家、政治家、知识分子,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们所进行的知识分享,规模十分之大。
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组织的品牌论坛上,我曾询问坐在我身边的中信出版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炜如何看待出版行业今年的变化、如何从单做出版向做出版与知识服务融合发展,他说中信在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品牌影响力大,所以图书出版和人脉资源便得以相互借力,相互衬托。
调研第三站:机械工业出版社
我还去过机械工业出版社(以下简称“机工社”)调研,那次是我和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袁楠一起去的。我们几乎走遍了机工社所有的编辑部、发行部、营销部以及新媒体中心的每一个角落。
首先,我对机工社的规模之大印象深刻,他们不但有三幢大厦,还有一家相当不错的书店。员工大概有两千到三千人。前年底北京开卷的总经理蒋艳萍曾和我谈起,中央级大出版社很能抵抗风险。我当时不太能理解,因为我对中央级大出版社了解不多,只知道优劣强弱大不相同。到机工社实地调研后,对蒋总所言才渐次明晰。从规模来看,凤凰传媒一个出版社最多不到300人,我们如果有一个500人的出版社,现在的气势就难以想象。译林出版社成立时只有7到8人,现在有200多人,用了30年人数翻了30倍。
第二,员工规模、生产规模、产品规模是相互促进和制约的,相辅相成。机工社人员多、规模大,决定了其出版的图书数量众多,过去每年图书出版数量好像都在3000种左右。相比较而言,凤凰传媒的年出书量是5000余种,但我们有8家图书出版单位,他们的出书量虽然是我们的一半,但远远超过凤凰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出书规模。
机工社还是一个学术期刊的重镇,拥有几十份专业的刊物。这些刊物在业内十分专业、权威。他们出版的期刊数量多、质量高,在专业范围内十分出色。
除了规模大外,板块强也是核心竞争力。大而不强的出版集团和单体出版社其实并不少,但机工社的三个出版板块都很强势。第一个是高校教材板块,其作者非常权威。机工社的职教教材做得特别好。我本来认为我们的凤凰职业教育出版做得不错,但和机工社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有很大差距。我有时候担心,未来凤凰传媒的一流作者会枯竭,并一直在为发现新的作者而不懈努力。我们举办了5次作者年会,虽然在国内属于创举,在赢得优质作者方面颇有成就,但我认为机工社的一流作者50年内都不会枯竭。据介绍,33%的院士都曾在那里出书。我清晰地记得去调研时看到出版社办公大厅有一面作者墙,上面有60个院士作者的照片。此外,江苏很多职教教师和名校名专业教授,也是他们的重要作者。我回来后就常想,我们在职业教材出版这方面,要用什么力量与机工社竞争。
第三,我们深入了解了机工社的大众出版。众所周知,机工社主要从事大众出版的公司是华章分社。过去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做社长时曾开拓过管理培训类的出版板块,经常听编辑说起华章分社。华章分社的副总经理佘广在给我们介绍大众出版产品线时,读者很难想象我当时的敬佩和吃惊。佘广说,机工社的图书在各个不同时期都在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他们将服务国家建设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科技强国、商业兴国和温暖中国阶段。佘总的表达极类似于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在我看来,他们的气概、理念和价值观是相通的。
机工社为科教兴国服务,出版了大量科技类图书。他们出了哪些书?我回忆了一下并查阅了手机所拍的照片,有《机电词典》《电子技术》《液压与汽动技术》《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大致所有科技领域的权威著作他们都出版过。延续几十年的优秀传统代代相传,今天的《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等国内原创和国外最新引进的著作,他们基本都未忽略,并已出版。
当然,出版是一回事,发行得好又是另一回事,好选题+好发行,才能实现出版的商业闭环,才能实现出版的价值。这一点,机工社的出版与发行真可谓相得益彰。如《电力电子技术》一书发行196万册,《电子机械工程设计手册》和《机械工程手册》两本各发行几百万册。《机电工程辞典》英汉对照版发行1.6万册,德汉对照版发行1万册,每本售价都达几百元。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机工社为推动经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从此开始,机工社出版了大量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方面的著作,华章公司在这一领域出版的图书也是琳琅满目,令人啧啧称赞。
据我的观察思考,机工社出版的这类图书大都有10到20年以上的生命周期。除了企业管理领域的众多图书之外,出版社独有的两大名人著作发行量更是巨大。一个是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的经典名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该书目前发行已达400万册。还有稻盛和夫的著作也是在机工社出版,发行数量也巨大。这两位作者著作在国内的出版发行,比在他们本国都做得更好。还有一本斯蒂芬·A.罗斯的《公司理财》也值得一提,这本书发行了77万册,销售码洋7400万。西方经济学、投资学、消费者行为学……机工社在这些领域的图书经常发行达百万册以上。
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便是温暖中国。这一阶段,机工社出版了大量的心理励志类图书,如荣格的《红书》发行量高达20万册。另一本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发行量达280万册,仅此一本书码洋就有1.54亿元,“勇气系列”还有很多,如“小孩的勇气”“成人的勇气”“恋爱的勇气”等。
第四,营销能力强大。华章公司的营销人员非常多,营销能力非常强,其营销人数占单位人数的七分之一。凤凰传媒各出版单位的营销人员数量基本达不到这一比例,我觉得凤凰传媒的营销能力还是有点弱,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短板。
第五,极其专业的管理者与极其专业的编辑出版发行审读人员。机工社的领导非常专业,印象中接待我们的是两位副社长陈海娟、时静。我之所以要到每个编辑部去看,是想看看其他员工的工作状态,判断一下他们到底是带着温暖的心情在这个单位工作,还是牢骚满腹地为完成任务而坐在那里打发时间。当然,员工的表情就会说话,他们的业绩也清晰地呈现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据我所见,那里没有什么离奇古怪的人,个个精神状态都非常饱满,这都得益于很好的企业文化。我曾收到一个朋友的微信,非常感慨。他说:“你看一个单位是不是好,是不是适合你,主要看两点。第一点,在这个单位里面,跟你常接触的那些人是不是对你非常友好,是不是值得你尊重,你是不是乐于和他做同事。第二点,你在这个单位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看看那些很快被提拔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如果那些拿着很高薪水和很快被提拔的人都是你认为很糟糕的人,说明你不适合在这个单位,你要尽早离开。”我读到这条微信后很受启发。人的管理很重要,各个出版单位的社长和总编辑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并以此明志做事。引进一个人,第一要心理健康正常,第二水平专业要高。同时,干部要像员工一样努力工作。这便是一个健康出版单位的管理文化。
第六,我在调研中看到机工社的数字创新部开发了一套作者系统,这是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每一个作者都可以登录这个系统,假如我是机工社的作者,我就可以在作者系统中查到我的哪本书什么时候出版,哪些编辑参与了书的编辑、发行、宣传,这些书读者有什么评价,这个月销量多少,目前总销量多少,自己将在哪天参加什么会议,参加过哪些视频活动、线上课、作者见面会……机工社的作者系统把出版社的作者和书都牢牢维系在这个系统里。这个系统做得相当不错。当然,要做到并不断完善这个系统,必须有足够多的作者。其实这个系统并不复杂,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之前并没有想到。
还有,就是机工社大大小小的直播间令我大长见识。他们大概有15到20个设备非常完备的直播间,有些甚至比很多报社、电视台的都好。其中,小型直播间有5到6个平方米,大的大概有100到200平方米,可容纳几十人甚至数百人。在这个可容纳数百人的直播间里,各种各样的机械长臂灵活运转,编辑营销人员每天都在直播。我调研机工社后加了他们的微信,佘广副总的微信从早到晚、从周一到周末似乎都在不停地直播。出版的打法变了,机工社真的适应了新的打法,在地面渠道之外开设出了新的营销手段和渠道。
从这方面来看,凤凰传媒在2019年较早地推动了新媒体营销,当时像我们这样走在前面的出版集团还不多。机工社的情况与我们相同,他们是在疫情之前启动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事物微小的变化,看到了实体店的危机。此后三年,机工社的网络直播和直播带货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版业绩不但未受影响,反而不断增长,这正是见微知著的智慧。
第七,机工社拥有全国有名的馆配公司,他们的馆配公司全国排名第三,拥有全国各地出版单位的图书,品种丰富,几乎代理了全国所有出版单位的产品,特别是科技类的图书。
调研第四站:博集天卷
我和姚燚也到博集天卷进行了调研,与黄隽青总经理进行了深入沟通。按照习惯,我也到每个部门都走了一圈,同编辑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发行人员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讨论,得到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认为,目前出版事业需要主管部门的呵护,图书市场需要激活。如果坊间有十本超级畅销书出版,引起全社会重视、关注并形成一个现象,那一定会引起阅读潮。当整个社会一直有好书不断出版,带领读者关注文化、思想、科技的前沿问题,那就不愁图书市场不兴旺发达。
第二,博集天卷遇到的盗版非常厉害。1990年代出版单位拼命地防盗版,但后来有了电商不怎么需要防盗版了,因为电商渠道网店就那么几家,能够控制,可如今又要日夜防盗版,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平台上常有店铺销售盗版。防盗版、打盗版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影视难做,风险巨大。博集天卷曾从众地投资影视拍摄,但赶上了末班车。谈起影视,作为优秀的出版人黄总不住地摇头。黄隽青是南京人,和我一样毕业于南京大学,又常回南京,早年曾和凤凰出版同仁有过多次合作,因此对凤凰非常了解。黄总真诚地羡慕凤凰,认为我们有一支由众多优秀职业出版人组成的团队。我内心很高兴,但口头十分谦虚。我认为目前国内职业出版人队伍发展不平衡,但凤凰团队的理念、状态、水平和精神都不比人家差,这是我内心引以为豪的。
以上就是我2024年调研得出的一些结论。另外,我还去了山东济南,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书展,详细看了许多展馆,比较了他们的产品。在炎炎夏日去杭州和浙江同行进行交流,老友叶国斌和邹亮、赵波、况正兵等在荷花满池的西湖边接待了我们。后来,我也在上海书展期间逗留了很长时间,几乎看遍了各个展馆的图书。还以评委的身份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逗留时间不长,但与南方传媒分管出版的副总肖风华进行了深入交流。肖总一位在西安做数字出版的朋友有一句话对我震动极大。他曾长期做教育出版,现在做数字出版很成功,他说,今后AI时代,最先被冲击的板块是教育出版,因为教育出版总体是重复和提高,不追求多样却归结统一的答案。这句话被我牢牢记在心里。10月,我还应邀前往云南出版集团,忝列为他们的专家智库成员,与集团领导和各出版社的社长们进行了极其真诚的交流。当然,我的“增值”收获是把他们迅速拉进了《文艺报》“编辑故事”群,他们将成为未来这一专栏的重要作者。
调研的结论已在上文逐一写出,再写一下总体但简单的结论。第一,总体而言,首先我感觉形势不太好,但仍然有做得好的出版人。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做得好,形势不好的时候做得更好的,才是真正有实力的出版人。第二,要心无旁骛把出版做好,不要有歪心思,如此,才可能把出版做好。第三,现在如果想要做好出版,需要比以前花更多功夫、更多精力。第四,我认为小规模的出版公司,特别是只盯着几个作者的出版单位是危险的,规模还是要大,东方不亮西方亮。第五,专业化很重要,先是专业,然后是市场化。未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还是愿意稍微回顾总结一下这一年的调研,也算是一份特别的调研报告,希望能对自己和同行们有所启发。
(作者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