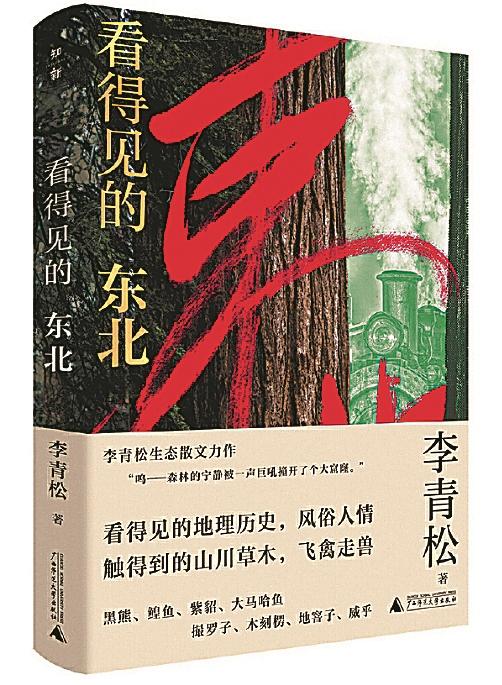□汪树东
李青松坚持生态文学创作长达30余年,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领域中重要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家。他从当《中国林业报》记者开始,就颇为关注中国的森林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到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及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工作后,他更关注森林修复和森林保护对国内生态的全局影响,并在职业生涯中,踏访全国山河,调查生态现状,寻访引人入胜的各地风物。他的《遥远的虎啸》《一种精神》《茶油时代》《开国林垦部长》《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等报告文学作品呈现了我国林业生态建设事业中的各种风景,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重要收获。
近年来,李青松有意在纪实笔法中更多地融入个人的独特情感和对生态问题的长久感悟,创作了不少新鲜的生态文学作品。《万物笔记》《大地伦理》《相信自然》《北京的山》等力作连续推出,社会影响卓然不群。新作《看得见的东北》聚焦于告别伐木时代后的东北林区和森林生态,书写东北特有的地方风物,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伦理,是对当下生态文学热潮的一种积极回应。
首先灌注于作品中的是尊重生命、尊重自然、肯定生态整体观的生态伦理。李青松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告别了伐木时代,该怎样重新认识自然?该怎样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本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的确,李青松的生态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展开,他的生态伦理既来自利奥波德、梭罗等先贤的哲理启发,也来自于他长期的野外调查与观察反思。他在《鳇鱼圈》中考察清朝开始的东北鳇鱼贡制度,在《贡貂》中探究清朝对东北紫貂的捕杀,在《黑熊:蹲仓叫仓揣仓》中谈及对黑熊的猎杀,在《大马哈鱼》中书写大马哈鱼的悲壮洄游等,都流露出对这些东北特有的野生动物的关注和尊重,对它们遭受的灭绝之悲剧和猎捕的惨痛表达出了极大的批判与忧愤。李青松也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灵性,例如在《红松之美》中对东北红松的勇气、精神和力量的礼赞。当然,更为令人尊敬的是,李青松始终坚持从生态整体观角度来审视东北的森林。在《哈拉哈河》中,李青松既写出了哈拉哈河流域生态的整体性,也强调哈拉哈河和整个地球生态之间的微妙联系。在《大马哈鱼》中,李青松更是关注通过大哈马鱼而达成的海洋生态与陆地生态之间交互共生的宏大协奏曲。在《大兴安岭笔记》中,李青松非常关注菌类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独特作用,“没有蘑菇等菌类,森林中倒下的枯树就会层层堆起;没有蘑菇等菌类,森林里的生命链条就会断掉,那张我们看不见的‘生命之网’就会脱落。”李青松自觉地以生命之网的生态整体观来审视自然万物与人类。这种生态伦理赋予了《看得见的东北》纯正卓然的精神底色。
其次,李青松的《看得见的东北》展示了对东北林区生态博物学式的审美建构。李青松的生态文学作品是具有相当大的知识密度的。例如他的《哈拉哈河》写的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一条河,把历史与现实熔于一炉,把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生态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活画出一条北方河流的全貌,洋溢着生态整体观的盎然诗意。他在文章中以壮丽的笔触描绘了哈拉哈河边火山岩上长出来的森林,精确地呈现了花尾榛鸡、黑熊、松鼠、哲罗鱼等鸟兽虫鱼的生活习性与生态位,同时穿插叙述了哈拉哈河上的打鱼人、诺门罕战役对当地生态的破坏、日本人对阿尔山林区的生态破坏以及阿尔山林务分局的伐木活动和封山育林。至于《鳇鱼圈》《大马哈鱼》《贡貂》《红松之美》等篇章更是展开了魏紫姚黄的生态博物学的审美建构。他在《红松之美》中这样描绘红松林的烟雾:“红松原始林的上空,常常弥漫着黄色的烟雾,像是撑开的宽阔的黄色大伞,把整个林子罩住了。形成这种黄色烟雾的,是千万棵红色的花粉。高大的红松上,开着无数多雌花和雄花,雌花在花冠,雄花在雌花的下方。六月下旬,花开放了,黄色的雄花花粉飘向空中,每一粒小极了的花粉上都有两只小小的鼓鼓的气囊,所以它比空气还轻,能飘到树冠去同雌花结合,能飘到林冠上空,随着气流在那里飘着、流着。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黄色的烟雾。”这是多么精确、神奇而又美丽的生态画卷啊!生态博物学的知识视野保证了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品的科学性,也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自然历史的好奇心,拓展出一种生态文学作品独有的审美体验。
此外,李青松也试图在《看得见的东北》中的不少篇章里探索生态文学的新的艺术路径。例如《哈拉哈河》以一条河流的流淌为线索,相继呈现了与此流域生态有关的各种野生动植物乃至人类历史、渔猎活动,最后上升到地球生态的整体观照中。此种结构堪称生态散文领域里的一种独创,将纪实与抒情共熔于一炉。《大马哈鱼》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大马哈鱼的历史、习性、生态位和赫哲族渔民黑嘎爹的坎坷命运,以及对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坚守,和年轻一辈黑嘎、冬妮娅夫妻的乡村振兴事业结合在一起。在真切地勾勒出大马哈鱼这个神奇物种的同时,也展现了赫哲人的历史和现实,礼赞了绵绵不绝的宇宙大生命。小说和散文的笔法相融,相得益彰。而《大兴安岭笔记》要写大兴安岭林区告别伐木时代后的林区生活和生态景观,作者集中呈现了大兴安岭林区深处的小镇塔尔气、绰尔林业局河中林场的蘑菇圈、绰尔大峡谷、敖尼尔林场,最后以林中小语的生态感悟结束全文,突出了生态文学的地方感、空间感,特色鲜明醒目。
尤其难得的是,李青松能够以生态眼光发现自然万物的丰盈诗意。例如他在《哈拉哈河》中写河边的火山熔岩上白桦、赤桦、黑桦、红柳、青杨、榛子等植物繁茂,“那些植物就是在火山岩的废墟里长出来的。植物吞噬了废墟,吞噬了废墟底下的肉和骨头,吞噬了能够成为它能量的一切,且长势巨旺,饱满强壮。渐渐地,它们就成了这片世界的主角。”《大兴安岭笔记》中写森林中的蘑菇:“当腐败之物行将瓦解的时候,蘑菇将一切消极的能量迅速转化,靠自身的内聚和吐纳,建立起生态系统中新的法则、新的秩序。因为蘑菇,森林里的腐败之物获得了新生。”这是就生态眼光发现的自然生命的盎然生机和丰盈诗,使得李青松的生态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诗意化特质。
整体看来,李青松的《看得见的东北》是对告别伐木时代的东北林区和林业生态的一种细腻生动的文学赋歌,是对另一种被遮蔽被忽略的东北形象的生态塑造。他以自觉鲜明的生态伦理描绘了东北大地上黑熊、紫貂、鳇鱼、大马哈鱼等独特的野生动物,深情回望历史,呈现出东北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前景。他的创作展开了关于东北林区的生态博物学式的审美建构,并有意开创生态文学的新的艺术路径,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