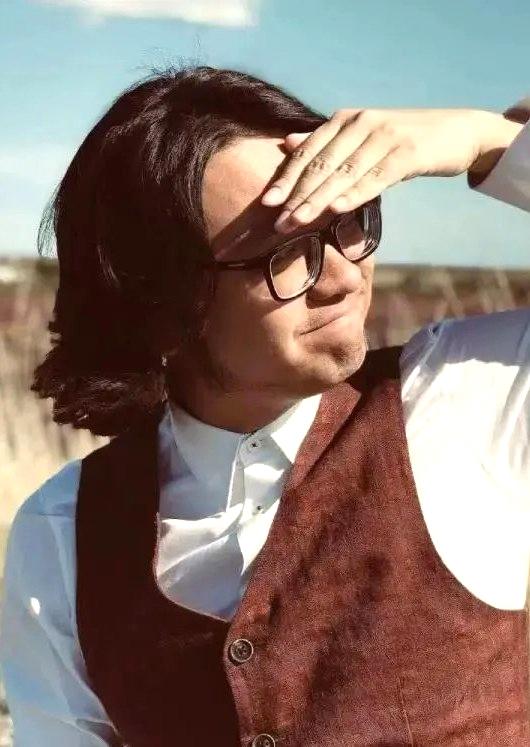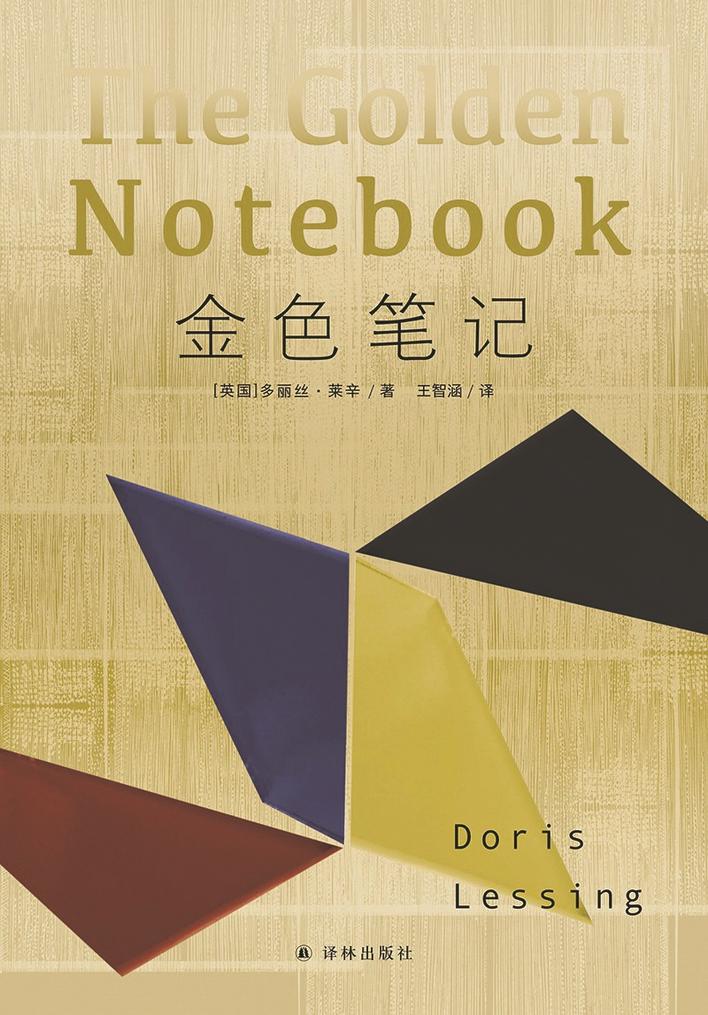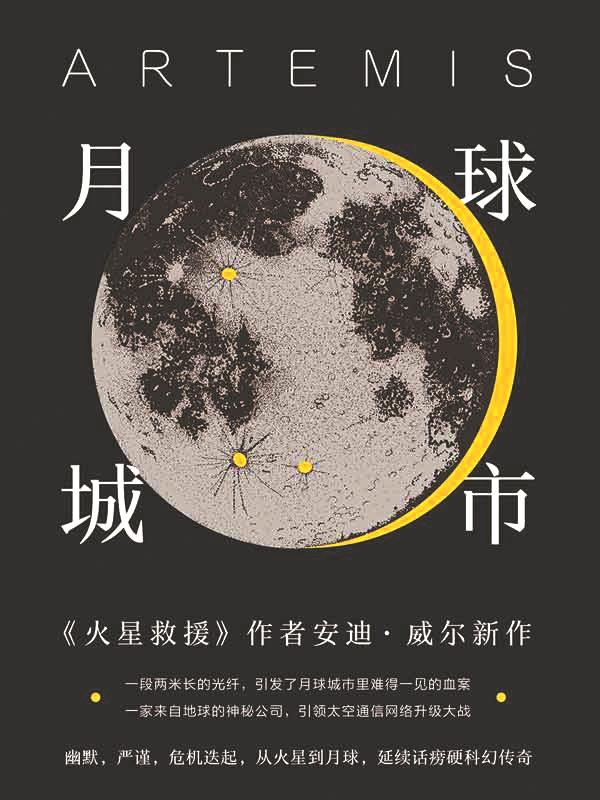至今还记得,我人生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从表哥那里借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的我不到十岁,但还是看完了整本书。我父母意识到我喜欢看书,于是给我买了非常多的外国文学名著,比如《简爱》《傲慢与偏见》《小妇人》《呼啸山庄》《悲惨世界》《雾都孤儿》《红与黑》等等,我也一本接一本地看完了。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早年的语文经验有一大半是由外国文学的译文构成的。我青春时代的文学记忆也多与外国文学有关。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读到的那些文字并不完完全全来自于奥斯汀、司汤达和伍尔夫,还有许许多多隐于其后的翻译工作者们。
大学本科,我进入了国际政治系,自此纯文学离我越来越远,英文学术论文构成了我阅读的主要内容,不过我偶尔还会翻看一些英文原著,有约翰·济慈的诗歌和书信集,乔治·奥威尔的杂文,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厄休拉·勒奎恩的“地海六部曲”,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等等。后来,“地海六部曲”和《神经漫游者》在中国推出了简体中文版,这让看过原著的我对译文的品质有了较为直观的体察——比如蔡美玲老师对《地海巫师》卷首诗歌《伊亚创世歌》的翻译让我铭记至今,原文为:“Only in silence the word,/only in dark the light,/only in dying life:/bright the hawk's flight,/ on the empty sky.”而蔡老师的译文为:“惟静默,生言语,/惟黑暗,成光明,/惟死亡,得再生,/鹰扬虚空,灿兮明兮。”蔡老师找到了英语与汉语之间共同的节奏、韵律与美学。
在我硕士毕业后申请博士的那一年,有幸获得了在译林出版社实习的机会,具体的工作内容是校对,于是时隔多年我又开始了一段与外国文学朝夕为伴的日子。在实习期间也承蒙编辑老师们的抬爱,询问我是否对文学翻译感兴趣,我虽然有非常多的忐忑,但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我开始了安迪·威尔的《月球城市》的翻译工作。
《月球城市》在2020年出版。之后,译林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又询问我是否有兴趣接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翻译工作。当我开始阅读《金色笔记》的英文原著,我很快就被莱辛的笔触所吸引,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野性而不驯的生命力,而这本书所涉及的主题——无论是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国际时局——彼此独立又相互交映出令人目眩的光影。于是怀着兴奋与忐忑,我接下了这个任务。《金色笔记》是本篇幅极长的小说,英文原文约有17万单词,因而翻译本书自然也相当于一趟极其漫长的旅途。正如同所有的旅途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成长,《金色笔记》的翻译工作也给我带来了进一步的蜕变。
“翻译是生命与热爱在燃烧”
在中国但凡谈到翻译,大多数人会想到“信、达、雅”三字。以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此三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三者之间也并无境界上的高低,而是优先级的降序,也就是说“信”为最优先,“达”次之,“雅”为最末。以我对《金色笔记》的翻译为例,莱辛在原文中使用过的一切语素,我要尽量做到在译文中一个都不少,而她在原文中没有使用过的,我也要尽量做到在译文中一个都不多,而不能单纯为了译文的“文采”而任意增删。
在能做到“信”的前提下,“达”也是译者应当追求的,尤其是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开始翻译《金色笔记》时,我时常把握不好是否应该保留莱辛原文的语序与句式,一位前辈讲述了他的经验:“关键还是要看这种遣词造句到底是莱辛个人的文辞风格,还是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本身的特点。”此番话让我茅塞顿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现代英语虽然仍然是印欧语系的一员,但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褪去了像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那样的屈折语的底色,而具备了相当多的分析语的特征,再加上其主谓宾(SVO)的句式结构,因而与汉藏语系的汉语有了相当程度的共性,而这也给英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带来了诸多的便利。话虽如此,可按照英文原文的语序直译时就会出现类似“机翻”的感觉:能看懂,但就是觉得哪里不太对。这里的“不太对”其实就是汉语与英语两门语言本身的差异。
举例来说,比如suppose在英文中是个较为常见的词,在语感上要比汉语的“猜”这个字“虚”一点,《金色笔记》中有一段艾拉与她父亲的对话,她父亲在感叹自己年迈了以后家庭、子女在他眼里都不再重要了,艾拉则追问,那在你眼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呢?她父亲答道:“God,I suppose.”我并没有把“I suppose”直译为“我猜”,而是翻译成了一个语气词“吧”:“上帝吧。”在汉语里“吧”这个字本身承担着类似于“I suppose”这个词在英语中的功能,即表推测。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基本只会在处理人物对话时采用这种“意译”或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所谓的“归化”的策略,因为我认为相对于其他部分,小说中的对话所体现的更大程度上是源语言的特点而非作者本人的文辞风格,而即便是我判断需要采用“意译”或是“归化”的策略,我也会尽量做到“信”,即尽量保留原文的一切信息且不增加任何功能词以外的语素。
至于“雅”,我非常赞同翻译家郭宏安老师对“雅”的新诠释:“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就我对《金色笔记》的翻译来说,莱辛的遣词造句其实是极其质朴且口语化的,因此译文的文风也应当与她的这种“文学性”两相对应而不是另辟蹊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质朴也未尝不是一种“雅”。
面对一个伟大的作家,译者也可能被激发出好胜心来。适当的好胜心是好的,这可以激励译者跟随作家的脚步;但过度的好胜心却是不应该的,因为翻译本质上只能是50%的创作。我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让读者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就像滋养了少时的我的那些译文一样。译者,尤其是年轻译者的修行,应该是一个放下自我的过程。译者是创作者,更是服务者,译者的创作应该为原著、为文学事业而服务。我要感谢那些伟大的作家和激励过我的翻译家们,是他们指引着我并让我知道:翻译是服务,翻译是克己,翻译是体察他人,翻译是架设桥梁,翻译是生命与热爱在燃烧。
译文: 1957年夏,分别了一段日子后,安娜和好友莫莉又见面了。
这两个女人正在伦敦的一间公寓里。
“重点在于,”当朋友在楼梯间打完电话回来后,安娜说,“重点在于,我可见范围内的一切都崩溃瓦解了。”
莫莉是个经常煲电话粥的女人。刚才电话铃响,她接起来就问:“喂?所以有什么新八卦吗?”现在她对安娜说:“是理查德,他马上来。他好像这个月就今天一天有空,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我可不打算走。”安娜说。
“别走,你给我坐好。”
莫莉打量了一下自己——她穿着长裤和毛线衫,都不怎么好看。“不管我现在是个什么样,他都只能照单全收了。”她下了决心,然后坐在了窗边,“他不肯说这次过来的目的——我估计又是为玛丽昂的事。”
“他没给你写信吗?”安娜试探道。
“他和玛丽昂都写了——字里行间很是友好。挺奇怪的,不是吗?”
这句“挺奇怪的,不是吗?”正是她俩亲密地聊八卦时的标志性“乐句”。虽然莫莉已奏响了这个乐句,但她还是转移了话题:“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反正他说了现在要过来。”
“他要是看到我也在这儿,怕是会扭头就走。”安娜说道,语气愉快归愉快,但却带着些许攻击性。莫莉敏锐地瞥了她一眼,问:“哦?为什么?”
安娜和理查德给人一种彼此不大对付的印象,此前安娜每次得知理查德要来,都会选择回避。莫莉说:“其实我觉得他心底里还是挺喜欢你的。问题是,他原则上得努力喜欢我——但他又是那种对人只有‘喜欢’或‘讨厌’两个选项的傻子,因此他把自己不愿承认的那些对我的讨厌全都转嫁到了你身上。”
“那倒没关系。”安娜说,“但你知道吗,你不在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现在很多人眼里咱俩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你才发现啊?!”莫莉颇为得意地说。每次安娜想明白那些显而易见——在莫莉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时,莫莉就是这种语气。
她俩的关系先前就已显现出了一种平衡:莫莉整体上更通人情世故一些,而安娜则悟性更胜一筹。
安娜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她此时只是微笑着承认了自己的后知后觉。
“咱俩各方面都如此不同,”莫莉说道,“所以这还挺奇怪的。我估计是因为咱俩过的是同一种生活——也不结个婚什么的。他们就只看得到这些部分。”
“自由女性。”安娜苦笑道。她接下来又补充了一句:“他们仍在用我们和男性之间的关系来定义我们,就连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也不能免俗。”她语气中带着一丝莫莉未曾见过的愠怒,因而引得对方对她从头到脚好一番打量。
“所以呢?我们不也一样吗?”莫莉有些尖刻地说。“不这么去定义咱俩可太难了。”她留意到安娜投来的意外的眼神,于是有些迟疑地又补了这么一句。接着她俩沉默了片刻,其间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与此同时,她俩意识到:一年的分别的确太久了,即便对她们这样的老友来说。
——节选自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译文出版社,王智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