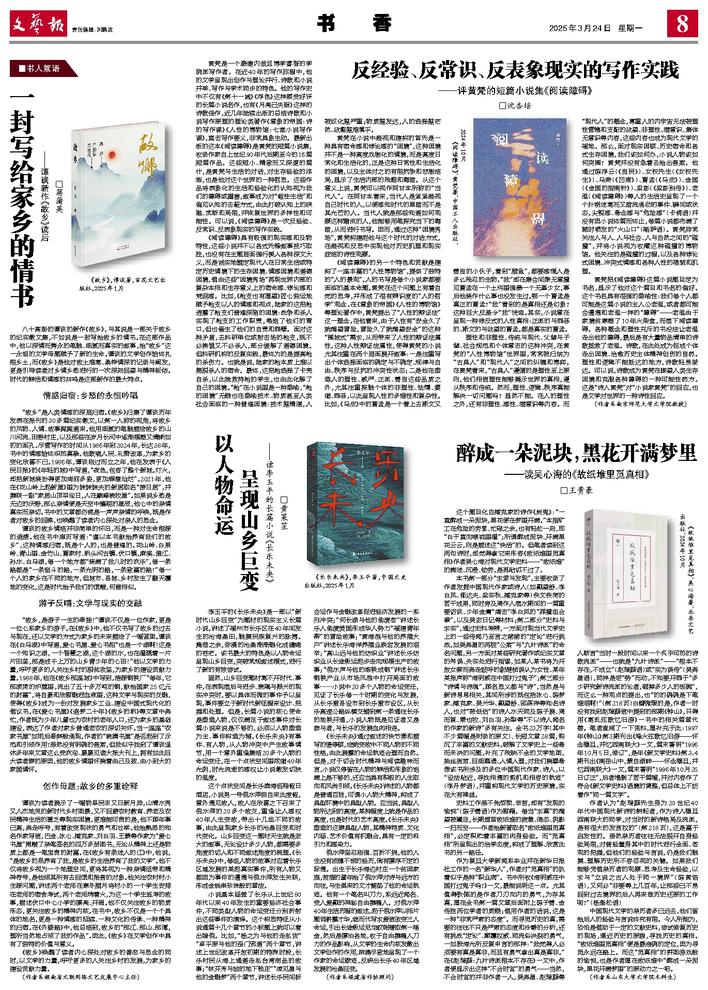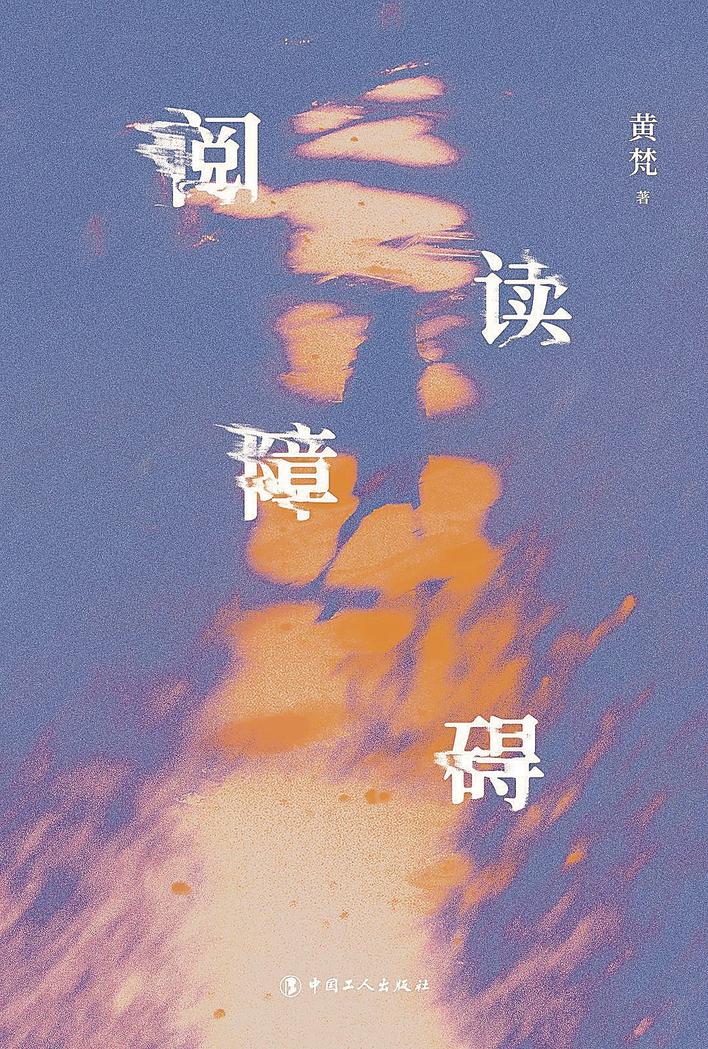黄梵是一个稳健内敛且博学睿智的学院派写作者。在近40年的写作旅程中,他的文学呈现出创作与理论并行、诗歌和小说并举、写作与学术同步的特色。他的写作史中不仅有《第十一诫》《浮色》这样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名作,也有《月亮已失眠》这样的诗歌佳作,近几年陆续出版的总结诗歌和小说写作原理的理论类著作《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人性的博物馆:七堂小说写作课》,直击写作要义,非常具象生动。最新出版的这本《阅读障碍》是黄梵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作家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16篇短篇作品。这些短小、精致而又深邃的篇什,是黄梵与生活的对话,对生存经验的淬炼,也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哲思。这些作品将表象化的生活和经验化的认知视为我们的障碍或圈套,叙事成为对“假性生活”和偏见认知的去蔽方式,由此打破认知上的狭隘、武断和局限,并恢复世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可以说,《阅读障碍》是一次反经验、反常识、反表象现实的写作实践。
《阅读障碍》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及物特性,这些小说并不以各式先锋叙事技巧取胜,也没有在主题层面强行楔入各种深文大义,而是诚实地锚定现代人在日常生活或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生存困境、情感困境和道德困境,借由这些“困境秀场”再现世界内部的复杂本相和生存意义上的宿命感、悖论感和荒诞感。比如,《枪支也有愿望》匠心独运地赋予枪支以人的情感和视点,陆家的这把枪透露了枪支们普遍深陷的困境:战争和杀人实现了枪支的工作职责,喂饱了他们的胃口,但也催生了他们的自责和罪孽。面对这种矛盾,去科研单位或射击场的枪支,既不必挨饿又不必杀人,部分缓解了道德困境。但科研机构的反复实践,最终为的是提高枪的杀伤力。也就是说,陆家的枪本质上难以摆脱杀人的宿命。最终,这把枪选择了卡壳自杀,以此挽救持枪的学生,也由此化解了自己的困境。“枪”在小说里是一种隐喻,“枪的困境”无疑也在隐喻技术、物质甚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种普遍困境:技术越精湛,人被奴化越严重;物质越发达,人的选择越茫然、欲壑越难填平。
黄梵在小说中凝视和建构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宿命感和悖论感的“困境”,这种困境并不是一种高度戏剧化的情境,而是高度日常化和生活化的,正是这种日常性和生活化的困境,以及主体对之的有限抗争和悲剧结局,显示了生活内部的残酷和晦暗。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梵可以视作阿甘本所称的“当代人”。在阿甘本看来,当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当代人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黯淡的人,他能够用笔探究当下的晦暗,从而进行书写。因而,通过这种“困境秀场”,黄梵构建起他与这个时代的对话方式,在凝视和反思中实现他对历史肌理和现实症结的诗性观察。
《阅读障碍》的另一个特色和贡献是建构了一座丰富的“人性博物馆”,提供了独特的“人的景观”。人的书写是每个小说家都要面临的基本命题。黄梵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自觉的思考,并形成了很有辨识度的“人的哲学”观念。在《意象的帝国》《人性的博物馆》等理论著作中,黄梵提出了“人性的辩证法”这一理念。在他看来,由于人性有“安全久了就渴望冒险,冒险久了就渴望安全”的这种“围城式”需求,从而带来了人性的辩证法属性。这种人性辩证法属性,使得黄梵的小说尤其注重在两个层面展开叙事:一是注重写出个体选择面临的确定与不确定、规律与自由、秩序与反抗的冲突性状态;二是他在塑造人的理性、威严、正派、善良这些品质之外,尤其注重探触个体的非理性、怯懦、萎缩、罪恶,以此呈现人性的多维性和复杂性。比如,《马皮》中的曹孟是一个看上去斯文又善良的小伙子,看到“腊鱼”,都要感慨人是多么残忍的生物。“我”却在集会间隙无意撞见曹孟在一个土沟里强暴一个无辜少女,事后他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哪一个曹孟是真正的曹孟?“我”看到的是真相还是幻象?这种巨大反差令“我”恍惚。其实,小说意在呈现一种悖反式的人性真相:正派的与罪恶的、斯文的与欲望的曹孟,都是真实的曹孟。
理性和非理性、传统与现代、父辈与子辈、社会规范和个体意志的这种冲突,在黄梵的“人性博物馆”世界里,常常被归纳为“古典人”和“现代人”之间的纠缠和博弈。在黄梵看来,“古典人”遵循的是理性至上原则,他们相信理性能够揭示世界的真相,遵从秩序和传统。然而,理性、逻辑、秩序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显然不能。在人的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感性、潜意识等内容。而“现代人”的概念,尊重人的内宇宙无法被理性管辖和支配的欲望、非理性、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等内容,这些内容也成为现代文学的福地。那么,面对现实困顿、历史宿命和各式生存困境,我们该如何办,小说人物该如何突围?黄梵并没有急着去给出答案。他通过陈浮云(《良民》)、女校先生(《女校先生》)、马荣(《凹痕》)、曹孟(《马皮》)、金国(《金国的指南针》)、梁彭(《梁彭别传》)、老温(《阅读障碍》)等人的生活史呈现了一个个扑朔迷离而又暗流涌动的事件、瞬间或状态,尖锐感、悬念感与“危险感”(卡佛语)并没有因小说终篇而终止,每篇小说都布满了随时喷发的“火山口”(略萨语)。黄梵异常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碰撞”,并将小说视为收藏这种碰撞的博物馆。他关注的是碰撞的过程,以及各种悖论式困境、冲突式情感和各种人性的褶皱和肌理。
黄梵把《阅读障碍》这篇小说题目定为书名,显示了他对这个篇目和书名的偏好。这个书名具有很强的隐喻性: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老温,或者都可能会遭遇和老温一样的“障碍”——老温由于家境贫寒糊了10年火柴盒,而落下阅读障碍。各种概念和理性充斥的书没法让老温走出他的障碍,最后是有大量物品清单的诗歌拯救了老温。诗歌,在此处成为促成个体走出困境、治愈历史主体精神创伤的良药。理性和逻辑不能抵达的地方,诗歌轻易驶达。可以说,诗歌成为黄梵在瞭望人类生存困境和克服各种障碍的一种可能性药方。这是“诗人黄梵”对“小说家黄梵”的回应,也是文学对世界的一种诗性回应。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