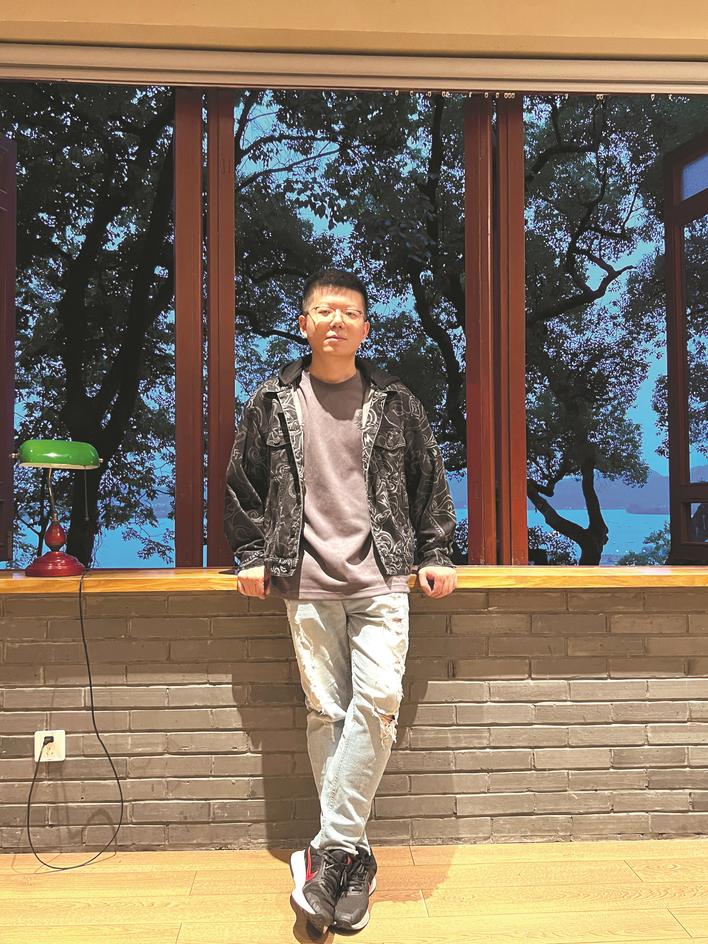乌兰其木格
作为一名1976年生人,我和“90后”徐兆正迄今有超过十年的交往。这十余年正好是彼此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事业从无到有并逐渐取得较为丰硕成果的十余年,是以后衰竭和垂亡之时必然要回忆到的“黄金之年”,只是他仍然像油力充足的机器,还在劲头不减地开疆拓土(我们甚至可以说,目前取得的成就只是他终其一生取得的成就的一小部分,是他更大事业的起点),而我已进入某种收尾阶段,任由身体和精神进入太多的慵懒与知足。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像是两个跑步者,在一个退出赛道后,由彼此勉励变成一个对另一个单方面的祝福了。
我认识兆正是他在大学念本科时,通过互联网、报纸来发表自己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看法,笔名叫“出何典齋走狗”。后来他去广西师范大学读西方哲学硕士,在我以为他究竟要以哲学为业时,他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博士毕业后赴杭州师范大学执教至今。表面看,读哲学是走了一段弯路,是一种进取途中的随波逐流或者说迁就,实质这一选择源自他对人生的缜密规划。从文学改道哲学再回归文学,说明并非方向的混乱,而恰恰是明确,是一种深思熟虑。他的博导、文学评论家张柠谈文学批评自身的要求时,提到三点,除开表达的明晰性和准确性之外,就是一个人的艺术判断力和理论思辨力。
在北师大读书数年,他遵从师嘱,把这一阶段精力用于消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小说和诗歌。加上早先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钻研,他实际渐渐形成了自己宏阔而结实的治学基础。在几年前的某一天,我们聊天时,他忽然提到自己已做了200万字的笔记。到今天,可能又有所增长,或许已有300万字了。因为这几年我见到的他非但没有因为教职稳定、组建家庭而出现懈怠,反而愈加投入,往往一天用进去十五六个小时,彻夜写作也很常见。我们创作者都知道,有些事对一个人极为重要,却不好表达,有些事对一个人不重要,却能描写得长篇累牍。譬如所有功夫片都不擅于描述一个练功者如何练功。当我们说到像徐兆正这样的学人做了200万字的笔记,无论怎么形容,都难免落到轻描淡写的境地,但具体到实际,却是要消耗一个人无数个日夜。
因为如上提到的努力,徐兆正在批评上具备了令人瞩目的不同。我认为有这样几点:
他有问题意识。他也接受约稿任务,但总体上,他把握住了自己批评的航向,围绕文学仍然存在什么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哪些有意无意被遮蔽的真相,他总是能有所行动。而且他知道分寸,注意跬步的积累,从不落入好高骛远的空谈。
在谈论问题时,他具有广博而深邃的基础。当一个议题或作品出现时,我们说,能够贴近作品去细读是好的;比这更好的,是熟知作者创作至今的情状,知道他的可取、局限,以及变化的概貌;比这更好的,是熟知作者所处的整个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能把作者及文本投放到文学长河里去加以考量;比这更好的,是同时熟知西方19世纪、20世纪文学的历史关节;比这更好的,是还具备了西方思想史的视野,对理性、宗教、信仰等等兼有充足的了解。这种景象好比科普视频里呈现的,通过地球看地球,和通过太阳系看地球、通过银河系看地球、通过宇宙看地球,所看到的终究不同。我不是说徐兆正通过过大的视域看待一件事物会不及物,而是说他同时具备了从小到大来衡量一件事物的能力,因而他也就能相对客观地看到一件事物的价值,以及可能连作者自己都会忽略的潜力。
对准确与节制的热爱。这种哲人的作风和试图让文章具有碑文般力量的用心常为我钦羡。我偶尔会感觉自己文字有不妥之处,但又看不清问题出在哪里,交给兆正看过修改后,每每惊叹此时已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
价值观的稳定。这既表现在对明显的反常识的不认同,也表现在对看起来正确、狂热、打着公理旗号的时髦事物的警惕,不会投身其中以自保或渔利。在具体需要做出选择时,他是服从于萨特的理念的,也就是通过选择来确立自己、建筑自己。如果不能做到最好,也绝不会伤害他人。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这可能是他的师长、朋友更能注意到的。就我和兆正相识的十余年,他完成了从学生到副教授、从书评人到学者的嬗变。如今他虽然不具备学者的名声,却是具有学者的实质的。而且他未来必定是一名可贵的、公认的学者。那么谈到价值观的稳定,其实也存在某种风险。我记得自己初入文坛时,一位我敬佩至今的师长叮嘱我不要混迹酒局,不要在其间迷失了自己。起初我以为是一句套话,记住这句话仅仅因为我对他心怀崇敬。但是这十余年我感受最多的正是这种圈子文化。它并非穷凶极恶地绑架你、勒索你,它的到来总是比春天还温暖,比春风还和煦,让人昏昏欲睡,难以抵抗。徐兆正在这方面远比我做得好,他差不多是一个足不出户的隐士。我们知道,相比于写作者,批评者所受到的引诱总是更多和更大。这几乎是所有文艺批评都不得不面对的考验。对此,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增益自己在志业方面的投入,始终把最宝贵的精力奉献给自己最珍爱的事业。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其他。
萨特的《文字生涯》是我时常翻阅的一本书,在那本自传最后,萨特这样写道:“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天才’的幸运儿。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唯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既无装备,又无工具,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我彻底获救的事业。”这段话,我愿与兆正共勉。
(作者系作家、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乌兰其木格:细读的正义
□赵 坤
在众多文学批评方法中,乌兰其木格偏爱细读。在她尤为擅长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研究中,细读是她进入批评的道门,也是她判断作家作品、构成批评标准,形成个人文学观的基本方法。
作为拥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研究者,乌兰其木格有着对民族文学语言与文化的独特敏感性,能够发现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化修辞方式上的审美异质性。比如讨论石舒清、阿舍、严英秀、阿微木依萝、莫景春、李进祥等当代文学现场里的民族作家作品时,她擅长以细读的方式,通过叙事类型学总结出他们在表现战争、苦难、死亡与信仰等方面独特的民族主题与美学意识。比如对回族文学的意象修辞的发现,就是通过具体文本呈现出的物候生态、宗教建筑、生活仪式和动物等等具有高度原型意义的意象,还原其文学表达的象征性,即“承载回族穆斯林民众对信仰的虔诚,对道德伦理的坚守,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守护等复杂而深刻的精神内蕴。”(乌兰其木格《论当代宁夏回族作家的意象书写》)类似的判断和评价贯穿于乌兰其木格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但与其说这是细读文本时的发现,不如说她是把民族作家作品置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视野之中,将包括民族文学在内的大文学史作为他者,借他者的镜像观察自身,避免只见树木的、独语式的类别文学研究。所以她会以文学批评者的立场,不那么委婉地表达出对于民族文学创作的批评与期待。比如她从作为两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的经验出发,细读了所有入围作品之后提出,“在全球化语境和消费文化的裹挟下,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写作呈现出功利化、封闭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乌兰其木格《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写作的创作理路及其问题》),并在内容、形式,意义和审美内涵等具体方面,谈到部分作品的陈旧、乏味,没能链接到新鲜生动的现实生活景观,也因此无法展开关于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度探索。
除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乌兰对于网络文学的持续性关注形成了她新的研究兴奋点。在考察了大量的网络文学研究后,她以文学史研究者的经验敏锐地意识到,判断新世纪以来的新兴文体类型的基础标准,必须要借重上世纪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甚至是古典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史经验,搭建起个人阅读史的坐标系,这是她赖以衡量网络文学文本位置系数的可靠框架。比如她通过对《琅琊榜》《芈月传》《后宫·甄嬛传》《梦回大清》等小说的细读,从性别视角讨论了“羽翼信史”的传统历史演义中女性的历史角色,将其纳入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同时代历史叙事中“女国民”的形象演变谱系里,思考女性解放、女性的历史想象、两性关系的变迁史等系列问题,将网络文学衔接到新文学书写的脉络之中。又比如,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翻译官》《星战风暴》等网络小说的细读,构成了她对网络文学中爱情主题小说的基本判断,上接《花月痕》《醒世姻缘传》、下连《人海潮》《玉梨魂》《金粉世家》的才子佳人的关系原型。而被过滤掉的中间部分,则是新文学中小说观念与叙事模式的现代性转变,也是网络言情故事对于启蒙文学观的主动放弃。显然,当乌兰其木格指出这类网络写作取悦性的媚俗与倒退时,她继承的是新文学的人文主义文学观。
必须要申明的是,细读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不是乌兰其木格唯一的方法,更不是绝对的方法。她的细读“以文学作品为本体”没错,但并不以割裂作者、读者和世界的“细读语义”为法则。换句话说,她并没有因为重视细读,而把自己困在本体论的“瓮”里。当面对具体的文本对象时,她擅于调动不同的理论参与复杂的阐释,比如在知人论世的框架里,讨论作者陈涛及其非虚构文本《在群山之中》,提出作者驻村的真实经历与现实主义写作,是如何继承古典文学的“文以载道”传统。又比如她以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理论解读南翔的短篇小说创作,发现其文本中独特的神经症叙事,以及系列小说题材的反思精神。当然,忠于细读始终是乌兰其木格文学研究的起始点,这构成了她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核心的文学观。在推动作品论由阐释进入诠证、由文学现场进入批评史、文学史的过程中,韦勒克关于细读伦理言简意赅的表述,大概可以作为乌兰其木格选择细读的理论来源,“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
这是细读的意义,也是细读的正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