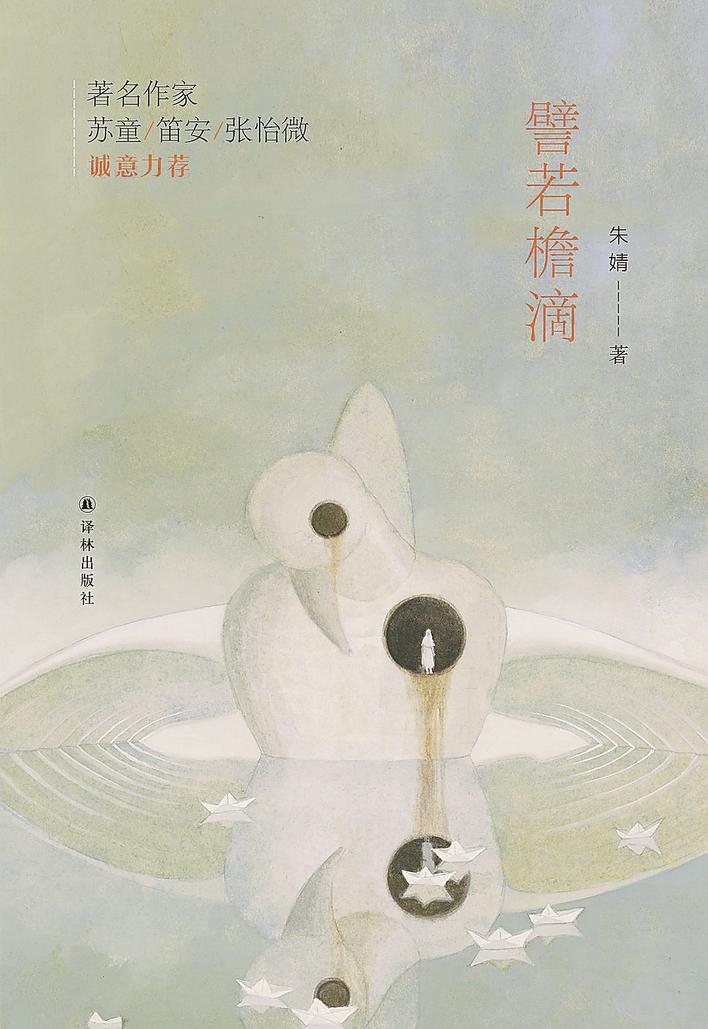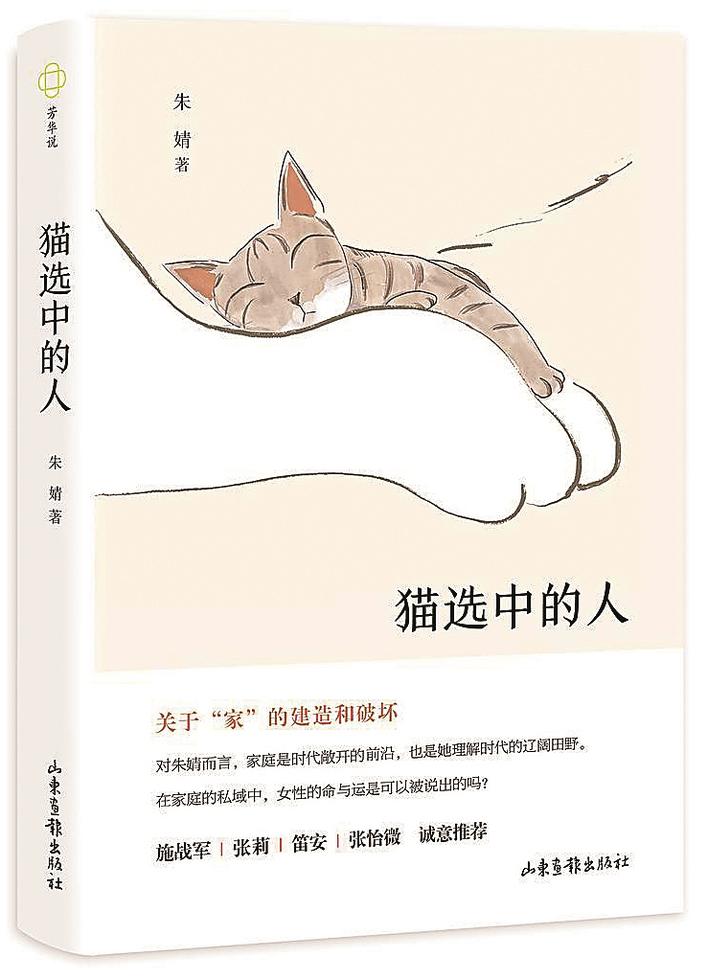■童 欣
青年作家朱婧的小说始终具有鲜明的女性风格,她执着也擅于塑造“家庭生活中的女人”,写她们的柔弱顺从、忍耐牺牲,也写家宅在风波里动摇,写她所爱惜的白瓷女像生出细小裂纹。她从裂纹里窥见光的踪影,却惶惑这光从何而来。朱婧自诩要写“与生命等长的女性故事”,当她由妻子变成母亲,捱过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后,她的小说世界也随之丰饶生长。终于,这种生命力量彻底撑破了白瓷女像,一个个“我”字从断口处迸出,化为丰盈血肉将碎片包裹重塑,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凝结成她滚烫的心,白瓷女像由此变成真正的女人。
雕刻白瓷女像的裂痕
自2017年恢复写作以来,朱婧一直专注于烧制家宅里的白瓷女像,她有意留下细小裂纹,以此证明瓷器的真实质感和久经风霜的优雅从容。她用指尖反复摩挲,体会裂痕凹凸不平的触感,她的爱惜把疤痕雕刻成精致的花纹。她真诚体贴婚姻里那些无伤大雅的破绽,比如丈夫的一次心猿意马、妻子持久的克制忍耐,以及时光里各种物事的破败变化。她大多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与女主人公保持距离,设置身份与时间的屏障,以女儿身份观察母亲、以丈夫视角缅怀妻子、以女友眼光描述闺蜜、以回忆方式重返少女时代……她好像有意回避激烈的情感,而是透过旁观者的眼睛描摹女像的面庞,怜惜中总隔着距离。
《猫选中的人》(2022)和《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2022)都是从丈夫的视角凝视妻子,婚姻中的强弱地位决定了妻子的内心世界始终被忽视。前一位丈夫不知道猫为何选中他,就像不知道妻子是从何时开始眷恋他,对他来说,娇爱妻子和怜惜一只幼猫并无区别;后者回忆亡妻,将她比作“不听不看不说”的鼠妇,小说止步于窥见妻子秘密的一角,更多真相依然藏身家宅的阴影里。朱婧塑造的妻子们都轻易接受了婚姻中的逼仄、匮乏和牺牲,将之视为世间平常。面对出轨的丈夫,《危险的妻子》(2019)最大的报复不过是独自旅行,“绝望主妇”或“致命女人”的剧情永远不会上演,即便“我”下定决心,其表现也只是把冰激凌的勺子挖得更果断些。
事实上,这与朱婧有意淡化冲突、削弱人物的写作策略相关,《譬如檐滴》和《猫选中的人》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面目模糊的。她不专注于雕刻某一尊女像的表情,而是集中精力勾勒这世间脆弱而美丽的人、事、物共同的命运,用弥散在时光里的细碎石子,拼贴出人生版图的星云变幻。然而,这种柔和克制的态度与对细小之物的过于珍视有时会折损小说的力量。一方面,朱婧的视角始终拘泥于家庭生活,特别是夫妻感情、男女关系,给人以停留在“茶杯里的风波”、消遣的“闺阁文学”的印象;另一方面,她的女主人公都太过纯洁柔顺,缺乏成长曲线与反叛性力量,更似神像而非人像,再加上作家本人的天性纯良、学识丰富,这既造就了朱婧小说的典雅纯正,却也让她对人生的理解偏向单纯,缺乏深刻和力度。
寻找光进来的地方
对于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女孩而言,缔结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是早就预约的幸福人生。但命运总是不讲理的,一瞬间就会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她无处可逃,只能在废墟里重建家宅,这是无须教养的本能。因而,自2020年起,朱婧反复书写“失去”的主题,她试图把断裂之处当成光进来的地方,赋予“失去”终将“获得”的意义,唯有如此,她才能为命运毁约的愤懑找到出口。《光进来的地方》(2020)、《鹳》(2022)、《蜜月相册》(2023)、《吃东西的女人》(2023)四部小说逐级搭建了朱婧直面伤痛、修复自我的探索之路,也构成了其女性写作转型的契机。
自我曝光的时刻,也是自我觉醒的时刻,可贵的是,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远超她的预期。最初的曝光依然通过性别的镜像反转完成。《光进来的地方》里,丈夫以回忆的方式填充妻子的一颦一笑,赋予其温柔体贴的完美品性。但回忆里的妻子并非真实的妻子,只是他内心渴望的投射。回忆与当下不仅存在“得”与“失”的对比,更隔着“虚”与“实”的界限,虚构的幻象只是光的折射,并不能作为本源的发光体。
直到《鹳》,随着女性视角的铺陈展开,光的来路才逐渐清晰。在丈夫猝逝后,一贯依赖他人的她成了孩子唯一的依靠,过去被认为是美德的柔顺,在保护女儿时全都摒弃。她称丈夫为“鹳”,即带来生命奇迹的使者,而捍卫奇迹的是她本身。《蜜月相册》里,主人公意识到,关于亡夫的微尘因她的回忆才得以聚集成石,拯救者与被拯救者身份发生互换。回忆的焦点也由怀念逝者转向发掘自身,朱婧以小说宣告:光不能从外面来,修复的力量只诞生于女性内部。
问题在于,把白瓷女像修复如初就可以了吗?女性与回忆的缠斗引发了对昨日之“我”的重新审视。《吃东西的女人》被朱婧视为“告别丧痛与自新的故事汇流”,对“丧失展开的提问”作了阶段性的回答。小说中丈夫的离世让完美家庭的逻辑断裂,父亲规训的经验全部失效,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女性真实的感受,她回溯过去,坦白旧日之“我”和“我”的生活并非无瑕,反而充满压抑、扭曲、束缚。小说在“女人”之上冠以“吃东西”的特征限定,“进食”象征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意味着不论得失,对旧日的告别都是今日新生的必经之路。
创造女性的力量之美
以《吃东西的女人》为标志,朱婧的女性写作进入新的阶段。她直面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小说中纳入更多女性议题,摒弃完美女性的造像,而是写吃东西的女人、大声说话的女人、控诉不公的女人。总之,如乔治·爱略特所言:“服从的义务结束了,而反抗的责任开了头。”
女性在朱婧小说中一度是美丽脆弱且沉默隐忍的。对比《水中的奥菲利亚》(2019)、《葛西》(2020)、《思凡》(2024)三篇同样以“师生畸恋”为主题的小说,可以清晰看到朱婧女性立场的转变和反抗意识的自觉。《水中的奥菲利亚》从引诱者角度告诉我们与恶的距离仅一步之遥,《葛西》以旁观者视角惋惜海上浮舟的命运不可改变;而《思凡》将师生畸恋的根源定性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权力倾轧,也反省女性自身的软弱动摇,勘探在反抗与沉默之间游移的人性。面对性骚扰,“我”和“她”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宣告了女人不再因顺从而美丽,即便注定徒劳,也要奋力一搏。蝴蝶微弱战栗的翅膀或许曾作为生命将熄的标记,现在,它应该酝酿出一场风暴。
《大声说话的女人》(2024)可视为朱婧创造新女性美学的最新探索。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细腻剖白了女性从沉默到大声说话的心迹转折,表现了女性天然的力量之美。朱婧用卫生间缺失的“一扇门”点破女性需求在家庭中长期被忽视的状态,这种忽视源于女性的沉默,根源则是父权制规训下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婚姻把雕刻白瓷女像的权力从父亲传递给丈夫,却从来没人问过她的想法。只有当“她”变成“我”时,改变才发生。小说围绕“我”对女性是否天生柔弱,以至不堪承受暴露内心的风险的质询展开,以生育为契机,促使“我”完成性别身份的认同:“不必隐藏天赋和能量。我是创造本身,我在我的身体里完成了最伟大的创造。”从《那般良夜》(2019)里,母亲为女儿不得不回归家庭,到《大声说话的女人》因生育恢复了女性身体的力量,这种差别不仅是从“母职惩罚”到“女性力量”的观念转变,更是女性主体性确立的结果。女性因遵从自我而具备力量,白瓷女像由此生出血肉,复活为真正的女人。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写道:“伍尔夫对于女性经验怎样使女人变得软弱是极端敏感的,但她对于女性经验如何使女人变得强大却相当迟钝。”朱婧近期的女性写作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女人生来就有创生万物的力量,她们柔美善感,同时强大无畏。
(作者系《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