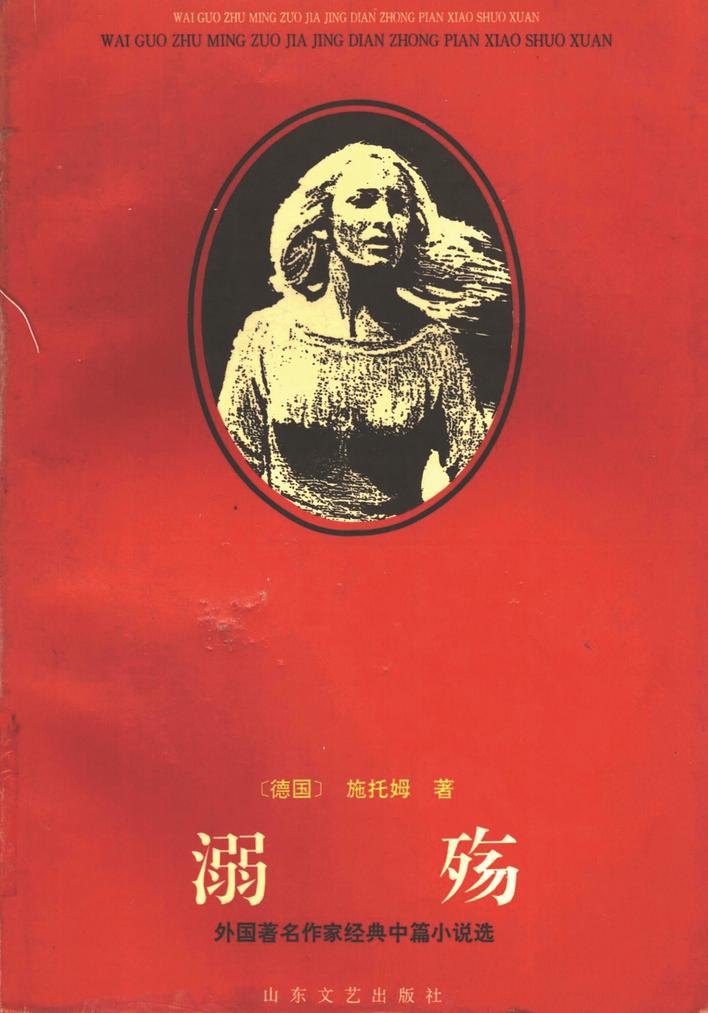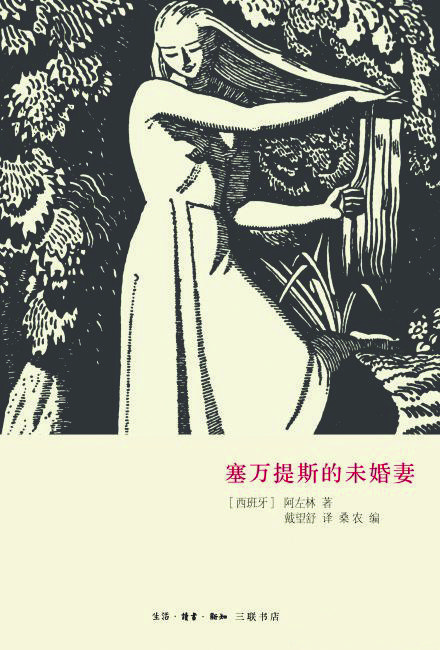2025年,我国意大利语言文学学者、翻译家、批评家吕同六的家属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一批文献,包括大量手稿、笔记本、约稿函、贺卡、邀请函以及书信。笔者在对其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施蛰存信函一封,涉及施蛰存与戴望舒两位文人的翻译活动。
经查证,《吕同六全集》不含此信,而施蛰存的书信在其各类文集中并无统一整理:《施蛰存全集》按通信者整理了部分知名人士的书简,且散见于书中各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则是按时间将通信内容附于相应日期下。而二者同样未对此信进行收录,因此此信当为佚信,值得钩沉、考证与辨析。
信件钩沉·译事初探
此信写于一页稿纸背后,字迹略草,篇幅较短,遗憾之处在于其右下角有大块破损且残页不可见,因此部分内容无从考证,然而这并不影响对绝大部分内容的理解。信件落款时间为1997年5月1日,寄自上海。原文抄录如下(省略号为信件破损处):
同六同志:
信、书、稿酬814元均收到,谢谢。
我今年93,已三年不出门,一份工资也用不完,稿费多少不计较了。1949以前的译书,如有出版社愿为印行,可以无条件同意,烦代为联系。
戴望舒还有二个遗稿,都是西班牙文学。一本是《两个皮匠》*,一本是阿左林的散文随……《小城》。也请你留意,有什么出版社能印……
此问好。
施蛰存
1997.5.1
《溺殇》这个译名不妥,只有“国殇”……别的“殇”。
*此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多年了,作者名记不清了。
可见施蛰存致信旨意,首先在于就收到的稿酬与书表示感谢,其次在于将其他译作的出版继续托付于吕同六,包括施蛰存自己的译书与戴望舒的译书。
吕同六常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主持组稿编辑多套意大利文学和外国文学丛书。其曾对中国在外国文学引进中存在的保守、狭隘心态提出批评,而提倡“全方位、多层次的引进”,“一为对外国文化的引进应当采取‘勇猛’的、毫不畏惧的、宽容的态度,二为对引进的对象,要有个‘分辨’,有个档次高低的区别”(《全方位、多层次的引进》)。
信中所提的书与稿酬应指1996年3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溺殇》。该书由吕同六主编,林达、陆雨莉作为副主编,《序》中写到该书主旨为“从浩如烟海的外国中篇小说中,选取那些艺术上确有特色,已有定评的佳作,提供这些名著的优秀译文”。其中收录5篇中篇小说,包括施蛰存译施尼茨勒的《爱尔赛》。《爱尔赛》讲述了“一个少女为了替父亲还债,蒙受难堪的羞辱,昏厥,自杀”的故事。小说通篇采用内心独白,描摹女主人公的心态、潜意识,从中似可瞥见施蛰存大量创作所受影响的来源。
旧译新传·版本考镜
吕同六主编《溺殇》所采用的《爱尔赛》,并非施蛰存耄耋之年的新译。施蛰存译《爱尔赛》的现存最早版本收录于1931年6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妇心三部曲》。在此版本中,小说题目被译为“爱尔赛小姐”,而作者译名则为“显尼志勒”。该选集还包括长篇《蓓尔达·迦兰夫人》和中篇《毗亚特丽斯》。上海言行社于1947年2月对该书进行了再版。通过对比,可确认此版《爱尔赛小姐》和《溺殇》收录的《爱尔赛》内容与译法一致,前者就是后者所采用的蓝本。
据《施蛰存文学著译年谱》以及各大期刊库,《爱尔赛小姐》在《妇心三部曲》之后的出版主要有两次。上海言行社在1941年5月将这部中篇小说单独出版,题目改为“女难”。福建南平复兴出版社在1945年出版小说集《爱尔赛之死》,其中包括《毗亚特丽斯》和《爱尔赛之死》两篇。直到1996年,《爱尔赛》的出版版本大致均沿用1931年神州国光社《妇心三部曲》版。从这之中,一方面可得知施蛰存所译《爱尔赛》的版本流变,另一方面也可窥见施蛰存早年译作绵长而悠远的影响力。这既体现了施蛰存的翻译之功,亦可见他对施尼茨勒作品投注的心血。
施尼茨勒的作品很难翻译,这在当时的翻译界几乎是共识。施蛰存据英译本对施尼茨勒的作品进行翻译,在大体采用直译的基础上,以其文学家的素养对句式进行灵活调整,避免雅辞丽语,力求通俗、质朴,以使语言流畅妥帖。66年后,著名翻译家吕同六在对“浩如烟海的外国中篇小说”的“优秀译本”进行遴选时,秉持着“文学翻译是科学的、创造性的劳动,也是艺术的二度创作”的观点,认为翻译“既需要对作家、作品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风格习俗力求有尽可能广泛、真切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对作家的思想意识、文艺观点、身世际遇、艺术特色和语言风格有尽可能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还需要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不断升华”,依旧将施蛰存所译《爱尔赛》纳入了四部中篇小说之一。(吕同六《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管见》)“十余年前旧译,犹有嗜痂者”,数十年后亦复是,施蛰存译作的经典性承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彼岸回声·译笔文心
以《爱尔赛》为代表的诸多译作,足以让施蛰存成为施尼茨勒在中国的重要译者。施蛰存在翻译与介绍的同时,其文学家与翻译家的双重身份产生交叠,他调动创作经验进行翻译,又将翻译所得技法实践于新的创作。这种学习、吸收与能动性的改造,完全可被视作近代中国以来介绍外国文学建设本国文学的一次经典案例。
自《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2号发表茅盾翻译施尼茨勒的剧本《结婚日的早晨》起,中国新文学对施尼茨勒的关注与介绍就是广泛的,以戏剧与小说为两个主要方向。施蛰存对施尼茨勒的关注和翻译集中在1927年至1937年,主要译介小说,而这一时期正是施蛰存进行现代派小说创作的起步与风格逐渐形成期。他曾就新文学界在外国文学介绍上的偏狭、松散与薄弱,批评这种“对国外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其译介工作涉猎范围极其驳杂,翻译作者国籍涵盖了十余个国家,当中不乏薄伽丘、海明威、都德、司各特等名家,但众多文学家之中,他对施尼茨勒的重视仍是较为突出的,因此施尼茨勒的小说艺术对施蛰存的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目前可见的范围内,施蛰存对施尼茨勒的翻译可以追溯到1929年1月上海尚志书屋出版的《多情的寡妇》。以《显尼志勒重要著作目录》中的译名为参考,再对重复翻译与改名再版的情况进行整理后可以推断出,施蛰存主要译介了施尼茨勒的作品共6部,即《牧人之笛》、《倍尔达·迦兰夫人》(又名《多情的寡妇》,亦即《孤零:妇心三部曲之一》)、《毗亚特利思及其子》(亦即《私恋:妇心三部曲之二》)、《爱尔赛小姐》(亦即《女难:妇心三部曲之三》)、《薄命的戴丽莎》、《戈斯特尔副官》(又名《生之恋》《自杀之前》)。除此之外,抗战刚开始时,施蛰存翻译了施尼茨勒的小说《维也纳牧歌》《喀桑诺伐之回家》《狂想曲》,“书稿译完当时没有机会出版,译稿在松江家中毁于兵燹,以后也没有兴趣再重译”。
在《薄命的戴丽莎》的《译者序》中,施蛰存对施尼茨勒进行了系统性介绍,“显尼志勒虽然是属于新浪漫主义者群中,他却不像霍夫曼斯塔尔——一个与他齐名的作家——那样地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他毋宁说是一个渗透着写实主义的新浪漫主义者,不过这写实主义当然是南欧式的”,并高度评价其“可以与他的同乡茀罗乙特媲美”,“或者有人会说他是有意地受了茀罗乙特的影响的,但茀罗乙特的理论之被实证在文艺上,使欧洲现代文艺因此而特开一个新的蹊径,以致后来甚至在英国会产生劳伦斯和乔也斯这样的分析心理的大家,却是应该归功于他的”。无论这些论断在事实层面是否准确,都能够反映出施蛰存对施尼茨勒创作的理解,以及他在将施尼茨勒引入中国时,着意取法、应用,并向公众强调何种文学思想与技巧。
施蛰存对《爱尔赛小姐》有极高的评价,他对作品的关注点在于“全体皆用内心独白,而不插入一句客观的描写”。若取施蛰存创作的所谓“心理分析小说”《石秀》具体观之,则可见在女性元素、非理性因素与表达技巧等角度上,两位作者之间存在的联系。《石秀》是典型的有限视角,所有情节的展开始终是透过石秀的眼睛,包括情节省略与叙述加速。施蛰存对于欲望的态度和施尼茨勒一样,都是科学实验意味的研究,而非评判或直接定性。欲望成为剖析的对象,也成为使人物得以丰盈完整的另一面。
当然,施蛰存对于施尼茨勒并非全然移植,而有自己的创作理念。施蛰存的创作不仅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土壤,更超越自己生活的当下,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与传说等更加遥远、广阔的时空背景。正如施蛰存在《关于“现代派”一席谈》中所说,引入“新的创作方法”是为“表现人物,加强主题”,但归根结底仍要“写反映中国国情的作品”,“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认真吸取这种‘进口货’中的精华,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随后才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创作出既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
遗稿浮沉·故人牵念
此封佚信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戴望舒的两本西班牙文学遗稿《两个皮匠》与《小城》。对于这两本译稿,施蛰存提到其多年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目前可见范围内,戴望舒译此书虽非毫无踪迹,但仅有一篇译者题记被收录在一本作品选内。该书书名为《二个皮匠》,与施蛰存的描述稍有出入,然确系同一作品。据译者题记,“《二个皮匠》是《倍拉米诺和阿保洛纽》的改题,是使阿耶拉一举成名的杰作。他的一切的长处,我们都可以在这本书中窥见”。戴望舒翻译此作,“是根据一九三一年马德里Pueyo书店出版的阿耶拉全集本,同时参考Jean et Marcel Carayon的法译本译出的”,“在译成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译文,总还不能满意,因为这部书实在是太难译了”(《〈二个皮匠〉译者题记》)。
1943年7月25日,戴望舒以笔名“白衔”在《风雨谈》上发表阿左林散文译作《一座城》,又于1947年7月1日以本名将其发表于《远风》第4期,于1947年8月18日将其发表于《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90期。该文以第二人称描写冈达伯里亚的小城桑当代尔,以移步换景的形式带读者走过当地的伽蓝、桥街、白街、海岸,即时性的见闻中兼有幽深的感触与哲思。阿左林今译作阿索林。徐曾惠、樊瑞华所译阿索林选集《卡斯蒂利亚的花园》与王菊平、戴永沪所译《小哲自白》中,均曾收录其散文随笔《小城》。经对比,可确认二者与戴望舒所译《一座城》系同一作品,这应当也就是施蛰存信中所提的《小城》。
戴望舒译《一座城》后被收入2013年桑农编阿索林作品集《塞万提斯的未婚妻》,该作品集《新编序》中提到,“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一题来自戴望舒、徐霞村的同名合译本。据唐弢《晦庵书话》中《阿左林》一则,该合译本集中有90年代《戴望舒全集》未收录的15篇译文,绝版已久,曾被唐弢借予师陀、傅雷,以“西班牙小景”之名重印后,被编者桑农买下。桑农以“戴译阿左林小品”为主题,收录《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原书中的戴望舒译作15篇,与《西班牙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见刊的其他阿索林小品文译文、相关小引与书话。编者在提及阿索林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时,高度肯定了戴望舒译作的价值。如此对戴望舒译作的重视与重新挖掘,无意中部分地完成了施蛰存在十余年前的托付,甚至是数十年前的托付。
1932年,施蛰存受现代书局张静庐之邀,出任《现代》杂志主编。戴望舒为《现代》杂志的文学生产活动提供了众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并参与了主要的编译任务。施蛰存在将现代派诗歌作为重要内容推出的同时,集中刊载了戴望舒重要的创作及译作,并鼓励和鞭策戴望舒更努力地创作诗歌与诗论。
在《现代》创刊号上,戴望舒主要译介了三位作家,除法国的阿保里奈尔以外,另两位正是1997年施蛰存在信件中提到的阿耶拉和阿索林。其中,对阿耶拉和阿索林的同步译介,包揽了杂志为数不多的连载份额,因为两者都是西班牙“1898年一代”的作家。他们以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与寻求国家出路的愿望为共同点,这“与‘五四’以后的知识者对现代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可以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刘进才《阿左林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为“1898年一代”的代表之一,阿索林受到了中国文坛的青睐。戴望舒对阿索林的译介是较早的,在其介绍中,阿索林是20世纪随笔体小说的创始人,认为小说是没有结构的,正如流动的、没有结构而又各色各样的人生。通读戴译《一座城》后,既可理解戴望舒描述的创新性文体,又能体会到译者所欣赏的思想性,亦即在“描绘日常生活和风景”之下隐含的“作者想要深入到西班牙民族的灵魂中去的努力”(刘叙一《“强烈的革命精神”:期刊译者戴望舒》)。因此施蛰存在信中提到的阿耶拉和阿索林两份译稿,或许与《现代》杂志早期对西班牙“1898年一代”作家的介绍存在关联。换言之,“1898年一代”的这两篇译稿,可能是二人在一同编辑《现代》时共同的约定。从阴阳相隔到两人皆已逝去,施蛰存惦念的译稿并未被全然埋没,戴望舒用心作的译文仍有迹可循,能被世人看见。
经由译事回到这封佚信,当中流露出的情谊,在任何意义、任何角度上都可以算作佳话。1927年夏天,施蛰存开始翻译施尼茨勒的作品。彼时他正与戴望舒、杜衡避居松江老家,施、戴二人一同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施蛰存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翻译。70年后,93岁的施蛰存经历心脏病的治疗,“三年不出门,也无处花钱了”,不要稿费而要书籍几乎已成为其惯例。如此情境下,施蛰存却依然记得托付友人多年前两本失去踪迹的译稿。而此时戴望舒已逝世47年,两人的分离时间早已超过同游时间。无论对文学,抑或对友人,这都是一份跨越时间的赤诚。戴望舒泉下若能有知,或许亦当会心一笑。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实习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