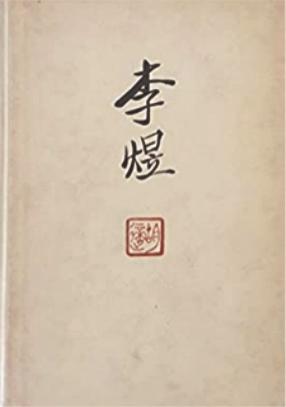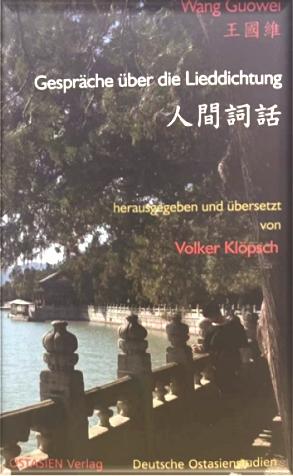“词”这种文学体裁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时期,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唐诗宋词比肩而立,同为中华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典诗歌在德语国家的译介开始较早,1747年至1749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整理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被译成德语,这部著作中收录了由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Prémare,1666-1736)翻译的八篇《诗经》作品。1825年,奥地利汉学家费之迈(August Pfizmaier,1808-1887)第一次用德语完整地译出《离骚》和《九歌》。除这两部经典之外,19世纪末,唐诗也开始被译介到德语地区,对中国诗歌的研究随之逐步展开,其中,李白、白居易、陶渊明等诗人的作品尤其受到文学爱好者、研究者的推崇。从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关于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中地位的一些说法,我们能够看出德国汉学界对于中国诗歌的重视:
中国文学因其诗歌而著名。千余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把“诗”作为其文学表达方式。尽管他们也必然会使用其他的文学表达形式诸如叙事、戏剧或小说之类进行创作,但是由于其使用的语言是口语(白话),这些文学表达形式被视为次要。如果上个世纪末人们没有重新发现上述文学形式并赋予其新的价值的话,那中国的文学史就只能被称为诗歌艺术史。
顾彬认为,在唐诗之后的千年中,只有宋代的“词”能够与唐诗相提并论:“以至于直到今天,唐诗和宋词仍没有失去其作为代表性诗歌的特色——在中国之外也是如此。”虽然顾彬将“宋词”置于和“唐诗”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综观德国汉学界对两者的译介和研究,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样的对等。
德语国家对“词”的译介情况概览
不同于对唐诗大量系统的研究和译介,词在德语国家汉学界至今少有人问津。到目前为止,有关词的比较有体系的著作仅有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发表于1950年的一部《南唐后主李煜词全译及分析:中国词艺术入门》。由于缺少对这个专题的深入研究,希望了解中国词作及词人的读者只能转而借助英美的一些论文和专著。
1922年,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出版诗歌译作集《中德的四季与晨昏》,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个部分,共收录54首作品,其中包括欧阳修的《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苏轼的《阮郎归·初夏》等8首词作品。卫礼贤在这部译文集的副标题中将所收录作品统称为“Lieder und Gesänge”(歌、咏),并在译文的风格上对这些作品采用了“无差别对待”的态度。卫礼贤的关注点显然更多是在作品的内容,而非形式上,德语读者自然也就无从分辨原作形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
1951年,霍福民在关于李煜词的专著之后,又出版了《春花秋月:宋词选译》,其中翻译了包括欧阳修、秦观、苏轼、王安石等词人的共计20首作品。史华慈(Ernst Schwarz,1916-2003)于1985年翻译出版了一部收录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作品的《中国女性诗歌:宋代词人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集》。2011年,甘默霓(Monika Gänßbauer)出版名为《雪中松》的词集,其中辑录翻译了38首辛弃疾的词。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散见于各种诗歌集或杂志中数量不多的一些词作译文了。相对于中国古词的丰富、词学研究的博大精深而言,可以说,这个题材在德语区图书市场上的介绍几乎还是空白。
2019年,“大中华文库”推出了《宋词选》德文版,这部译文集共收录169首词,覆盖了各流派宋词的代表性作品。2017年,叶嘉莹著《人间词话七讲》德文版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项目完成后,这部译著于2024年由德国的学术出版社Peter Lang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由德国汉学家、中国诗词研究专家吕福克(Volker Klöpsch,1948-)翻译的《人间词话》(德国Ostasienstudien出版社出版),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首个德文全译本。对于词及词学在德国的译介和推广,这些著作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空白的作用。
霍福民与他的“中国词艺术入门”
1950年1月,霍福民出版专著《南唐后主李煜词全译及分析:中国词艺术入门》,这是德国汉学界在中国词研究方面的一部拓荒性的作品。
在这部著作中,霍福民除了介绍李煜的生平及其文学创作之外,还介绍了一些与词相关的基础知识,例如词牌名,以及一些常见的概念和意象。霍福民在书的前言中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与目标,他认为德语国家对中国诗歌的根本特点缺乏清晰的认识:“即便是对专门研究汉学的人来说,想弄清楚中国诗歌的本质特征已经很不容易,更不要说那些不懂中文的读者了,他们从译文或者一些编译作品中获得的印象一定是非常混乱的。”虽然德语地区有冯·查赫这样优秀的译者,但查赫的作品“分布过于分散”,所以即便是汉学圈里也有很多人并不熟悉他。而研究论著中的译文又因为过分注重字面对应,所以只有非常熟悉中国语言和诗歌的人才有可能窥见一些原文的精妙之处。这也正是霍福民给自己这部著作添加“中国词艺术入门”这个副标题的原因所在,他要让那些真正抱着探究心态的人能够了解中国诗歌艺术的独特之处和真正的价值所在。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著作针对的是那些对中国诗歌抱有研究兴趣的西方读者。
霍福民在这部著作中共翻译了李煜的45首词作品。他采用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译介形式:每首词的译介都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逐词对应式的翻译,名词解释以及内容解读。以《浣溪沙》为例:首先是词牌名,词牌名采取直接音译的形式,原文紧随其后,词牌名之前是带有说明解释性质的德语,用这种方式将“词”的特殊之处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词牌名“浣溪沙”之下是逐行逐词式的翻译,译者不仅给每一句编号,并且完全依照原文的词语顺序来安排相应的德语译文,同时将用于解释或为了照顾德语行文习惯而添加的词全部用括号标出。在书中的其他一些地方,译者甚至会将对应的中文字用括号直接加在德语译文中。
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
李煜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逐词翻译之后,霍福民选取作品中的一些词汇做了进一步解释。在上面这个例子中,他选择的是“三丈”“金”“点”和“酒恶”这四个词。在注释之后,作者用一句话总结了词的主要内容,并对内容进行解读。霍福民选注的词多为中国古典诗词作品中的常用概念及典故,他对于作品的解读也比较简单,可见当时德语地区的读者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内容还是非常陌生的,而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霍福民这本“中国词艺术入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在45首词的译介部分之后,霍福民另辟专章,逐一详解这些作品所涉及的词牌,作品的版本和流传情况,书的附录中还有对一些核心意象和文化词汇的注解,附录之后是作品的原文。
从霍福民著作的整体结构看,其“介”的功能显然远大于“译”,体现出了明显的学术研究特征,是符合作者预设的“词学入门”这个目标的。不过,若单从“介”的角度看,作品的结构安排又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缺陷。译者力求直观呈现原文原貌,基本照搬了中文的句式结构,希望能够与原文形成一一对应。但是,可对照阅读的原文并没有被安置在译文旁,而是全部附在正文之后,这种布局结构实际又放弃了视觉上的直接对应。对那些具有一定中文阅读能力、希望借助霍福民译文认识词艺术特点的读者而言,如果想要对照阅读就会非常麻烦。而如果是不具备中文知识,仅希望通过霍福民的译文来了解词的读者,霍福民的译文又因为太过于贴近中文的句式结构而显得非常生硬,是否真的能让德语读者“窥见词的精妙之处”很值得怀疑。
霍福民的著作为普及中国古典词艺术做了全面且具有拓荒性质的基础性工作,对词在德语地区推广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著作所采用的特殊译介形式,使其所适用的目标群体变得非常有限,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词在更大范围内的普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由于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普及一些与词相关的常识,因此从内容上有欠深入。霍福民为了介绍词的特征,集中以一位词人的作品为例来展开论述,这样横截面式的介绍虽然能够很好地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介绍对象,却无法让读者了解词的全貌。霍福民著作的这些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德语国家对词的译介及研究状况决定的。要使德语国家的读者对词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仅凭借一部著作显然远远不够,但遗憾的是,在霍福民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系统性研究或译介的出现,宋词在德语国家的接受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大中华文库”与“走出去”的宋词
2019年,由德国汉学家吕福克作为主要选编者与译者的《大中华文库·宋词选》出版。《宋词选》共收录、翻译词作品169首,来自41位词人以及两首无名氏作品,其中112首作品为首次译成中文。《宋词选》距霍福民的著作已经过去近70年,但词对于德语读者而言依然十分陌生。在为《宋词选》所作的前言中,吕福克开篇就写道:
中国古词的优美与丰富多彩到今天尚不为德语读者所知。在德语区的图书市场上,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本有代表性的词选,即便是具备文学造诣的读者或者文学爱好者,也并不对任何一位词作者有深刻的了解,能够具备一定质量的德语译作只有寥寥几十首,并且散见于一些年代久远的集子或者一些少有人问津的专业论文中。即便是讲述中国文学史的那些代表性著作也不十分关注宋词,只用几页篇幅草草地一带而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德语读者对宋词又从何了解呢?
那么,德语国家的汉学界对“诗”和“词”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呢?对这点,霍福民和吕福克给出了同样的解释。吕福克认为宋词之所以被冷落,是因为西方汉学向来偏重研究被视为主流的儒学,因此忽视了其他相对自由的文学表达形式。霍福民更是指出了这种偏好的源头。他认为这与西方汉学的源起有关:由于“汉学研究最初是从接受儒家典籍开始的,我们在这些典籍中接触到的最古老的诗歌作品是已经被奉为经典的《诗经》,因为据说这部著作中有经孔子亲手编订并含有教化意义的内容”。
叶嘉莹在《人间词话七讲》中也谈到了词的“非主流”地位,认为这与其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有关:“诗与文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文章可以用于载道,诗可以用于言志……词,它师出无名……词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它就是歌唱的歌词。”正因如此,词最初也被称为“曲子词”,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词是被轻视的。宋朝人编集子,很多人不把自己写的词编到里边去”。叶嘉莹在书中还引用了一个黄庭坚作词的故事来说明古人对于这种文学体裁的轻视态度,这个故事出自释惠洪《冷斋夜话》:
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
正因如此,这些被认为是“艳歌小词”的作品长期游离在正统文学之外,也因而未能真正引起注重儒学传统的德语国家汉学界的兴趣。
吕福克认为,由于此前德语地区对词这种体裁译介的巨大空白,单靠一部《宋词选》,是不能从根本上弥补宋词译介与研究的不足的:“在德语区,人们对于中国古词的博大精深还几乎一无所知。仅以宋代而言,收录在《全宋词》中的1330余位词人的近两万首作品中,能够翻译成有一定质量的德语的仅四、五十首而已。从数量上,这个比例还不到0.5%。”但《宋词选》“毕竟还是能够让德语读者首次看到一些重要的作品”。
正是考虑到宋词在德国的接受现状,《宋词选》从选篇方面更侧重于“全”,将词这种文学体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介绍,篇目从组成上涵盖了不同时代、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不同于霍福民译介风格的是,《宋词选》的译文更注重传达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性。不过,《宋词选》依然没有脱离学术和研究的特征。在《宋词选》前言中,译者提纲挈领式地对词进行了概括描述,介绍了词的发展历史、主要特点及常见题材,同时也解释了可能会对德语区读者造成理解困难的一些背景知识。在译文中,译者对一些与文化背景相关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注解。此外,作品附录的推荐书单中列出了这一领域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成果,为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基础资料信息。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为这部作品划出可能的目标读者:他们应该是具有较好文学素养,或者对中国文学有一定了解并抱有较强兴趣的专业读者或精英读者。结合宋词目前在德语国家的接受状况,这样的目标读者群设定是切合实际的,也是合理的。
《宋词选》可以被认为是继霍福民著作之后这一领域的又一部具有拓荒性质的作品。这部著作因其所借助的平台“大中华文库”,因而带有鲜明的机构化运作特点。“大中华文库”1994年被批准立项,1996年正式开始实施,目的是“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这种机构化的译介形式从选本到出版,整个过程能够体现出统一的思路。在向外推介中华优秀作品的过程中,通过主动的政策引导,帮助一些应该得到译介,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引起关注的作品走出国门,系统地填补外译领域中存在的空白。从选编方式看,由中方的出版委员会选定其中一半作品,德方译者负责另一半作品的选编,这种方式兼顾中外的不同视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推介方式。因其拥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也比较容易实现高素质译者的选择以及译文质量的把控。《宋词选》的德方选编者及译者吕福克是德国为数不多从事宋词研究及翻译的专家,译者对德国汉学图书市场以及德国读者阅读习惯和“盲点”的了解,也有助于译作顺畅地进入德国图书市场。
但是,从《宋词选》的传播情况来看,我们却遗憾地发现,这部制作精良、构思细致的作品集从出版至今,始终没有实际完成“走出去”的任务。《宋词选》出版之后,并未真正进入德国的图书流通渠道,不但在amazon.de或buecher.de等图书电商平台上找不到这本书,即便是在德国大学的图书检索系统里,也查不到这本书。也就是说,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目前在德国都还接触不到这本书。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地方依然是在中国,而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中,《宋词选》与德语教材和字典归在一类,似乎正在成为学习德语的工具书。这种现状,可以说与“大中华文库”把中国文化经典“介绍给全世界”的初衷相去甚远。
如何使中国优秀的文化、文学经典“走出去”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在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不懈地为之努力。“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至民间,中国文学‘走出去’在体制和机制建设上日臻完善,文学外译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渠道和层次日趋多样。”
2024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德文版(吕福克译,德国Ostasienstudien出版社出版),以及叶嘉莹的《人间词话七讲》德文版(顾牧等译,德国Peter Lang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朝前迈出的又一小步,但还远未达到使宋词在德语国家落地生根的目标。宋词在德语国家的译介情况也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为世界所了解,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仅完成译与介,这个“走出去”的任务实际还远未完成。在探讨如何从文字上更好地将中国文化经典呈现给世界之外,我们同样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使完成了语言层面转换的作品进入有效的流通渠道,真正引起潜在读者的关注甚至兴趣;如何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群体,借助译介作品,加深目标群体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吸引更多人关注中国文化,同时也促使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加入研究和译介中国文化作品的队伍,保证译介工作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更加持久地进行下去。霍福民或吕福克等汉学家的拓荒性工作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如何使他们的工作持续地发挥效用,只有这样,如宋词这样凝聚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品,才能真正做到跨出国门,生根发芽,担当起文化使者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