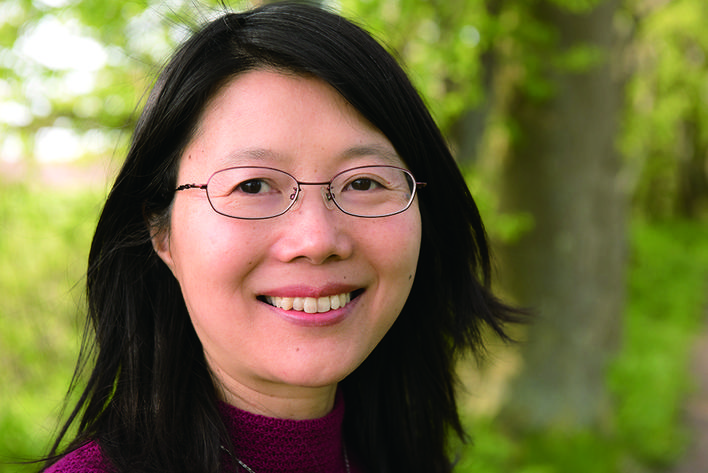文学翻译绝非一个男孩对翻译家母亲说的那句话:“妈妈,你不就是把中文换成瑞典文吗?”将莫言等众多中国小说家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翻译家陈安娜女士跟我提起过:“我儿子以为文学翻译简单得很呢。”男孩长大后对母亲的工作定有更深理解,而世间的多数人对文学翻译恐怕还是容易想当然。
文学翻译不只是把一种文字换成另一种,也不光是有良好的双语能力就足以胜任。
为何这么说呢,首先,“语言能力”一词已运用得过于笼统,而与文学相关的语言能力不单是工具性的、能以段级考试做数值评定的语言能力,更要紧的还有对细致的情绪、物事的情状等有高度理解和精确再现的语言能力。文学译者首先要有能力对作者的文学语言心有灵犀。其次,即便译者的文学语言能力和作者的并不在同一高度,至少要和作者的归属于一类。换言之,译者也具备敏感的理解力和精确的呈现力。对作家留白于字里行间的能够感知,并不着痕迹、不添油加醋,唯借译笔之轻重加以暗示。
其次,文学语言是历史和文化中生长出的活生生的语言,不是计算机上弹跳出的字符。
一方面文学语词牵涉到修辞和象征等,比如“苹果”在文学里可能就不单是字面意思的一种植物果实,而是爱、生育、诱惑、知识、欲望和不朽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语词须在作家和作品生出的文化土壤中具体地感知。斯德哥尔摩的夏夜和上海的夏夜都涉及“夏夜”,但它们的湿度、温度和亮度,在当地居民心中受期盼程度,和燕子接触的时间点却全然不同,在上海一燕不成春,斯德哥尔摩则一燕不成夏。要准确理解这么简单的字眼都要求文学翻译跨过原生文学家园,走到另一片土地上寻根。如此呼吸到足够气息,有较全面的把握,才有可能吐出贴切的译文,而非敲出毫无根基的字符。
我并不反对必要时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而加大翻译的程度,可总体而言,我更倾向于让文学翻译努力接近原文。译者对原作的所谓重新建构在我看来并不可取。译者无权对原文重构,尤其经典作品往往有精密仪器般的严丝合缝,译者应尊重作者的思虑,不宜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更胜一筹。译者工作主要还在破译,破译话语,正如苦思冥想的刑警拉·科尔破译死亡了的生命的灵魂话语、逃逸了的罪犯的癫狂信息。若要展示个人建构力,译者大可另辟舞台展示独立的写作。
然而有一种建构是文学翻译必须实施的。译者不宜只看到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只看到作家的盛名或作品的光环,而应将作家作品当作动物,知道它在生物谱系中的位置,它和相关生物在灵魂上如何勾连、呼应和变化。因为一位优秀作家的文字从来不是作家个人的,而是某种文化里凝出的一滴,又终将落地、回流文化大地。在凝结过程里,它已然经历过传承,落地后又将由未来的一滴去传承。
同时,译者对作家作品及生平还应有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须有语言的禀赋和严谨而持久的研究能力,换言之,应该也是优秀的作者和文学研究者。
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一般而言当代作品不如经典作品严密和精准。尽管如此,译者不宜改写原文中不如人意之处。在不违背原文的情况下译者可凭遣词造句予以助力,但对原文的弱点和弊端,却不能改变和粉饰。一方面,瑕疵是作者特性的一部分,和皮肉相连。另一方面,一本书不能靠译本变身为夸张的广告语上的杰作。在当下的时代,文学奇迹实不多见。有时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不多不少。读者大可带着更耐心和谦虚的态度细看一本书里是否有些养分,而没必要急着拿它回去膜拜。我认为书的意义不在于让人膜拜,而在于让人感受到灵魂。
我从事文学翻译的时间不算长。虽说文学翻译并非计划内的生活内容,回想起来,我为它所作的积累不算短也不算少。至于兴趣,中学时纯粹出于兴趣,我竟涂鸦翻译过史蒂文森的《金银岛》。
2010年偶然得知我喜爱的一本瑞典文学经典《格拉斯医生》有数十种语言的译本,竟还没有中译本,我出于分享的愿望将其译出,满足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发表节译。出乎意料,2012年以全译本选入译文经典。那时的我不知文学翻译的轻重,下笔就首译经典名家,初生牛犊般的坦然也促成了一个较高起点。译本得到瑞典学院院士、文学翻译家和汉学家马悦然教授的赞许,认为听到了原作者的嗓音,是中瑞文学翻译历史上的很重要的里程碑。
带着文学翻译的自觉完成的译本是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岛居民》。那时我已明白文学翻译如履薄冰,好在我特别仔细,首先注意不可有硬伤。我也力求贴近作者的气息。《海姆素岛居民》充斥着百年前海岛渔民的生活用语和植物名称,但这部小说的翻译带给我极大的愉悦。比如写下海岛景观的一些译文时,说得上有作者和译者合一的迷幻瞬间,理解的大门敞开着、天上的神乐鸣响,才能给我这样的感受。
又翻译了其他一些书籍后,复旦大学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丛书主编陈迈平老师将翻译《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的任务交给我,我有过犹豫。这部小说有一个中译本,据说因为转译以及当年资讯的不足造成不少大的硬伤,加上译本对原作有多处删减,重翻确有必要。但我倾向于首译。翻译家李玉瑶说,关键还是看你够不够喜欢。玉瑶这句话点醒了我,那是毋庸置疑的,我其实是热爱,因此才会在文学评论集《这不可能的艺术》里特别评介过它。
在瑞典的我着手翻译这部小说时,责编方尚芩在上海淘得旧译本先做起了解,很快发了愁:“这样的内容和节奏,如今的读者哪有耐心看得进啊。”我理解她的焦虑,可我能做的是对文本负责,当下的读者能否跟随小说节奏和情致实不能在我的思虑之内。它是往昔岁月里一些灵魂的故事,是塞尔玛·拉格洛夫为留住那些美好灵魂做出的文字上的努力。这样的书籍不能成为当下的热门书纯属必然,归根结底也无关紧要。
在技术和娱乐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今日,那些炫目的一切和灿烂的金子夺人眼球,但人类文化里最精华的成分在某一部分人眼中从来都不是那一些别的,而始终是灵魂、是人的精神。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就是挽留生动而美好的人物精神的。而我认为文学翻译的重点不是语言的置换而正是精神的推介,是把一种语言文化里的精神、某些人的精神推介到另一语言文化中的某些人那里——那些期待接受的人。至少在当下,人的精神生活很不发达,也未呈现出比往昔更高级的特征,文学翻译的课题之一是善意地提醒人关注灵魂、感受灵魂。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吸引了止庵这样的评委读者。这本书获得《出版人杂志》主办的2019年书业年度评选文学翻译奖,责编听颁奖的王家新先生说到这一句内幕,十分高兴。其实在编辑过程中,她早已爱上这本书,可那时的我们都不确定和我们一样喜爱它,接收那些灵魂的信息的人会是谁。 远在瑞典的我不能特意飞去领奖,可我为这份高水准的接收欣慰,这个奖也因此比2016年获得的瑞典学院文学翻译奖还要让我高兴。
译介与人的灵魂连接的作品,和灵魂对话,让它们借我发声,让读者和往昔的灵魂交流,这是我进行文学翻译的动力。《文艺报》原编辑王杨于书店巧遇我的《这不可能的艺术》,因此找我辟评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