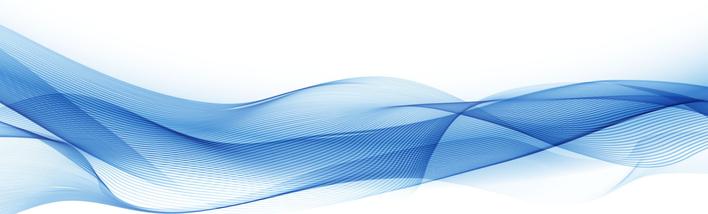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著作现在似乎已经较少有人引用了,他已经在日新月异的理论迭代中被挤到“古典理论”那儿去了,也被经典化了。但他的真正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却被当下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所淡忘,或许当初也没有真正地受到重视。
可是,我认为,中国当下的批评状况,正是最需要杰姆逊方法的时候。虽然,他具体的研究结论和论述很多都可以讨论甚至质疑。
不过,我所说的杰姆逊,不是作为理论家的杰姆逊,而是作为批评家的杰姆逊。这个面向也正是被当代文学批评界所刻意忽略的。那么,杰姆逊的哪些方法值得我们重新正视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点:历史辩证法、中介化、总体化。
历史辩证法
杰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中说,“我们不可能不断代”。他敢于进行历史分期,敢于通过断代来下判断,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支持他进行断代和下判断的依据是社会的基础性的物质性的变化,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科技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型或思维装置。
物质生产,是解释文本的终极原因、绝对的实在界。这都是老话了,社会历史批评似乎是个过时的方法了。但杰姆逊的批评实践证明,这种批评方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如果没有,那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最怕做成僵死的机械决定论,所以要引入多元决定论和历史辩证法。对此我不想多说,因为已经说得够多。我只想强调一点,也是杰姆逊特别吸引我的方面,就是他特别善于对一个阶级的美学经验进行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批判。比如对资本主义文化或资产阶级美学经验的分析。随着生产方式等基础变动,社会关系也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个阶级主体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不断在演变,它表现为美学观念和艺术形式的变化逻辑。这也是现实主义演变为现代主义,再演化为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动力。
有一点尤其重要,杰姆逊提醒我们,不能只看到资产阶级成功的美学实践,还要看到他们失败的美学实践,不要只看到他们通过美学经验和艺术形式对历史的把握,更要看到这种把握的不可靠性。杰姆逊对后现代艺术的分析就是对失败的形式的分析,对再现的不可能性的分析,也是对一个无法在审美经验内部把握自身历史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分析。
这种黑格尔式的历史辩证法非常迷人。这应该是跟卢卡契学的,我们都熟悉卢卡契关于叙述与描写的著名区分。卢卡契在《理性的毁灭》中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它从哲学、社会学演化的角度讲述了德国资产阶级理性崩溃的历史,资产阶级从理性地把握世界开始,最后蜕变到无法理性地把握世界和自我,于是,哲学和社会学也从理性主义变成了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套历史辩证法被杰姆逊讲得大开大阖、引人入胜。杰姆逊说,理论也是叙事,好理论也应该是好叙事。我们的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太不会讲故事了,或者说,讲的故事太拙劣了,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在讲故事。这就是不懂历史辩证法,不懂历史自身的戏剧性。
对我本人来说,这种对失败形式的分析启发很大,我曾分析过当代文学从现实主义到先锋文学的演化,或许是不自觉地学习了杰姆逊和卢卡契。其实,当代文学表意实践也充满了类似的失败,虽然还没有沦为表意链的彻底断裂,却也丧失了指涉物,成为依托旧有文学惯例、在文学系统内部循环的自我指涉的游戏。而大众文化也往往陷入精神分裂式的自嗨。这都值得用类似方法分析。这种美学的失败,显现的或许也是一个失败的历史主体形象。
中介化
杰姆逊一再强调,社会历史批评要从形式入手。历史抵达文本,中间隔着千万重中介。历史是通过语言结构和知识型,最后在形式和修辞的层面表现出来的。杰姆逊设计了复杂的解释学模型,这种模型显得过于繁琐,甚至有叠床架屋之嫌,我想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程序性的设定力求避免简单化的历史决定论。他刻意在强调,形式是在多元决定的力场中成形的。因而,历史的也是形式的,形式的也是历史的,政治的是审美的,审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没有先后。按精神分析的话转述就是,对文本的分析就是对征兆的分析,而征兆或政治无意识的秘密恰恰在形式之中,形式就是内容,反过来说也一样,内容也是形式。我想,正是为了把握这种多元决定的复杂机制,杰姆逊才如此偏爱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
历史与文本之间,经过复杂的多元决定和中介环节,存在着终极的再现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文本都是现实主义的。文本总是对社会历史深层动力的回应,是对社会实践的某种表征或象征行为。即使对那些极端的后现代文本,比如能指播散的文本,或精神分裂式的文本,我们仍可以识读出寓言式的密文。说到底,形式本身总是对历史的再现,即使看似纯能指流的形式也是对历史具体内容的抽象。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反过来也一样,杰姆逊说,现实主义也总是现代主义的,它一直是隐而不彰的装置,进行着主动的形式创造。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形式创造,本质上都是表现性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偷偷摸摸,一个是明目张胆。
总体化
对于“总体化”,似乎当下谈得比较多了,但谈得还不够。我想在此借杰姆逊做点发挥。
我认为,总体化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批评策略。也就是说,总体化的美学阐释,不仅包括解读出沉淀在形式中的时代秘密,还包括敏锐地识别出那些革命性的文化新因素、那些崭新的感受力、新的政治可能性。这需要批评家富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发现。
总体化是双向的,不单是通过历史理解文本,更是通过文本把握历史。只有通过文本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尽管可能是拉康意义上的、暂时的,我们注定只能不断打开一个个瞬间,从而瞥见历史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身是介入历史的新参数和能动性元素,它是总体内部的契机和活跃力量。好的理论和批评并不谋求自己的所谓半自律的主体性,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文学理论,不要老想着创造体系,批评就更不要总想着流芳百世。
基于这些方面,才构成了真正的总体化,也就是“认知测绘”。认知测绘是需要把自己绘制在里面的。
所以,作为批评战略的总体化和认知测绘,要求批评要站在当代文化的上方,走在它前面。通过对复杂中介和多元决定格局的敏锐洞察,重新测绘。它要在玻璃幕墙林立的现代都市空间抽身而出,上升到高空进行观察,从而对当下进行诊断和分析。
当然,现在这样做是有些困难。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的批评家都应该把自己的时代作为最特殊的时代来看待,因为他在最前沿和自己的时代相撞,面对的是暂时无法把握的文化的混乱与复杂;与此同时,当下的文化也显示了一种生猛的活力,一种混乱中的机会。这需要识别,需要发现。这使批评家处在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之中,他难以看清,但又不得不作出判断,因为有无判断和作什么样的判断,将影响未来的路径。“至今,我们都知道,在这后现代空间里,我们必须为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重新界定,继而把进行积极奋斗的能力重新挽回。”(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这才是真正的批评的总体化。这才是真正的认知测绘。真正的理论必须是元理论,真正的批评必须是元批评,它清醒于自身的历史性,它是镶嵌于历史总体中的一部分,它是自反的、能动的,它可能成为创造时势的契机和现实实践的推动力。
杰姆逊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是空间性的,标志着空间性对时间的胜利,换言之,就是历史的终结。那么,我们不妨接着说,好的理论和批评就是要重新超越空间,解放时间。这里所说的时间,不是历史目的论的时间,而是意味着历史的可能性。启动时间,就是让时间再度前进,重新流动起来,这意味着让矛盾显形,从而不断产生新的契机,创造新的机运和时势。
我觉得,作为一个批评家,杰姆逊是有意识地在这样做。我当然不认为他达到了这样的理想目标。但他令人佩服地显示了这样的视野、雄心、能力、技巧。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结 论
重读杰姆逊的书,应该说,现象的分析和具体结论已不重要,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他对大势的判断和那种敢于下判断的气势和把握历史的信心。尤其是他所指出的,面对纷纭复杂的、让人不知所措的文化转折,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姿态和批评态度。这往往让我深感共鸣。他的战略战术构想,包括对各种文化批评的微词,让我有种奇异的感觉,仿佛他是对着当下的中国批评界说的。尽管他的文章的语境是美国,写作时代很多是上世纪80年代。
这让我不禁去想象理想的批评,或者说,当下最稀缺的批评。我想,那是超越形式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的批评。同时,它还要超越一般社会历史批评的模式。它不是从既定的社会历史前提出发,不是以决定论的简单思维,直接走向对文本的思想内容的评判,更不是以文本为素材和入口,去论证某种社会学的结论,印证某种历史学的判断。另外,它也要超越文化研究的清规戒律和政治正确,因为新的文化状况已宣告旧有文化反抗形式和文化批评模式的失败,省略形式或美学分析的英雄式的意义博弈或游击战,往往会被重新吸纳和收编。
理想的批评要在历史与形式的纠缠关系中同时把握文本和历史。它清醒于自身的历史性和叙事功能,放弃立刻建立理论体系的幻想,不停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批评只能是真正的社会历史批评,一种开阔的批评,正如杰姆逊所说,社会历史批评或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是一种和其他的理论方法并列的流派,而是一个平台。它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斡旋于各种理论之间的主导性的调停角色,一个中介者和主持人。
以上构想可能只是我的借题发挥,它或许只代表了我对我们自己的期待。面对新世纪文化,文艺批评不但要有一种新的视野和雄心,还要具备新的能力和技巧。批评家们要试着克服在纷乱复杂的历史文化情势面前的无力感,试着建立一种理解文本和把握历史的信心。
希望我们能摆脱沮丧感,变得更勇敢一些,更高明一些,也更努力一些。
(作者系海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