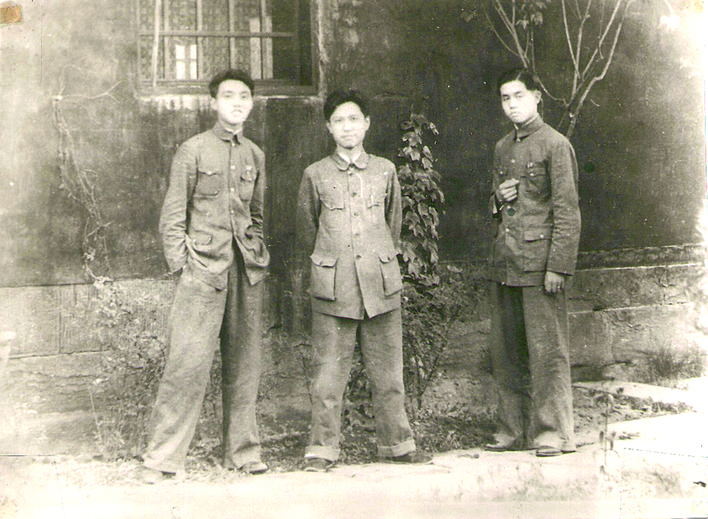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各种组织、学校等,纷纷向大后方撤离疏散,曹禺也随剧专迁往长沙、重庆,最后于1939年4月再迁到川南江安。在江安这个宁静、闭塞的小县城,度过了他难忘的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迎来了曹禺的又一次创作高峰,《北京人》《蜕变》《正在想》等作品相继问世,《家》的改编也酝酿成熟。在这个环境条件比较差的小县城里,曹禺仍然坚持进行大量的戏剧创作和教学,他的执著精神,为话剧事业特别是对抗战戏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在这三年中,曹禺与江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在40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深情地写到: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永远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哺育之恩。曹禺自称在江安时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可称“人杰地灵”。
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大小各级机构的腐败状况,给曹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他耳边时常响起周恩来在1938年同他谈话的声音——“抗战必胜,最后的胜利必属我们中国人民”。创作的激情和冲动让他不能自已,必须一写为快。曹禺决定以一个省立后方医院在抗战初期的遭遇为题材,揭露抗战中大后方的动摇分子和腐朽人物,鞭挞当时黑暗丑恶的现实。
1940年2月初,曹禺快要构思完毕,正准备进入写作阶段。剧专接到妇女工作队的邀请,赴重庆作劳军公演。学校决定4月赴渝公演,演出两个现成的大戏,一个选顾一樵的 《岳飞》,一个是余上沅、王思曾合作的《从军乐》。余上沅觉得一次旅行公演,带两个戏太少了,希望曹禺把正在酝酿的新戏赶写出来。在朋友们信任的催促下,曹禺推托不过,只好答应赶一赶。
曹禺将这出戏取名《蜕变》,构思大体完成后,他请学生季紫剑(季虹,上影厂演员)帮刻钢板,吃住在他家里。季紫剑听说跟曹禺一起工作,心想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满口答应。
第二天,曹禺和季紫剑就开始紧张的工作。曹禺家住江安开明绅士张乃赓的乃庐公馆内,房间在楼上,总共约十五六平方米,外间是饭厅,也是创作室、会客室,靠窗有一个竹制旧书架,靠墙一对旧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方桌;里间是卧室,有一张床,一个矮斗柜,一张小长桌,拥挤不堪。小斗柜紧挨着床,柜上放着纸、笔和煤油灯,煤油灯旁放着一盒火柴。这样,晚上创作灵感来了,曹禺就可以随时抓起笔来写。
饭后,曹禺就与季紫剑共用这张吃饭桌子开始工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曹禺与季紫剑白天同吃、同工作,晚上同榻而眠,闭门谢客,日夜苦干。就连张家的佣人都说:“每天晚上都是人家都睡了,还看见他点起灯写字,早晨我一起来打早火,看见他又在用功了。真像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将来不晓得要干啥子大事哦。”
就这样,季紫剑也了解了曹禺的创作习惯。他发现曹禺在写作时,有时握笔的手指不断地跷动,便是在思考、推敲。曹禺右耳朵边有一个突出的小肉球,写作时,他常用右手不知不觉地去捻弄它,而被他的学生们戏称为“灵感包”。一次,几张蜡纸已经刻完,季紫剑向曹禺索稿,只见他正用右手捻那个小肉球。他问:“万先生,我刻好了,你写好了吗?”曹禺好象没有听见,只顾捻动他耳边的小肉球,季紫剑起身走到曹禺身旁,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句:“万先生,我刻好了。”曹禺猛地一惊,定神一看,是季紫剑在叫他,他生气地说:“你不要催我好不好。”季紫剑猛然醒悟,他这一叫打断了曹禺的文思,忙回到自己座位上,整理已经刻好的蜡纸,以后再不敢中途打断曹禺写作。
曹禺虽已完成了《蜕变》的总体构思,但在具体执笔时,还是反复酝酿。灵感袭来,想到一场好戏或一段对话就奋笔疾书。写完一张就放在一边,到整理时再将它们串在一起。剧本经他反复推敲、修改多次后,才写在江安产的竹纸上。因为长时间的连续熬夜,人已十分疲劳,加上夜晚受了凉,在剧本快要完稿时,曹禺患上了重感冒。
1940年4月15日,大型话剧《蜕变》被剧专带到重庆,在国泰大戏院举行了公演,获得很大成功,轰动了整个大后方和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文学大师巴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国立戏剧学校(1940年7月在江安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已经迁到川南小城江安,他随后由重庆来到江安,看望他的朋友曹禺。
巴金到了江安,就住在曹禺的家中,两人相见,百感交集。当时的江安县城没有电灯,晚上7点后全城漆黑。巴金、曹禺多数时候在一起聊天,两人常对坐在一张长写字台两边,在昏暗摇曳的桐油灯下谈心。他们谈抗日战争,谈社会政治,谈人生感悟,更谈作家的责任与中国戏剧文学的前途……曹禺讲述了自己在江安新写的剧本《蜕变》《北京人》的创作过程,更谈起《家》,他流露出想改编《家》的意思,巴金鼓励他试一试,并对他说:“你有你的‘家’,你有你个人的情感,你完全可以写一部你自己的《家》。”通过几天相互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坚定了曹禺改编《家》的决心。
在江安,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他时常与吴祖光、沙梅等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清茶,一坐就是半天。他们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过往人群。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举止记录下来。有一次,大街上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让他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就尾随这个人。这人原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名黄久安。过了不久,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着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便有点儿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一个亲戚家里躲藏起来。其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万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产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样做豆浆,又怎样点卤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看着、琢磨着,有时还仔细地询问这位老婆婆,临走时,他还给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在江安的日子里,曹禺不断地将他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东西都融于所编剧本之中,成功地塑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和戏剧情节。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曹禺的故事。
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江安的耗子够厉害,一是个头大,二是多,到处都有,无孔不入。吴祖光曾写过一篇曹禺与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江安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有一个厚厚的本子。可一天他打开抽屉时,那本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他很无奈地又重新整理编写,可又一次遭到同样的命运,最后他不得已采取了特殊保存方式,才将剧本完成。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状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大概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后来《北京人》问世,曹禺把耗子巧妙地写进戏里,每逢演到出现耗子的台词时,引起了极有“喜剧味”的舞台效果。以致于四十多年以后,江安代表到北京拜望曹禺时,他还问到,江安的茶楼还多吗?耗子还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