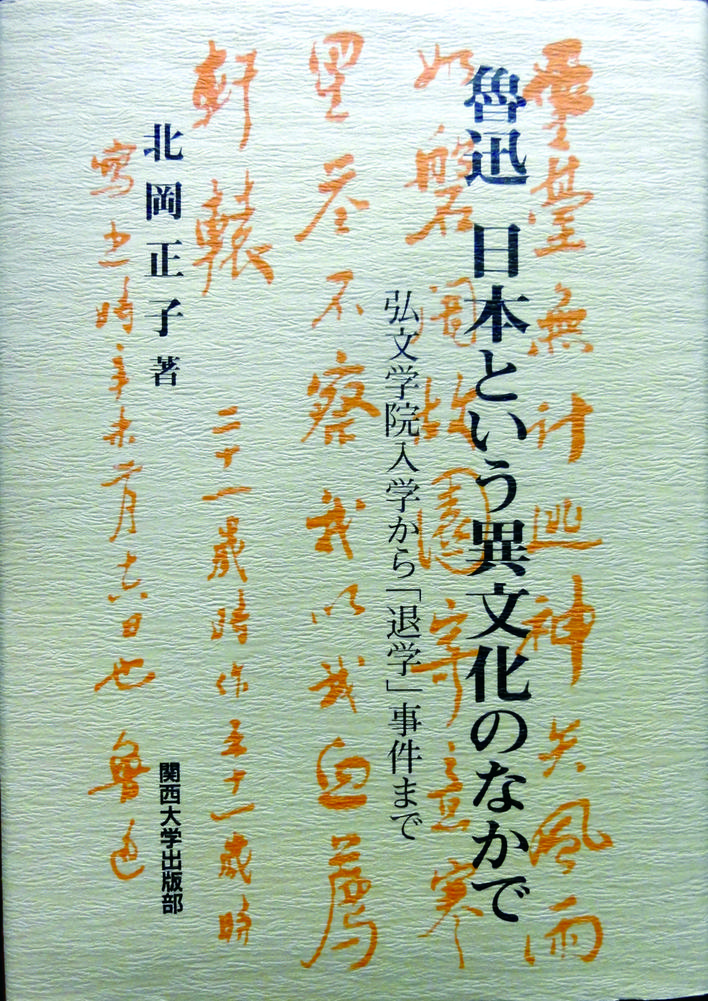今年,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读鲁迅的文章,是1954年,那时我刚入大学中国文学科不久,学习汉语才两三个月。读的是《孔乙己》。对于一个连初级汉语都没念完的学生来说,拿这篇作品当课本,实在强人所难。选来做课本的理由,好像是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这篇又短,于是“就它吧”。老师要求课外拼命查词典练发音,课上紧赶慢赶不说,下次上课时学过的地方还都得背诵下来。所以,时至今日还会脱口而出:“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学生们之间见了面,也是“我都快要背死了!”第二年升大二,讲读课本选的是《呐喊》。一本红皮书,现在还留作纪念,版权页上写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1月北京重排第1版,1954年1月北京第四次印刷。我觉得战后在书店书架上能够最早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的作品。
那时的我开始参加鲁迅研究会。该会是无所属的自立研究会,会员有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大都是20多岁的青年。每周集聚一次,读鲁迅作品并交换意见。研究会充满了一股思考风气,那就是学习鲁迅精神从而确立起自己在战后日本社会的生活方式。我们当时是把人民中国的青春与自己的青春重叠在一起,并通过读鲁迅迈出走向未来的一步。研究会的集体阅读讨论的记录,登载在誊印版薄薄的《鲁迅研究》杂志上。研究会的规模不大,但杂志的读者却遍布日本全国。研究会大约持续10年,杂志出了30几本便结束了。
可以说参加这个研究会,左右了我此后的人生。在鲁迅研究会里,我和大家共同阅读了鲁迅的很多作品。我们相互确认作品文意,直到都能理解透彻,也相互切磋探讨如何读取鲁迅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就是这样,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一篇一篇地去解读鲁迅的作品。在这潜移默化当中,不论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自问要是鲁迅处在这样的时候会去怎样做,同时也会联想起在研究会上大家通过讨论所获得的共识,并以此来衡量自己。在研究会上,我遇到很多值得尊敬的学长和朋友。其中就有已仙逝他界的丸山升和伊藤虎丸。当我遇到困难,感到气馁时,因鲁迅而与他们结下的友情曾多次给予我以勉励,使我能够走到今日。
我在研究生院写硕士论文,是1960年代初。题目是《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当时关于留学时期的鲁迅,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探明。有一天,我在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书,是滨田佳澄的《雪莱》,觉得其中的某些表达方式和内容与《摩罗诗力说》里关于雪莱的部分很相像。我确信这就是《摩罗诗力说》第六章的材源并写进论文里。而查清其他部分的材源,则是自那以来十几年以后的事了。我把检读的结果,以《〈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为题,从1972年到1995年(中间有很长时间的休载期)在中国文艺研究会杂志《野草》上连载了24回。我的文章虽然只是“笔记”,然而其能刊载到最后一篇,全都仰仗持续了40年的中国文艺研究会和今年出到第88号的《野草》杂志。
读过我这篇文章的人问我:“资料是到匈牙利和波兰去查的吗?”我的回答是:“不,我从未去过欧洲。”可认为是材源的书籍,若日本图书馆未藏,便委托我所在的大学图书馆去向外国图书馆索寄缩微胶卷。另外,在《摩罗诗力说》中还有不少作品并未被译成日语,尤其匈牙利和波兰的诗歌作品,译成日语的就更少。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几篇这样的作品,全是因为有汉译的缘故。有位先生特意从中国寄赠宝贵的翻译过来。我不曾忘记那时的感动和感谢的心情。而且我以为,鲁迅到日本留学时的20世纪初,正是日本只盯着先进的西欧走向近代化的时期,然而鲁迅的目光所向,却也同时扩及到东欧,今天的中国学者不仅继承了对鲁迅的尊敬,也继承了鲁迅那种睿智的眼光。
我出生于鲁迅逝世的那一年,今年75岁。从曾经工作过的大学退休已经5年。我在供职30多年的大学里跟学生们恐怕是没少读鲁迅的作品。《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几乎都读了。杂文也读得相当多。通过在教室里的学习而以鲁迅为毕业论文题目的学生,每年都有二三名。也有学生作关于鲁迅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我的承担于教学场所的工作结束了。
而今我想要完成的不是“笔记”,而是货真价实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我在与鲁迅的反复而持续不断的对话中苦战。我每天都会感到从《摩罗诗力说》里新发现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我在年轻时学汉语并与鲁迅相遇,现在已踏上人生旅程的黄昏,却仍在前行的途路不断获得鲁迅的教示。
(作者系原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