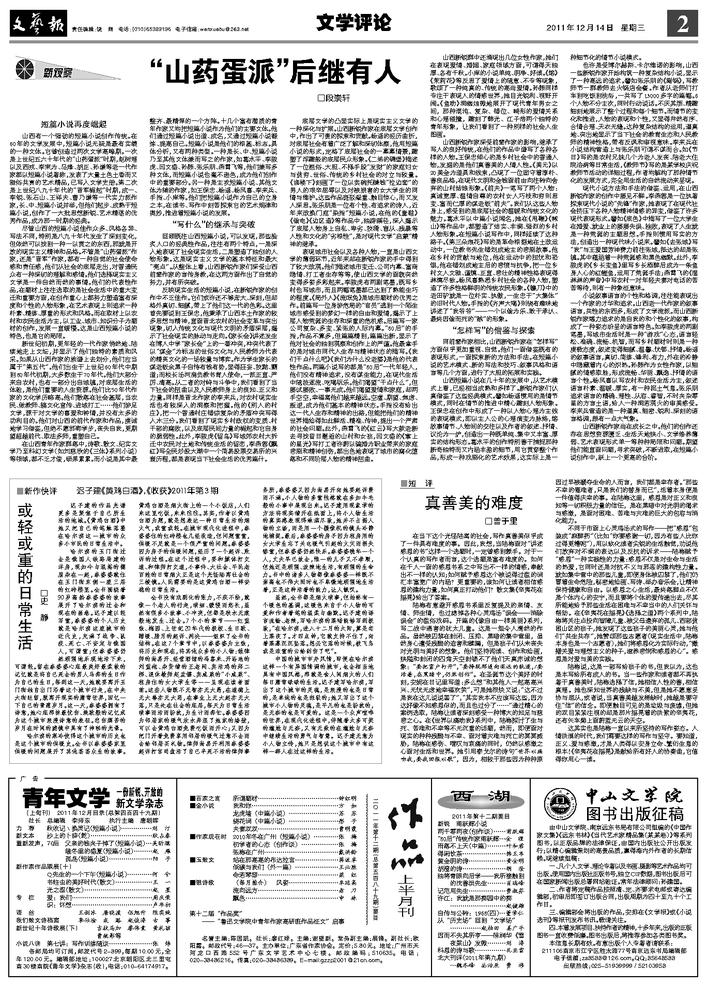短篇小说再度崛起
山西有一个强劲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在60年的文学发展中,短篇小说无疑是最有实绩的一种文体。它曾创造过两次文学高峰期。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赵树理以及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老一代作家都以短篇小说著称,发表了大量土色土香而又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已写入文学史册。第二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晋军崛起”时期,成一、李锐、张石山、王祥夫、曹乃谦等一代实力派作家,长、中、短篇小说并举,但他们起步、成熟于短篇小说,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新锐、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成为那一时期的经典。
尽管山西的短篇小说佳作众多、风格各异、写法不同,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依然可以找到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品格。不管是“山药蛋派”作家,还是“晋军”作家,都有一种自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从社会的底层走出,对普通民众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感情。他们选择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在题材上往往选取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迁和重要方面,在创作重心上都努力塑造富有深度和个性的人物形象,在艺术表现上则追求一种朴素、精练、厚重的形式和风格。而在取材上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以工业、城市、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创作,发展一直缓慢。这是山西短篇小说的特色,也是它的局限。
新世纪初期,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悄然地、陆续地走上文坛,并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素质和风采。如果从山西作家的族谱上去划分,他们应当属于“第五代”。他们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大多数生于70年代。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也有一部分出自城镇,对底层生活的体验,是他们重要的人生资源。他们比50年代作家的文化学历略高。他们散落在社会基层,当农民、做教师、搞文化宣传、进城打工……他们涉足文学,源于对文学的喜爱和钟情,并没有太多的功利目的。他们对山西的前代作家和作品,虔诚地学习借鉴,但绝不愿邯郸学步,丧失自我,更期望超越前代、取法多师,重塑自己。
在山西青年作家群落中,诗歌、散文、纪实文学乃至科幻文学(如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等领域,都不乏才俊,硕果累累。而小说是其中最整齐、最精悍的一个方阵。十几个富有潜质的青年作家又均把短篇小说作为他们的主要文体。他们通过短篇小说出道、成名,又通过短篇小说锻炼、提高自己。短篇小说是他们的根基、标志。具体分析,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中、短篇小说乃至其他文体兼而写之的作家,如葛水平、李骏虎、闫文盛、孙频、张乐朋、燕霄飞等,他们兼写多种文体,而短篇小说也毫不逊色,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另一种是主攻短篇小说、其他文体为辅的作家,如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手指、小岸等。他们把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在读书、写作中刻苦探索它的艺术规律和奥妙,推进着短篇小说的发展。
“写什么”的继承与突破
回顾既往山西短篇小说,可以发现,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性作品,往往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入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二是塑造了独创的人物形象。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和最大“亮点”。从整体上看,山西新锐作家们深受山西前辈作家的言传身教,在这两方面作出了自觉的努力,并有所突破。
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在新锐作家的创作中不乏佳作。它们或许还不够宏大、深刻,但却格外真切、细腻,带上了他们这一代的色彩。这里首先要说到王保忠,他秉承了山西本土作家的较多思想与精神,直面晋北农村的社会变革与突出现象,切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深层,揭示了社会现实的脉动与走向。《家长会》讲述发生在博人中学“家长会”上的一番冲突,冲突代表了以“煤金”为标志的世俗文化与人民教师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一场较量与博弈。作为学生家长的煤老板余黑子自恃有钱有势,显得狂妄、狡黠、霸道;而校长汤河肩负教书育人使命,一派正直、严厉、清高。从二者的对峙与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当下社会的扭曲以及人民教师身上的良知、正义和力量。同样是晋北作家的李来兵,对农村现实生活也有较深入的洞察和把握。他的《别人的村庄》,把一个普通村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写得入木三分。我们看到了现实乡村政权的变质、村干部的腐败,以及底层民间力量的崛起和它自身的脆弱性。此外,李骏虎《留鸟》写城郊农村大拆迁中农民对土地和传统生活的留恋,李燕蓉《飘红》写全民炒股大潮中一个简易股票交易所的兴衰历程,都是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优秀篇什。
底层文学的凸显实际上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深化与扩展。山西新锐作家在底层文学创作中,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杨遥的经历曲折,对底层社会有着广泛了解和深切体察,他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定格了底层社会的一幕幕情景,雕塑了浮雕般的底层民众形象。《二弟的碉堡》描述了一位粗俗、大胆、不择手段“发财”的家庭妇女与贫穷、世俗、传统的乡村社会的对立与较量。《谯楼下》刻画了一位以卖碗托赚钱“拉边套”的男人的艰辛屈辱以及对被损害的女大学生的同情与维护。这些作品斑驳凝重、触目惊心,而又发人深思。张乐朋是一位有个性、有追求的诗人,近年来改换门庭“染指”短篇小说,在他的《童鞋》《偷电》《边区造》等作品中,独辟蹊径,深入揭示了底层人物身上自私、卑劣、狡猾、盲从、残暴等人性和文化的“劣根性”,是对现代文学“启蒙”精神的继承。
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却在新锐作家的手中得到了较大改观。他们描述城市变迁、公司内幕、富商隐情、打工者生存等等,使山西文学的面貌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李骏虎有两副笔墨,既写乡村也写城市,而且两幅笔墨都已达到了熟能生巧的程度。《局外人》《流氓兔》是城市题材的优秀之作。前篇写一位身涉危局的“官员”逃到一个陌生城市感受到的梦幻一样的自由和爱情,揭示了上层人物荒诞的生存和深重的危机感。后篇写一家公司复杂、多变、紧张的人际内幕。“80后”的手指,作品不算多,但篇篇精到,篇篇出新,显示了他对社会的独到观察和创作上的严谨。他最拿手的是对城市同代人生存与精神状态的描写。《我们干点什么吧》《我们为什么没老婆》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两篇小说写的都是“80后”一代年轻人,他们没有精神追求,没有谋生能力,在现代生活中随波逐流、吃喝玩乐。他们渴望“干点什么”,但屡试屡败、一事无成。他们渴望爱情和家庭,却两手空空,幸福离他们越来越远。空虚、期望、焦虑、叛逆,成为他们基本的精神状态。手指没有给出这一代人生存和精神的出路,但能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描绘得如此鲜活、精准、传神,提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此外,燕霄飞的《红云》写大款老新去寻找昔日邂逅的山村和女孩,闫文盛的《掌上的星光》写打工者许蔚以骗婚为职业带来的家庭悲剧和精神创伤,都出色地表现了城市的腐化堕落和不同阶层人物的精神扭曲。
山西新锐群中还涌现出几位女性作家,她们在表现爱情、婚姻、家庭领域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各有千秋。小岸的小说单纯、明净、好读。《熔》《茉莉花》等反思了爱情上的随意、不专等现象,歌颂了一种纯真的、传统的高尚爱情。孙频同样专注于表现人的情感世界,她目光锐利、视野开阔。《鱼吻》洞幽烛微地展开了现代青年男女之间,那种混沌、复杂、错位、畸形的爱情关系和心理碰撞,雕刻了韩光、江子浩两个独特的青年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社会人生图画。
山西新锐作家深受前辈作家的影响,继承了写人的良好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谱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王保忠倾心的是乡村社会中的普通人物,发掘的是他们真善美的人情人性。《美元》以20美金为道具和线索,凸现了一位固守着淳朴、善良品格,在现代文明和金钱面前由向往转向舍弃的山村姑娘形象。《前夫》一笔写了两个人物:真诚宽厚、温情自尊的农村女人巧枝和穷则思变、富而仁厚的煤老板“前夫”。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的是底层社会的温暖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葛水平以中篇小说闻名,她在《甩鞭》《喊山》等作品中,都塑造了结实、丰满、强烈的乡村人物形象。在短篇小说写作中,同样延续了这种路子。《第三朵浪花》写的是革命根据地在土改运动中,一位教书先生错划成地主的悲剧故事。他在乡村的贡献与地位,他在运动中的担忧和恐惧,他在错划成地主后的悲愤与抗争,把一位乡村文人文雅、谨慎、正直、悲壮的精神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杨凤喜熟悉乡村社会的各种人物,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传统农民形象。《镰刀》中的老田驴就是一位朴实、执傲,一生忠于“大集体”的旧时代人物。手指的《齐声大喝》则饶有趣味地讲述了“我爷爷”——一个以偷为乐、敢于承认、最终因偷而死的“贼”的形象。
“怎样写”的借鉴与探索
同前辈作家相比,山西新锐作家在“怎样写”方面似乎更加重视、自觉。他们一面借鉴既有的表现形式,一面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法。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模式、新的写法和技巧、叙事风格和语言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拓展和实践。
山西短篇小说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从艺术模式上看,已经相当成熟和多样了。新锐作家们认真借鉴了这些经典模式。譬如杨遥惯用的是情节模式,同时在情节的推进中精心雕刻人物形象。王保忠在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以人物心理为主线的表现模式,即以主人公的心理演变为脉络,熔故事情节、人物间的交往以及作者的叙述、抒情、议论为一炉,创造出一种既单纯、集中又丰富、厚实的结构形态。葛水平的创作特别善于捕捉那种新奇独特而又内涵丰盈的细节,用它贯穿整个作品,形成一种戏剧化的艺术效果,这实际上是一种细节化的情节小说模式。
也许是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影响,山西一些新锐作家开始构筑一种复杂结构小说,显示了一种高远的追求。譬如张乐朋的《涮锅》,写教师节一群教师去火锅店会餐。作者从老师们打车到吃饭到洗浴,一共写了13000多字的篇幅。6个人物不分主次,同时行动说话。不厌其烦、精雕细刻地展示了整个过程和每个细节。而情节的变化和推进,人物的表现和个性,又显得井然有序、合情合理、天衣无缝。这种复杂结构的运用,逼真地、突出地显示了当下社会的教育生态和人民教师的精神性格,带有反讽和审视意味。李来兵在小说结构营造上与张乐朋可谓不谋而合。如《节日》写的是农村兄妹几个为老人发丧、陪老大住院治病等日常生活,《教师节》写的是某学校庆祝教师节活动的详细过程,作者均解构了那种情节化的发展方式,完全用生活的自然流动来呈现。
现代小说方法和手法的借鉴、运用,在山西新锐作家的创作中屡见不鲜。李燕蓉是一位执著探索现代小说的“先锋”作家,她表现了在现代社会挤压下各种人物精神情感的异变,借鉴了许多现代表现形式。譬如《底色》中描写了一位大学生在婚爱、就业上的屡屡失误、挫败,表现了人生就是一种荒诞的主题思想。手指则惯用写实的方法,创造出一种现代味小说来。譬如《去张城》写“我”与王爱国劳神费力前往张城,抵达的却是张镇。其中蕴涵着一种荒诞感和黑色幽默。此外,李骏虎的《乡长变鱼》里写乡长酒醉后成为一条鱼身人心的红鲤鱼,运用了荒诞手法;燕霄飞的《湿淋淋的声音》中写农村一对年轻夫妻对电话的苦苦等待,则有一种象征意味。
小说叙事语言的个性和格调,往往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才华和追求。山西老一代作家的叙事语言,共性的东西多,形成了文学流派。而山西新锐作家竭力追求的是自我的和个性化的叙事,构成了一种姿态纷呈的语言特色。如李骏虎的两副笔墨,写城市生活时是一种“游戏”心态,语言轻松、准确、流畅、机智,而写乡村题材时则是一种虔敬态度,叙述变得细腻、温馨、忧郁、抒情。杨遥的叙事语言,真切、简练、锋利、有力,外在的冷静中隐藏着内心的炽热。孙频作为女性作家,以细腻的情感取胜,形成流畅、华丽、飘逸、抒情的语言个性。杨凤喜以写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叙述语言朴素、温暖、厚实,有一种泥土气息。张乐朋追求语言的精确、理性、从容、睿智,不时夹杂零星的方言土语,给人一种洞若观火的审美感受。李来兵营造的是一种逼真、细密、锐利、深刻的语言格调,颇有一点大气象。
山西新锐作家尚在成长之中。他们的创作还存在思想资源匮乏、生活天地狭小、文学修养薄弱、艺术表现形式单一等种种局限和问题。期望他们能直面问题,寻求突破,不断进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