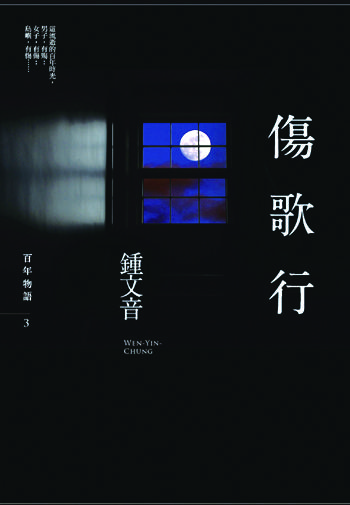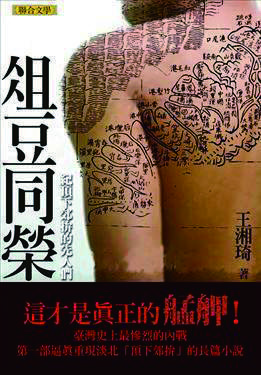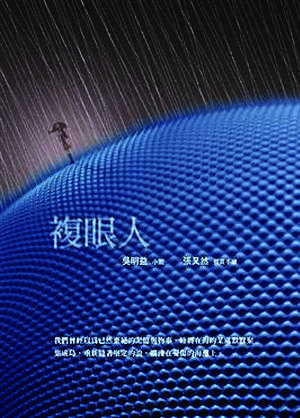贺淑玮在评说《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时认为:2011年是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台湾作家交出了傲人的成绩:一份绝对可以昂然挺立的漂亮书单。
台湾“特有种”小说
获得“开卷好书奖”的台湾本地作家小说创作有吴明益的《复眼人》、纪蔚然的《私家侦探》、林俊颖的《我不可告人的乡愁》等。《复眼人》以科幻框架和写实细节展现台湾(或整个世界)面临的生态灾难。作者设想报载的太平洋上巨大垃圾涡流(俗称“垃圾岛”)撞上台湾,台湾东部海滩从此被清除不完的垃圾所覆盖。然而在此之前,台湾已因生态环境恶化而暴雨不断、海水上涨,致使大学教师阿莉思与其丹麦籍丈夫所建的海边住宅、阿美族女子哈凡的咖啡店等被海水所淹。小说由此引出了阿莉思的好朋友、布农族知识分子达赫和他在按摩店结识的情人小米等,展现了阿美、布农等原住民族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文化状况及其屈辱艰辛的生活处境。小说的另一线索是设想太平洋上“瓦忧瓦忧”小岛上的原始族群为避免资源匮竭而有每家次子需驾舟出海、自生自灭的习俗;而阿特烈出海后,所幸漂上垃圾岛得以生存,并随着垃圾岛撞上台湾海滩,为阿莉思所救。时值阿莉思因丈夫和儿子上山攀岩失踪未归,阿特烈的到来抚慰了阿莉思的心灵创痛,也以其特殊的野外生存技能协助阿莉思寻找小儿踪迹。此外,多年前参与台湾公路建设的德国钻探专家薄达夫和挪威海洋专家莎拉为考察垃圾岛事件来到台湾,由此回顾和反思了当年隧道建设的艰辛和对生态的破坏,讲述了莎拉父亲阿蒙森由捕鲸人转变成反对猎杀海豹、鲸鱼并为此英勇献身的生态保护者的故事。小说多条线索并进而又环环相扣,丰富的想象力使一个个故事都能引人入胜。
小说写的是经日积月累而悄然发生的灾难,杨照称为“日常庸俗的毁灭”,以区别于近年来好莱坞环境生态电影中那“一夕之间”的毁灭(杨照:《毁灭的日常庸俗——读吴明益的〈复眼人〉》)。小说中除了垃圾岛撞击台湾以及若隐若现幽灵般的“复眼人”设计略带科幻色彩外,其余大多细节是写实的,就是现实中的普通人及其生活。好莱坞式的灾难固然耸动视听,但观众觉得离自己还远;而《复眼人》所写大部分是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真实事情,虽然仅是日常、渐进、悄然发生的“毁灭”,却因人们对它熟视无睹才更为可怕,小说也因此有了撞击人心的警醒意义。
小说的另一“好看”之处是其中流转着友爱、温润的人情暖流,十分感人。来自不同国家、族群,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们相互关爱,相濡以沫。然而就是这群善良的人们却在遭受着无法抵抗的灭顶之灾,这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鲁迅语),小说因此具有了撼人心扉的悲剧力量。
陈建忠将《复眼人》称为“特有种”小说,并解释 “特有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台湾独有的“原生种”;另一则是指特别“带种”的小说家——不爽现实的他们带领读者揭穿这个世界的假面,让希望的天光可以从文字的缝隙中泄漏出来。按此定义,纪蔚然的《私家侦探》亦属此列,李维菁就称纪蔚然为“台湾特有种侦探”。
纪蔚然是台湾著名剧作家、大学教授,却出人意外地写出一部侦探推理小说。《私家侦探》的主角吴诚本是剧作家和大学戏剧系教授,因厌倦于学院的迂腐僵化和剧场的肤浅浮夸,突然辞去教职并退出戏剧界,在卧龙街小屋挂牌当起私家侦探,却真的遇见了台湾从未有过的连环杀人案。没有专业训练和专用设备的吴诚只靠眼睛、耳朵和一双腿,从网络“维基百科”查询资料,探案过程中自己反被当做嫌犯。小说有着作者一贯的自虐并自乐的幽默笔调,能让读者一边笑一边痛而达到“痛快”的效果(李维菁《纪蔚然——台湾特有种侦探》)。因此《印刻》主编蔡逸君认为它不只是一本侦探小说而已,作者其实是“诊断我们这个病态台湾社会的医师”。
作品艺术上的特点是有意模糊虚实的界限。小说主角的身份与纪蔚然本人有许多重叠,出现的地景(街道、公园、商店)名称都是完全真实的,使得读者以为小说人物的所作所为就在大家平常起居熟悉的大街小巷、房中屋外同步发生,由此营造出虚构小说的临场真实感。这一点,与《复眼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岸题材文学创作
台胞返乡探亲、台商投资大陆、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随着两岸交往的一波波热潮,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也应运而生。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居住于大陆的台湾作家以台湾人的大陆生活为题材的创作。章缘为台南人,1990年留学纽约,成为旅外华文作家。2004年她来到北京,2005年后常年居住于上海,并在《上海文学》《文学报》等大陆报刊上发表作品。2011年6月其小说《最后的华尔兹》为《新华文摘》转载。章缘文笔简洁精致,作品直扣人性深处,特别对女性心理有细腻的把握,近作常以台湾人(特别是台商家属)在上海的生活为题材。不过其兴趣并不在原配小三之类的纠葛,也不是追逐财富的商战故事,而是衣食无忧的富商太太们进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在跳舞、打乒乓的悠闲生活中接触大陆人事时的情感波纹、内心幽微。章缘自称这种因不同地域文化相碰撞而获得新鲜视角的创作为“越界书写”。章缘在美国时,因文化的隔阂而有题材枯竭之感,北京和上海则让她觉得“到了一个写作者的天堂了”,她努力学习上海话,相信在上海住得越久,上海的林林总总就会更内化为她的一部分,那么她就能写出具有“真滋味”且是台湾人视角的“上海的故事”(《越界书写:台湾留美作家在上海》)。陈建忠在评说其2011年出版的小说集《双人探戈》时指出:看来,台商族已成为台湾境外文学生产的主角,他们在中国大陆有自足的生存机制,但又和中国大陆的变动不可或分;或许有可能继在美国的“留学生文学”,成为新崛起的“台商族文学”亦未可知。
2011年4月,从文坛“失踪”了30年的蒋晓云由“印刻”出版《桃花井》,被称为“春天文学出版界的最大收获”、“小说史的一则传奇”。小说写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李谨洲,历经大半生颠沛流离,等到了两岸开放探亲后,重返家乡寻回失散的长子,又找了个桃花井的寡妇董婆续弦,期望在家乡安度余生,然而因两岸隔阂、城乡差距、父子代沟、个性冲突、私利挤压等缘由,问题接踵而至,幸好这位“台湾老头”都能以智慧加以妥善解决,终能遂其叶落归根之愿。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近年来“眷村”题材格外红火,作者却认为当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未必都与眷村有关系,有些“纯难民”其实与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太多渊源或理念交集。不同于眷村的忠君爱党气氛,他们对当时国民党的不信任常常溢于言表。作者是有意为这些自己所熟悉的非主流群体留下时代的影像。
历史、家族、地方志小说
以历史、家族和某个特定地方为书写对象的作品,近年来在台湾十分兴盛,2011年的小说写作延续着这一势头。如钟文音出版了长篇小说《伤歌行》,完成其经营多年的“岛屿百年三部曲”。作者认为这是“变形的家族书写”,与其称之大河小说,不如说是“百姓史小说”。三部曲着笔于岛屿的“野性”——平民百姓的生命力和草根性:第一部《艳歌行》描绘台北都会女子的情欲癫狂与拉锯;第二部《短歌行》描绘岛屿男子的生死际遇和早逝;第三部《伤歌行》则勾勒家乡云林的女性生命史,“以迤逦百年为经、苍茫云林为纬,道出了岛屿之南钟姓、舒姓两大家族的悲欢际遇”。(蔡昀臻专访《长成唯一的那棵树——钟文音谈三部曲写作》)
颇具特色的地志书写,当属王湘琦的《俎豆同荣》和杨丽玲的《艋舺恋花恰恰恰》两部小说。前者叙说咸丰三年,因渡头利益以及神明信仰等矛盾,艋舺的“顶郊”泉州三邑人与“下郊”同安人爆发了“顶下郊拼”。以黄龙安为首的三邑人攻入并焚烧了同安人居地八甲庄,“下郊”首领林佑藻率庄人奋力抢回城隍爷金身,败逃辗转至大稻埕,另图新局。作者称这是一个“从失败中再站起来的故事”,他尝试“藉此思索台湾人性格中坚忍奋发又冲动绝望的宿命”。“俎豆同荣”本是清朝台湾巡抚邵友濂在祭祀汉番战役阵殁者时所题匾额,包含着对交战双方一体礼敬,望其和平相处、消弭争斗之意(王湘琦《俎豆同荣》自序)。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表明他同样的信念和用心。
《艋舺恋花恰恰恰》的作者杨丽玲认识到:“历史需与故事共同存在,大历史之下,被忽略小人物的故事更让人感动。”她运用时空交错笔法,穿梭在清末、日据到光复与上世纪90年代之间,以大目坤仔在除夕之夜被人砍杀于路旁为小说的开场,然后以“亡灵”的多向度历史观照之眼,“穿透自身、穿透时空,看见自身的生命史,看见艋舺蔡、陈、张三大家族的没落史,看见‘查某人花’的艋舺娼妓史,也看见这个城市边缘之域的流变史”(杨翠《在时空穿堂中迷走》);并加上具有记者身份的死者之妹所做的明查暗访,共同“细细织造出一张属于艋舺的底层面貌”。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读者“在这些刀光剑影的黑道追杀,或者男贪女爱的咸湿色情之外,也可以思索自身和历史发生的关系”,并看见更多的自尊、温暖、幽默,展现更大、更宽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