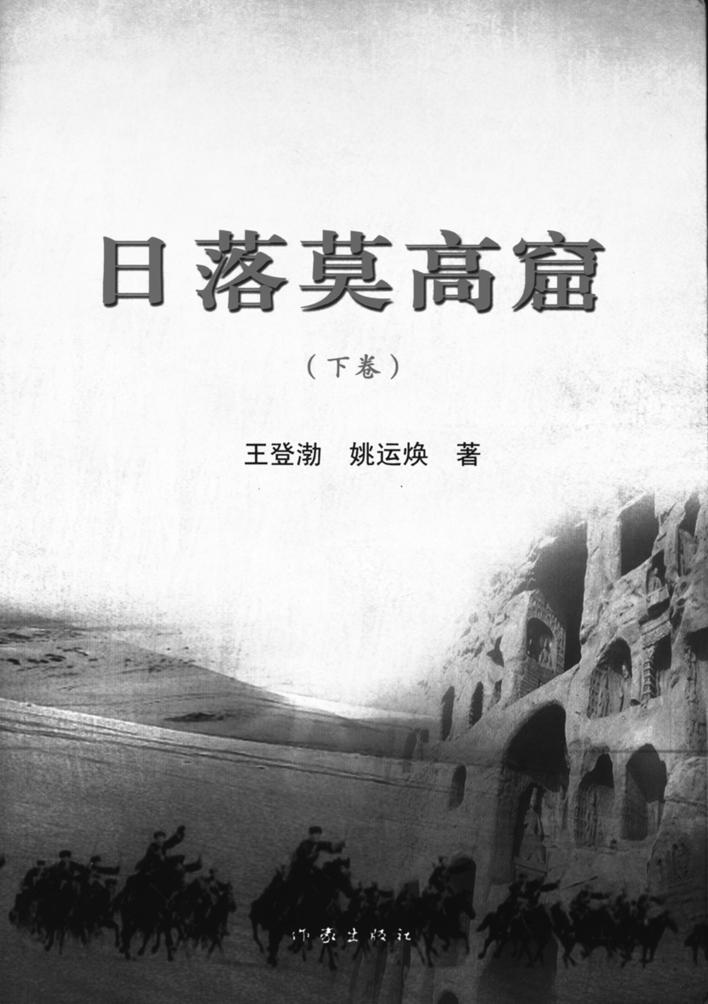由王登渤、姚运焕创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日落莫高窟》这部小说,事关中俄现代史上一宗重大事件。上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沙皇属下阿连阔夫带领的阿尤古斯军团败退新疆,之后该军团又将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变为兵营。刚被俄国及欧洲探险家盗劫过的东方艺术圣地又一次遭到俄国沙皇败军的蹂躏。小说故事牵涉到新疆与甘肃,在这片几乎横穿了半个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时逢乱世的中国人开始和类似阿尤古斯沙皇败军这样的困兽斗智斗勇。小说开始是两条线索平行发展:新疆督军谷达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韬略,最终使这支军团解除了武装,为日后将其驱赶到敦煌埋下伏笔;而在敦煌,女艺术家白草与当地驻军首领邹季南联手对莫高窟文物的整理、保护同时也在展开。当两条线索重合后,故事叙述逐渐走向高潮,视敦煌艺术为生命的弱女子白草和守土有责的军人邹季南团结当地士绅,为了敦煌民众的生命安全与莫高窟的文物安危,与阿尤古斯军团的败军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斡旋与较量。整个故事所涉人物有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军人、前沙俄驻伊犁外交官、社会贤达、艺术家、土匪、乞丐、日本间谍等,宏大严谨的叙事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使这部小说极具阅读的趣味。在这种一直处于高涨趋势的故事展现中,白草与邹季南爱恨情仇的命运悲剧、阿连阔夫及手下哥萨克骑兵悲惨绝望的命运结局,都在作者清晰而又出奇的场景中一一上演与落幕。这部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及情节,几乎都是因为每一场冲突或重要事件的需要而出现或被设置,全篇叙述风格简洁明快、矛盾冲突集中,在险象环生中有强烈的节奏感,极富戏剧化特征。
戏剧化特征曾是古典主义小说表现的重要特征,现当代小说的发展趋势是逐渐淡化或远离这种特征。现当代小说通常是在重大情节或矛盾冲突上用减法,在人物行为的琐碎细节上用加法。现当代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历史的事件常常被淡化为背景,人物行为的偶然性却得以无限放大。小说艺术当然是以人物表现为主体,如果以人物为原点,现代小说的表现可视为向内转,向人物内部无限地挖掘,或者是侧重于微观世界的表述;而古典主义的小说,则是人物向外部开放,无限地接近于事件,侧重于宏观世界的表述,因而戏剧化的或表演式的矛盾冲突成为其叙述的风范。正是电视剧的兴起,使戏剧化的这种表现形式以更大的规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很多观众喜爱这种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这让一些自视清高的小说家不屑一顾,认为那是通俗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在书斋中产生的对于古典艺术表现形式的蔑视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
笔者认为,历史题材的小说所表现出的这种古典主义式的回归,对今天逐渐迷失在琐碎细节中的小说叙述风格是一种矫正。在这样的意义上,《日落莫高窟》这部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回归古典的趋势,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同时,这部小说也明确地标示出小说故事与真实历史之间确实有着一道不能混淆的界限。
现当代许多历史小说文本的叙述者总是自信自己能够通过无限的偶然性细节,直抵历史事件的深层,揭示历史事件在更高层面的真实,从而跃身一变,将真假不分的故事混同于历史,将自己变为历史学家的导师。许多以古代或近现代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作者常常是在这样一个真假判断中,在试图评判历史是非的狭隘的历史观中创作出大量历史不像历史、小说又不像小说的所谓历史小说。如果缺乏学术精神的历史小说作者以历史学家或历史评判者的至高至上者自居,只能歪曲或损害真实的历史。在已有历史现象的表层下,历史小说的作家能不能有自知之明不再冒充历史学家,不去担当历史评判者的角色,以便能够在审美的道路上行走得更远,以满足人们欣赏与情绪排遣的不同需求,似乎是当今电视剧兴起后给文学表现提出的一道难题。
事实上在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像古希腊荷马的两部口传史诗,在人们数千年的赞赏中,也一直是作为文学作品而流传,谁也不会将其当做历史著述来阅读,这无疑具有艺术化石与艺术标本的作用。
在《日落莫高窟》这部小说中,作者并未标榜自己这部小说为历史小说,但小说文本所涉人物与情节又都是在已有历史事件的河岸中产生与穿行,历史长河中的无数细节,并非按照历史学家的考证,而几乎都是按照作者艺术表现的需求,在一片人烟罕至的浩瀚沙漠中以文学的方式戏剧般地铺展开来。这部60多万字的作品,在整体的叙述上没有自以为是地充当历史学家的角色对历史事件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小说一开始就毫无遮掩地运用戏剧化的表现技巧,比如分镜头式的情节转换、蒙太奇式的空间穿插、悬念与矛盾交替、情景与抒情交融等手法的反复使用。在这一点上,使这部小说与众多的小说区别开来。小说创作到了现当代,越来越疏远戏剧化的表现方式,表现历史题材的小说,大多追求删繁就简,试图直接去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此,表现人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一些人那里就等同于生活,表现历史题材的小说故事就等同于历史,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误区。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要么是虚构的,要么是非虚构的,这之间几乎没有调和的道路,如果将虚构融入非虚构,那答案只有一种,即虚构,非虚构在此情况下就变得永远没有可能。所以文学作品只能是虚构的,真正的历史著述必须是非虚构的。非虚构的作品与文学没有关系。纪实与历史著述面对表现对象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叙述,几乎没有过多的叙述自由。但是小说,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真实地描摹对象,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或娱乐需要,比如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在真实与写意、具象与抽象之间到底孰轻孰重,确实是一目了然。
这部小说由于具有比较纯粹、直白的戏剧化叙述角度,因此人物的形象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敌我之间、官匪之间的话语展现也是平等的。尤其要做到敌我之间、即沙皇所属军团与我方之间的平等展现,这对任何一个中国作家来说,都绝不是容易的事情。鸦片战争之后,沙皇俄国勾结西方列强屡次瓜分中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几个勘界议定书,在19世纪后半叶20多年的时间,割走我东北、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这些沙俄的败军流窜至我国境内,试图祸乱西北,并将西北作为他们反败为胜的根据地。对此,故事的叙述者对这些残兵败将仍然表现出了人道情怀,而当时中国人的好客与善良,也逐渐也消磨了这支桀骜不驯残军的意志。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国家最高当局政令不畅,我国西北的政府兵力又孱弱到几乎无法应对任何大小规模的战争。在这样的危局中,如果没有小说故事中所呈现的曲折与智慧,要将这支困兽之军彻底瓦解,并非易事。最终事态得到平稳控制,这种结局可能是历史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故事叙述中的事实,因为故事的展现过程与历史的展现过程并不完全相同。
故事的展现过程是戏剧效果的体现,因而也是戏剧本质或艺术本质的需要。小说可以选择真实,也可以不选择真实,小说创造了小说叙述中的事实,这种事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也没有必要苛求其与历史真实相符。正因为故事中叙述事实的建立,使得这部小说与真正的历史著述完全区别开来,显示了自己完整的艺术价值,这样也是对于真正历史的承担与负责。如果将这样一部小说冒充历史著述,那反而是对于历史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