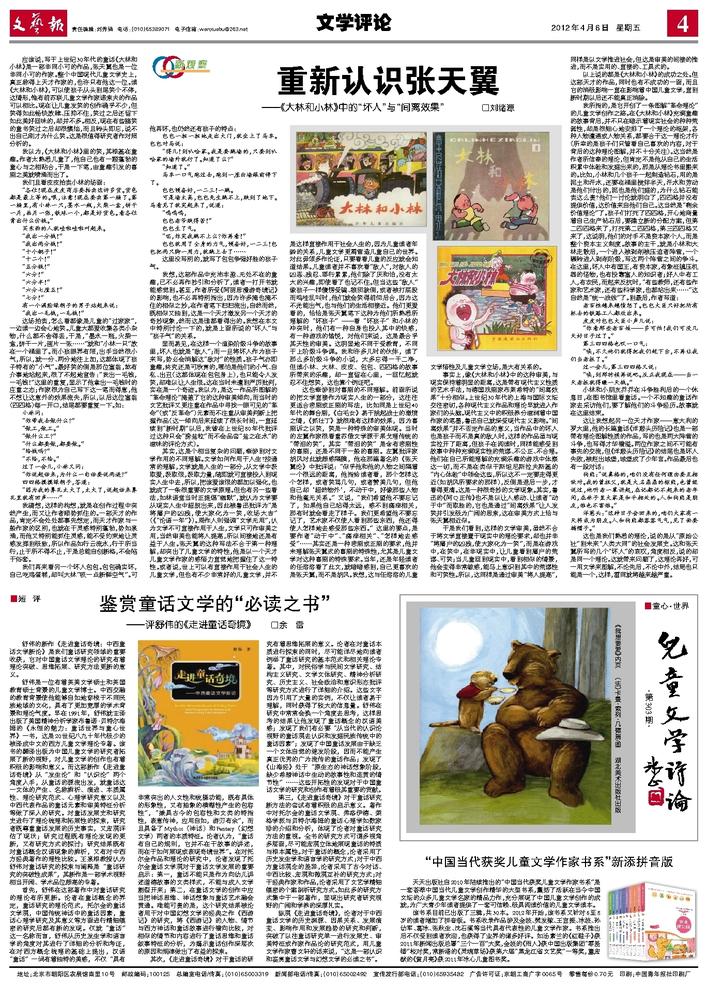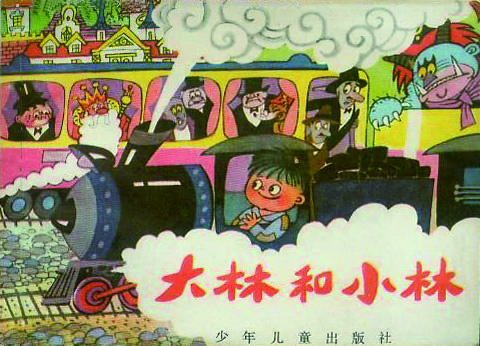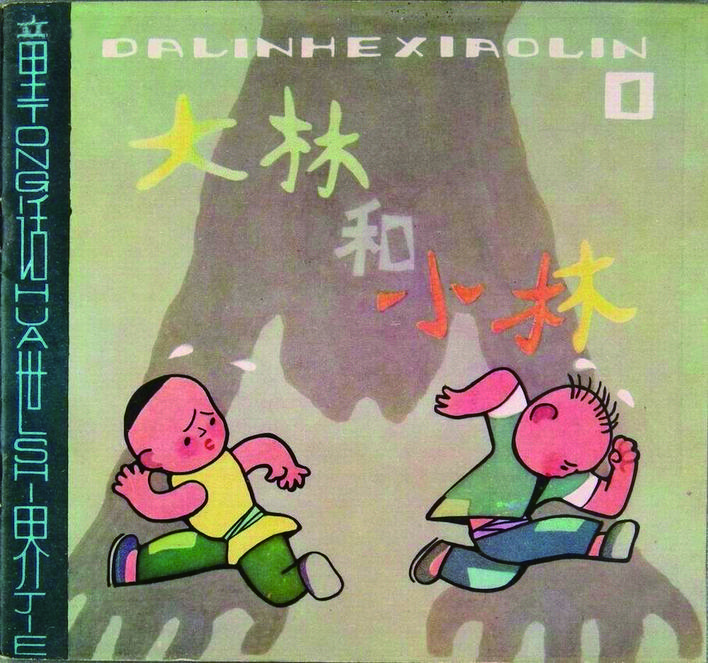应该说,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童话《大林和小林》是一部非同小可的作品,张天翼也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作家。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真正称得上天才作家的,也许只有他这一位。读《大林和小林》,可以使孩子从头到尾笑个不停,这情形,惟有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家诺索夫的作品可以相比。现在让儿童发笑的创作确乎不少,但笑得如此畅快放肆、压抑不住,笑过之后还留下如此美好回味的,却并不多。相反,现在有些搞笑的童书笑过之后却很懊恼,而且转头即忘,说不出自己刚才为什么笑。这是很值得研究者作对照分析的。
我以为,《大林和小林》里的笑,其根基在童趣。作者太熟悉儿童了,他自己也有一颗蓬勃的童心与之相贴合,于是一下笔,由童趣引发的喜剧之美就喷涌而出了。
我们且看皮皮拍卖小林的场面:
“各位!现在皮皮商店要拍卖这许多货。货色都是最上等的。喂,注意!现在要卖第一桶了。第一桶里,有小林一只,墨水一瓶,火柴一盒,饼干一片,画片一张,铁球一个,都是好货色。看各位肯出什么价钱。”
买东西的人就哇啦哇啦叫起来。
“我出一分钱!”
“我出两分钱!”
“十个铜子!”
“十二个!”
“五分钱!”
“六分!”
“六分半!”
“六分七厘五!”
“七分!”
有一个满脸绿胡子的男子站起来说:
“我出一毛钱,一毛钱!”
这场拍卖,怎么看都像是儿童的“过家家”,一边读一边会心地笑。儿童大都爱收集各类小杂物,什么都不舍得丢,于是,“墨水一瓶,火柴一盒,饼干一片,画片一张……”就和“小林一只”放在一个桶里了。而小孩眼界有限,出手当然很小气,所以,就一分、两分地往上加,这都体现了孩子特有的“小气”。最好笑的倒是那位富翁,煞有介事地站起来,很了不起地宣告:“我出一毛钱,一毛钱!”这里的重复,显示了他拿出一毛钱时的庄重之态;作家很为自己写下这一笔而得意,他不想让这意外的效果流失,所以,以后这位富翁(四四格)每一开口,结尾都要重复一下。如:
小林问:
“你带我去做什么?”
“做工,做工。”
“做什么工?”
“什么都要做,都要做。”
“给钱吗?”
“不给,不给。”
过了一会儿,小林又问:
“你说起话来,为什么一句话要说两遍?”
四四格摸摸绿胡子,答道:
“因为我的鼻孔太大了,太大了,说起话来鼻孔里就有回声……”
我猜想,这样的构想,就是在创作过程中突然产生,而又让作者顺势抓住的。一部天才的作品,肯定不会处处都事先想定,而天才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区别,也就在于灵感特别蓬勃,势如泉涌,而他又特别能抓住灵感,能不受约束地让灵感发挥到极致,所以作品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于是总能自创新格,不会陷于俗套。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坏人包包。包包确实坏,自己吃鸡蛋糕,却叫大林“吸一点新鲜空气”。可他再坏,也仍然还有孩子的特点:
包包一扭一扭地走出大门,就坐上了马车。包包对马说:
“得儿!到叭哈家。我是要跳墙的,只要到叭哈家的墙外就行了。知道了么?”
“知道了。”
马车一口气跑过去,跑到一座白墙跟前停下了。
包包预备好,一二三!一跳。
可是墙太高,包包先生跳不上,跌到了地下。马看见了就笑起来了,说道:
“呜呜呜,
包包老爷跌得苦!”
包包生了气。
“呸,你笑我跳不上么?你再看!”
包包就用了全身的力气,预备好,一二三!包包把两只脚一用力,就跳上去了……
这里没写别的,就写了包包争强好胜的孩子气。
我想,这部作品中充沛丰盈、无处不在的童趣,已不必再作抄引和分析了,读者一打开书就能感觉到。甚至,作者所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影响,也不必再特别指出,因为许多掩也掩不住的相似之妙,在作者笔下汩汩流出,自然而然,既相似又独到,这是一个天才激发另一个天才的奇妙现象,然而这是谁都看得出的。我想在本文中特别讨论一下的,就是上面所说的“坏人”与“孩子气”的关系。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渲染阶级斗争的故事里,坏人也就是“敌人”;而一旦将坏人作为孩子来写,势必会消解这“敌对”的性质。孩子气亦即童趣,终究还是可欣赏的,哪怕是他们的小气、自私、出丑(这都体现在包包身上),也只能令人发笑,却难以让人生恨。这在当时未遭到严厉批判,实在是一个奇迹。我以为,是这一作品所图解的“革命理论”掩盖了它的这种审美倾向,而当时的文艺批评又更注重在作品中寻找一眼可见的“革命”(或“反革命”)元素而不注重从审美判断上把握作品(这一倾向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后,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批评过这种只会“捞盐粒”而不会品尝“盐之在水”的滋味的评论方式)。
其实,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对文学作用的不同理解。文学如何作用于人生?按通常的理解,文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从文学中汲取爱,汲取恨,汲取力量,随即就可直接投入到现实人生中去,所以,把该爱该恨的都加以强化,也就成了一条很重要的文学原理。但也有另一些看法,如林语堂当时正提倡“幽默”,就认为文学要从现实人生中超脱出来,因此被鲁迅批评为“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论语一年”》)。周作人则强调“文学无用”,认为文学不可直接作用于人生,文学只可作审美之用,当然审美也能将人提高,所以间接地还是有益于人生。张天翼的这种写法不合于第一种理解,却突出了儿童文学的特性,他是以一个天才儿童文学作家的感悟力直觉地把握住了这一特性。或者说,世上可以有直接作用于社会人生的儿童文学,但也有不少非常好的儿童文学,并不是这样直接作用于社会人生的,因为儿童读者年龄的关系,儿童文学更需营造儿童自己的世界。对此毋须多作论证,只要看看儿童的反应就会知道结果。儿童读者并不喜欢看“敌人”,对敌人的凶恶、残忍、罪行累累,他们除了厌和怕,没有太大的兴趣,即使看了也记不住。但当这些“敌人”像孩子一样傻愣受骗、狼狈跌倒,或者被打屁股而呜哇乱叫时,他们就会笑得前仰后合,因为这不光能出气,也与他们的生活相接近。他们更爱看的,恰恰是张天翼笔下这种为他们所熟悉所理解的“坏孩子”——看“坏孩子”和小林的冲突时,他们有一种自身也投入其中的快感,有一种游戏的愉悦,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合乎其天性的审美。这明显地不同于受教育,不同于上阶级斗争课。我和许多儿时的伙伴,读了那么多阶级斗争的小说,大多忘得一干二净,但读小林、大林、皮皮、包包、四四格的故事所带来的乐趣,却一直留在心里,一回忆起就忍不住想笑,这也算个例证吧。
这也牵涉到对喜剧的不同理解。前面所说的把文学直接作为现实人生的一部分,这往往更适合悲剧或正剧的写法,比如同是上世纪40年代的舞台剧,《白毛女》易于挑起战士的激愤之情,《抓壮丁》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喜剧诉之以笑,笑是一种特殊的审美体现。当时的左翼作家很看重苏俄文学源于果戈理传统的“带泪的笑”,其实“带泪的笑”是含有悲剧性的喜剧,还是不同于一般的喜剧。左翼批评家胡风对此就颇感隔膜,他在那篇著名的《张天翼论》中批评说:“似乎他和他的人物之间隔着一个很远的距离,他指给读者看,那个怎样这个怎样,或者笑骂几句,或者赞美几句,但他自己却‘超然物外’,不动于中,好像那些人物和他毫无关系。”又说,“我们希望他不要忘记了,如果他自己站得太远,感不到痛痒相关,那有时就会看走了样子。我们更希望他不要忘记了,艺术家不仅使人看到那些东西,他还得使人怎样地去感受那些东西。”这里的要点,是要作者“动于中”、“痛痒相关”、“怎样地去感受”……其实还是一种悲剧或正剧的要求,他并未理解张天翼式的喜剧的特殊性,尤其是儿童文学对这种喜剧的特殊要求。当年,还是年轻读者的任溶溶看了此文,就暗暗感到,自己更喜欢的是张天翼,而不是胡风。我想,这与任溶溶的儿童文学悟性及儿童文学立场,是大有关系的。
事实上,像《大林和小林》中的这种审美,与现实保持着明显的距离,这是带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艺术手法,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十分相似。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与国际文坛交往密切,各种现代主义作品和理论早就进入作家们的头脑。现代主义中的积极养分滋润着中国作家的笔墨,鲁迅自己就深受现代主义影响。“间离效果”并不否定作品的意义,当作品中的坏人也是孩子而不是真的敌人时,这样的作品虽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但孩子在阅读时,同样能感受到故事中种种充满现实性的荒谬、不公正、不合理。他们在自己所能理解的充满乐趣的游戏中体察这一切,而不是在类似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内心体验”中领会这些,所以这不一定要走得更近(如胡风所要求的那样),反倒是退后一步,才看得更清。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文学现象。其实,鲁迅的《阿Q正传》也不是以让人感动、让读者“动于中”而取胜的,它也是通过“间离效果”让人发笑并引发极为广阔的思索,这在审美方式上恰与张天翼相近似。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学审美,虽然不合于将文学直接置于现实中的理论要求,却也并非“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而是在游戏中,在笑中,在非现实中,让儿童看到屠户的荒谬、可笑;当儿童回到现实中,看到相似的情景,他会变得非常敏感,能马上意识到其中的荒谬性和可笑性。所以,这同样是通过审美“将人提高”,同样是以文学推进社会,但这是审美的间接的推进,而不是实用的、直接的、工具式的。
以上说的都是《大林和小林》的成功之处。但这部天才的作品,同时也有不成功的一面,而且它的消极影响一直在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直到新时期以后还不能真正消除。
我所指的,是它开创了一条图解“革命理论”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在《大林和小林》充满童趣的故事背后,并不只在暗示着现实社会的种种荒诞性,却是很细心地安排了一个理论的框架,各种人物遭遇或人物关系,都要合于这一理论才行(所幸的是孩子们只管看自己喜欢的内容,对于背后的这种理论图解,并不十分关注)。这当然是作者所信奉的理论,但肯定不是他从自己的生活积累中体验和发掘出来的,那是从理论书里搬来的。比如,小林和几个孩子一起制造钻石,用的是泥土和汗水,还要在桶里搅拌半天,汗水和劳动是他们付出的,泥也是他们掘的,为什么钻石能卖这么贵?他们一讨论就明白了,四四格并没有提供价值,这价值来自他们自己。这当然是“剩余价值理论”了。孩子们打死了四四格,开心地商量着自己生产钻石后,要建立新的分配方案,但第二四四格来了,打死第二四四格,第三四四格又来了,这说明,他们的对手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故事的主干,就是小林和大林走散后,一个进入被剥削被压迫者阵营,一个辗转进入剥削阶级,写这两个阵营之间的争斗。在这里,坏人中有国王,有资本家,有象征镇压机器的怪物,也有投靠富人的知识者;好人中有工人,有农民,而起来反抗时,“有些教师,还有些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些科学家,也都站出来……”这自然是“统一战线”了。到最后,作者写道:
老百性越来越愤怒了。包包大臣只好把所有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出来。
皮皮对包包大臣小声儿说:
“你看那些老百姓——多可怕!我们可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第三四四格也叹一口气:
“唉,不久他们就得把我们赶下台,不再让我们当老板了。”
过一会儿,第三四四格又说:
“唉,到那时候再说吧。反正我现在——当一天老板就得赚一天钱。”
小林和小朋友乔乔在斗争胜利后的一个休息日,在图书馆里看童话。一个不知趣的童话作家去采访他们,要了解他们的斗争经历。故事就在这里结束。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天才作家——意大利的罗大里,他的长篇童话《洋葱头历险记》也是一部带有理论图解性质的作品,写的也是两大阵营的斗争,也写得才华横溢。两位作家之间不可能有事先的交流,但《洋葱头历险记》的结尾也是坏人失败,被赶出城堡,城堡成了少年宫。作品最后也有一段对话:
狗熊:“说真格的,咱们没有任何理由要互相敌对。我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棕熊,也曾经说过,他听老一辈讲起,在记都记不起来的老年间,在林子里大家是和平相处的。人和狗熊是朋友,谁也不害谁。”
洋葱头:“这种日子会回来的,咱们大家有一天将成为朋友。人和狗熊都客客气气,见了面要摘帽子。”
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理论,说的是从“原始公社”到未来“人类大同”的社会发展史。这和张天翼所写的几个“坏人”的哀叹,角度相反,说的却是同一个理论。这就带来问题了,这理论再好,可一用文学来图解,不论先后,不论中外,结局也只能是一个,这样,雷同就将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