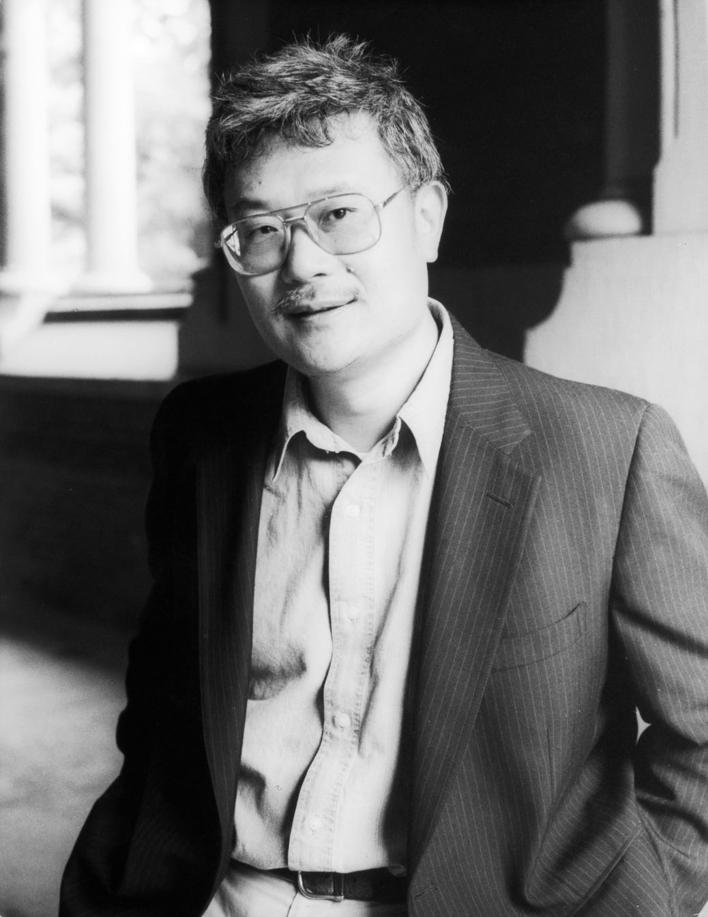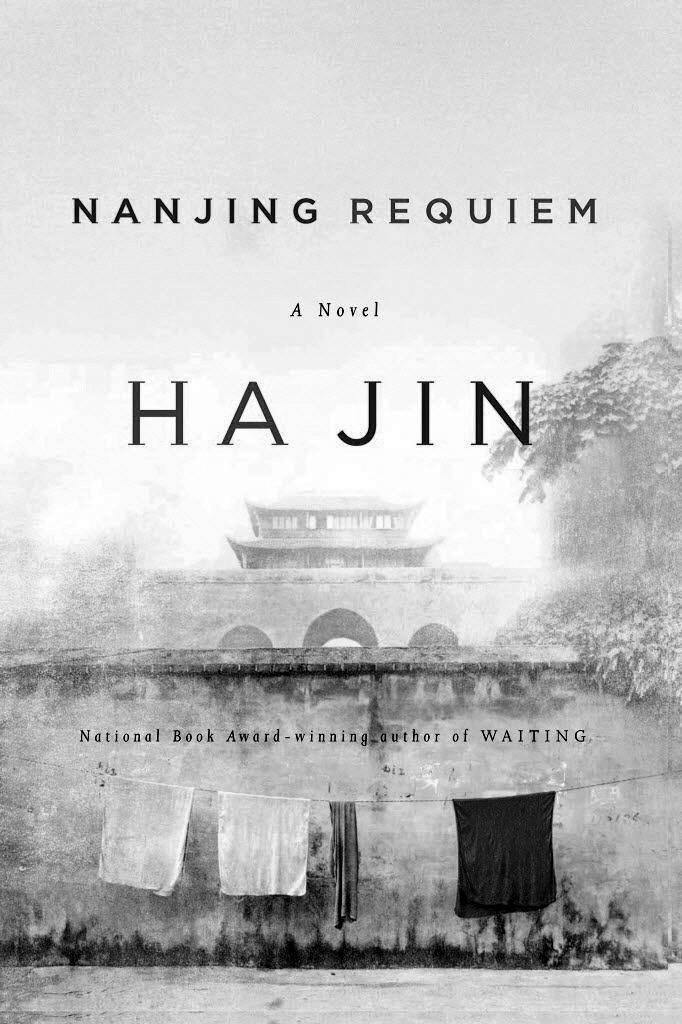“南京大屠杀”是作家不忍又不敢去触碰的创作素材,阅读每一份史料和书写每一个文字时,都难免让人心中隐隐作痛、悲愤难平。在小说《南京安魂曲》的创作过程中,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曾两次在放弃与坚持中挣扎,最终还是完成了《南京安魂曲》,因为“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
小说中美国人明妮·魏特琳成为了“南京”故事的主角。她是战争年代生活在南京的美国人、金陵女子学院的院长,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为中国平民提供避难,她教中国女孩基本生存技能,她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谴责一切践踏人的尊严的思想与行动,她痛苦终未能保住21个女孩的性命,她绝望于自己已被误解和将被遗忘……
哈金的6部长篇小说:《池塘》《等待》《疯狂》《战争垃圾》《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都存在两大叙事空间,除了《自由生活》关注20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的中国“新移民”之外,其他作品都以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故事”为蓝本。而同为“中国故事”的《战争垃圾》和《南京安魂曲》都是以“史”为基础,以“战争”为基本叙事元素。
《南京安魂曲》整体结构如同一张“日程表”,简单、清晰。哈金安排着1937年的每一天正在发生的事,并铺垫好将会发生的事。任何一部作品的“日程表”都有自己的特点,它应该是独立与惟一的,不存在模板和规矩,而作家讲故事的功力就体现在这张“日程表”的设计上,他需要规划,预想到可能会突然出现的插曲和即将发生的奇迹。哈金为《南京安魂曲》安排的“日程表”,是用扎实的现实主义传达质朴的文学理念,让读者对过往有回忆、对当下有体悟、对未来有期待、对自我有救赎。看似平常的生活,潜伏着生存危机,咆哮着滔天罪恶,翻滚着尔虞我诈,往日的平静与温暖根本让人无暇顾及。与同样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战争垃圾》相比,哈金这次选取以相对偏“柔”的“金陵女子学院”为视点,由它去承载1937年“南京”种种张牙舞爪的“力”:武力、暴力、自私、嫉妒、贪婪。
需要指出的是,“个人”和“国家”是哈金作品的两大关键词,无论是他的短篇还是长篇,贯穿创作始终的理念是对“人”的思考:人在世界中如何自处?个人与国家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同时,除了《南京安魂曲》之外,哈金的其他5部长篇小说,都是以男性为故事主人公。若搜索以女性为叙事中心的作品,最为典型的是《纽约来的女人》。《南京安魂曲》虽然仍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本应决斗的是“力”(战斗)之较量、昂扬的是“力”(生命)之美丽,但是这部作品选择放弃将男性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对象。这应该是哈金小说创作思路的一些调整。他的关注者被设定为女性,如明妮、安玲、玉兰。他慨叹和书写在民族大灾难、人性大对决中更为弱小的平凡女人所受到的戕害、荼毒、攻讦。美国人明妮和中国人玉兰都因为这场“屠杀”患上了精神疾病。玉兰是因为遭遇身体的直接摧残而精神错乱,明妮则是因为承受心灵的慢性折磨而精神错乱。而安玲的日本儿媳盈子被战争强行按压进复杂的民族矛盾之中,在战争中失去了中国丈夫,战后又不得与中国亲人相认。由此可见,哈金对女性的关注超越了民族和种族,她们都是这场残酷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明妮和安玲都无法在世间放置对自我的救赎。安玲在小说中说:“上帝会让我们对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有个交代的。”21个被日军安上“妓女”的身份、从金陵学院强行拖走的女孩,是明妮心病的症结,她因为自己未能保护她们而深感罪孽,这才是她神经错乱的根本原因。当明妮回到美国后,终于没有盼到来自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的信,她认为她被遗忘了、被抛弃了,她不会得到21个中国女孩的谅解,于是明妮通过自杀的方式让自己获得解脱和救赎。
安玲同样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悲剧的人物。她是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小说的叙述者。她的特殊身份使她多次陷入尴尬。儿子浩文娶了日本姑娘盈子,安玲一面目睹日军的疯狂屠杀,一面感受着亲情,战争把她推入了对中日两个民族的惟一认定和必然抉择。被迫做日本军医的儿子以汉奸罪被中国游击队处死,可实际上,浩文对母亲说,“不管我到哪里,都是个贱民”。而安玲不敢去安葬儿子,更要编造儿子是在回中国的路上被日本人杀死的谎言,以此保护亲人和儿子的名声。二战结束后,安玲与儿媳、孙子在日本相见不敢相认。安玲承载的是人世间“死别”与“生离”的双重大悲痛。
哈金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达是多元生动的,既有血淋淋的场面描写,又有压抑痛苦的间接转述,“金陵女子学院”是对大量平民生命的庇护,更是对根植在人性中的“恐惧”的安抚。小说中,3000多妇女跪在“科学楼”前,痛哭哀求“活菩萨”拉贝不要走,美国人明妮说,她没想到这些妇女对拉贝先生有那么深的感情,而中国人安玲明白,她们是希望受到保护。在1937年的南京,还有一群挣扎在暗无天日的夹缝中的人,他们同样拥有着悲戚的命运。一个小个子姑娘当街遭受玉婷和美燕的毒打,因为她们认为她爸爸设计轮船是为日本人工作,可小个子姑娘不断澄清着一个事实:爸爸同样也要养活这个家。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对不同民族间关系的描写细腻而耐人寻味。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中国百姓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以及他们对与日本人有些许关系的中国同胞的无情打击……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小说对战争背景中“个人”和“国家”具有深层次的理解和表达。战争让人恐惧,人性的恶也同样让人不寒而栗。战争在破坏着世界,扭曲着人。
“历史应该被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载才不容置疑、不容争辩。”这是明妮·魏特琳对安玲说的。这也是作家哈金想要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