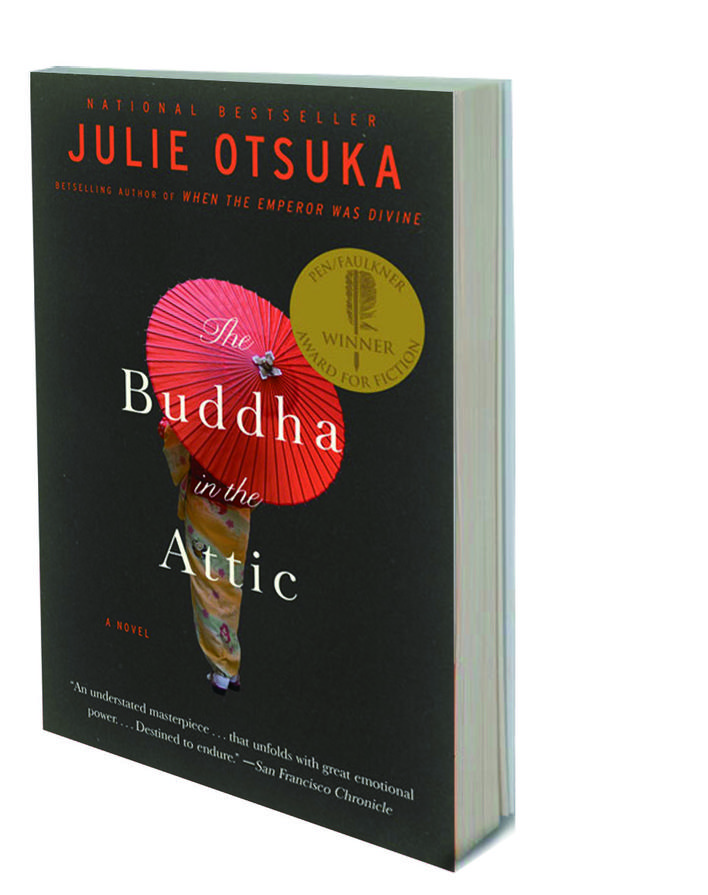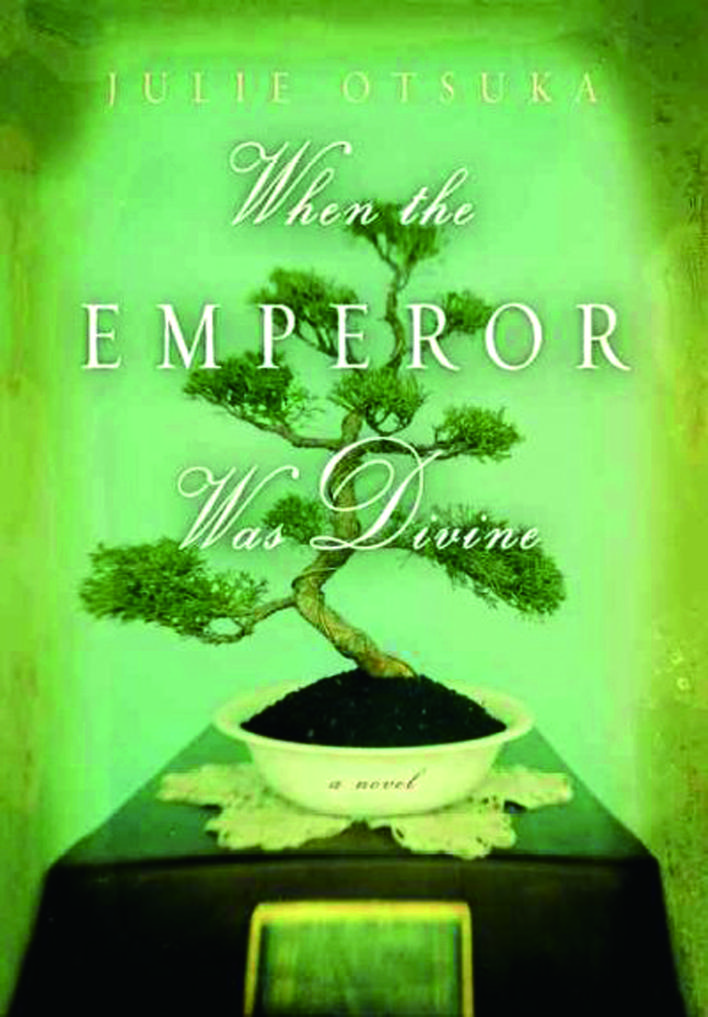今年3月,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揭晓,日裔美国女作家朱丽·大塚( Julie Otsuka)的作品《阁楼上的佛》(The Buddha in the Attic)最终获奖,捧走了1.5万美元的奖金。
笔会/福克纳奖是美国文学界一项重要奖项。它创设于1981年,基金来自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捐赠的一部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获得过福克纳奖的作家中不乏像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E.L.多克托罗等大名鼎鼎的文坛大佬。与他们相比,朱丽·大塚自然是小字辈的文坛新人。然而,这一结果也并不让人感到惊讶:《阁楼上的佛》在前一年就以极大呼声进入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只不过,最终美国国家图书奖却以奖项空缺的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朱丽·大塚生于加利福尼亚,曾在耶鲁大学学美术,30岁的时候开始小说创作。2002年出版的处女作小说《皇帝曾为天神时》(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以日裔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为背景,叙述了住在伯克利的一家人被拘禁于拘留营的故事。《皇帝曾为天神时》广受好评,为她赢得了亚裔美国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而正当人们对这位文坛新秀充满期待的时候,朱丽·大塚却“沉默”了起来,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直没有重要作品发表。直到2011年,她的第二部小说《阁楼上的佛》问世,人们才发现,原来她依然钟情于二战这段历史,新作可以说是追溯了《皇帝曾为天神时》的主人公在拘留营故事之前的经历。
然而,这两部作品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姊妹篇。《皇帝曾为天神时》写的是个体经历,是“小”叙事,是独奏;《阁楼上的佛》则回忆了群体的历史,是“大”叙事,是和声;前者不断转换叙述视角,父亲、母亲、女儿轮番成为故事中的主角;后者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它从头到尾的集体式叙述声音,“我们”——那些从日本舶来的“照片新娘”始终吸引着读者关注的目光。故事分8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追溯了“我们”在船上的辛苦与对未来的憧憬、下船之后见到丈夫时的失望以及紧张无奈的“初夜”、田间繁重的劳动、对白人雇主的屈从、学习语言以适应环境的努力、生儿育女的艰辛、与子辈越来越多的隔阂以至最后战争引发的种族迁移与隔离。性别、种族、文化、身份、战争、代沟、历史、记忆,少数族裔文学中几乎所有常见的主题均浓缩在短短100多页的故事中。
《阁楼上的佛》以一种精致的“宏大”吸引着读者。严肃的种族历史大框架之下,一个个平凡的生命所划出的轨迹更能勾动柔软的心灵产生共鸣。小说采用含蓄的、有节制的、诗一般的语言陈述了在生活的重重考验、折磨之下的“我们”的希冀、隐忍、痛苦、努力。这种集体式叙述的声音既勾勒出群体共同的感受,又照顾到个体独特的经历,收放自如、视野广阔。这种独特的叙述视角成为小说的一个亮点。在这种全能视角之下,一个女人,不,一群女人的一生立体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怀揣着从未谋面的丈夫的照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自日本各地的小姑娘们踏上了遥远的赴美之旅。然而,在目的地迎接她们的并非照片上英俊的男子们和她们被承诺的美好、舒适的生活。打击是沉重的,但她们选择了接受,或者说她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对岸那些人叫着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中有个人用手捂住了眼睛转过身去——我要回家,但其余的人都低下了头,整整我们的和服,走下跳板,走进了还泛着暖意的日子里。这是美国,我们对自己说,什么都不必担心。但我们错了。”
还没有等她们做好任何心理准备,打击就接踵而来。艰苦的生活条件、陌生的文化语境,她们以惯有的顺从承受着来自性别的、种族的、精神的、肉体的重重伤害和折磨。“我们忘掉了佛,忘掉了上帝。我们内心生长出来的冷漠到现在都融化不了。我们不给妈妈写信了…… 我们不做梦了。我们什么也不要了。我们只干活,就这样。”这种“卓绝的”忍耐力自然是来源于这些女人自幼所接受到的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它也是在作为“先行者”的丈夫们的教导之下、得以强化的结果——“反抗的惟一方式,我们的丈夫告诉我们,就是不反抗。”于是,她们听任丈夫摆布、听从女主人的吩咐、顺从男主人的要求,又独自承受着一切后果和打击。生活让她们变成了“空心人”、“隐形人”。
艰苦的生活造就了麻木的心灵,却也让“我们”迅速地适应了陌生的环境。接下来,生儿育女的经历多多少少改变了生活的基调。添丁进口使生存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麻木的心灵却在婴童们的啼哭声中慢慢软化。母亲,成了这些女人们新的身份——一种确定无疑的、让人安心的身份。她们竭尽所能照顾好这些孩子,呵护这灰暗生活中的一丝希望和光明。孩子慢慢长大了,在与她们相同却又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上了学、学会了英语、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却反而忘记和疏远了自己的母语和母亲。“通常,他们都以我们为耻。”“我们”养大了孩子之后,又失去了他们。
她们失去的还不仅仅是孩子。战争的消息传来。他们远隔重洋的母国日本再次给他们带来灾难,原本艰难却正在慢慢稳定下来的生活再起波澜。仿佛一夜之间,他们成了“叛徒”,成了不受欢迎、应被驱逐的人。不断有人的丈夫被抓走、孩子辍学,不断有人被调查、被恐吓、被威胁,直至终于有一天,他们被要求集体迁移,迁移到无人知晓、前途未卜的远方去。渐渐地、他们淡化在邻居们的记忆里……
而挖掘这段被淡忘了的历史,表达被噤声了的声音,成为作者的追求。朱丽·大塚以小说家的细腻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宏大关怀。作品表面冷峻,底下却激荡起狂乱的回声。小说的标题“阁楼上的佛”,很容易让人们把它同“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女性主义的经典批评之作建立起联系。然而在笔者看来,朱丽·大塚将叙事的声音给了深受各种歧视、遭遇各种挫折,称得上是命运多舛的这一群“她者”,也许不仅仅是旨在替这一弱势群体申冤叫屈,或者唱响女性抗争的颂歌,反而是表现了超越性别的宏大历史主题:“美国梦”的破灭、少数族裔的生存和身份危机、面对战争的思考等等。“佛”是许多日裔美国人的信仰,但他在小说中鲜有露面。被遗忘在阁楼上的“佛”是一种俯视的视角,他始终在角落里笑着,旁观着人类在他身边的忙忙碌碌,或睿智、或愚蠢的各种抉择……
在沉重的历史面前,人们也许应该低下高贵的头颅,听一听被我们放置在阁楼上的那些“沉默”的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