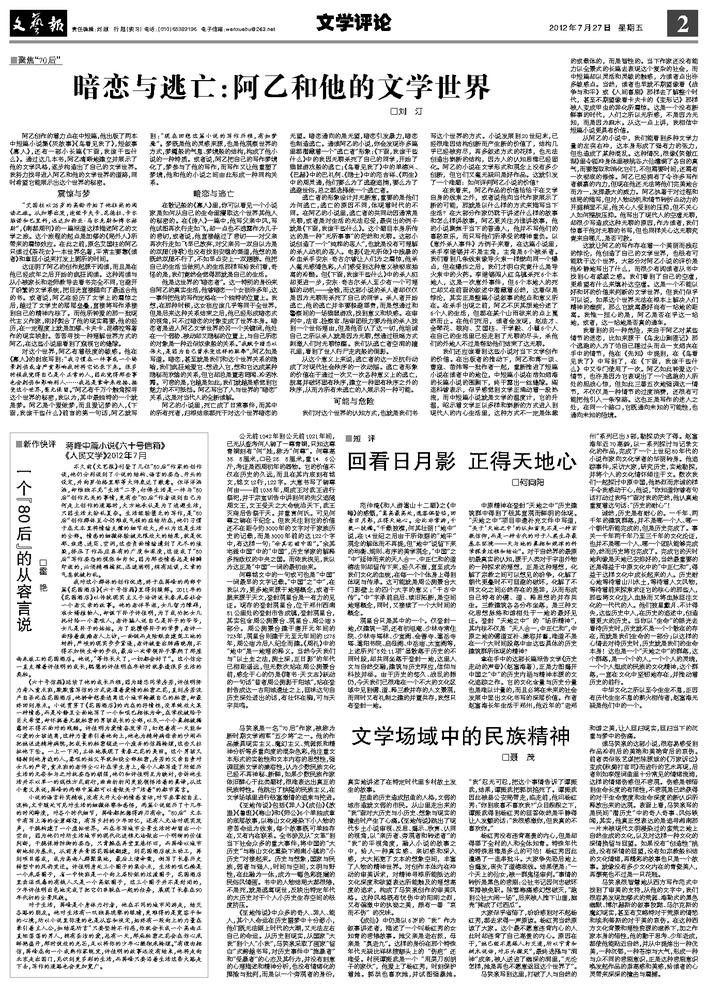阿乙创作的着力点在中短篇,他出版了两本中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短叙事《寡人》,还有一部小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通过这几本书,阿乙清晰地建立并展示了他的文学风格,逐步构造出了自己的文学世界。我努力找寻进入阿乙和他的文学世界的道路,同时希望它能展示出这个世界的秘密。
震惊与梦
“艾国柱以26岁的高龄开始了他狂热的阅读之旅。从加缪出发,途经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和巴里科,远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南都周刊》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阿乙的文学之旅。这个旅程的起点是加缪的《局外人》所带来的震惊效应。在此之前,原名艾国柱的阿乙只读过《茶花女》一本世界名著,平常主要靠《读者》和章回小说来打发上厕所的时间。
这证明了阿乙的创作起源于阅读,而且是在他已经成年之后开始的疯狂阅读。这种阅读与从小被家长和老师教导去看书完全不同,它避开了纷繁的文学系统,把目光直接瞄向了最适合他的书。或者说,阿乙在经历了文学上的震惊之后,越过了文学史的层层垒叠,直接将写作承接到自己的精神内核了。而他所钟爱的那一批现代主义作家,刚好契合了他的现实需要,他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加缪、卡夫卡、昆德拉等著作的现实映射。苦苦寻找一种理解世界方式的阿乙,在这些小说里看到了窥视它的缝隙。
对这个世界,阿乙有着极度的敏感。他在《寡人》的封底写到:“我习惯在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刺伤或者严重影响我时将它记录下来。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正常的人,因此觉得那些事也会刺伤和影响别人……我总是拿命来迎接、接受这个世界,毫无保留。”阿乙有千万个触角探寻这个世界的秘密,我以为,其中最独特的一个就是梦。阿乙是个爱做梦,而且爱记梦的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前言的第一句话,阿乙就写到:“现在回想这篇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梦既是他的灵感来源,也是他观察世界的方式,梦魇般的气息、梦境般的结构,构成了他小说的一种特质。或者说,阿乙把自己的写作梦境化了,梦参与了他的写作,而写作又让他重塑了梦境,他和他的小说之间由此形成一种同构关系。
暗恋与逃亡
在散记般的《寡人》里,你可以看见一个小说家是如何从自己的生命里攫取这个世界其他人的秘密的。在《诗人》一篇中,他写父亲中风,写他试图再次行走如飞,却一点也不透露作为儿子的悲切,或者说,他直接越过了悲切——对父亲再次行走如飞早已放弃,对父亲另一双自以为是的双腿(诗歌)也没有找到安稳的渠道,他想的是既然双腿不行了,不如早点安上一双翅膀。他把自己的生活当做别人的生活那样写给我们看,奇怪的是,我们竟然会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生活。
他是这世界的“暗恋者”。这一特别的身份来自阿乙的真实生活,他曾暗恋一个女孩许多年,这一事件把他的写作定格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我想,在那种时候,这女孩应该几乎等同于全世界,但是后来这种关系结束之后,他已经形成暗恋式的视角,只不过暗恋的对象变成了世界本身。暗恋者是进入阿乙文学世界的另一个关键词,他处在一个弱势、被动却又隐秘的位置上,与自己所恋的对象是一种近似奴隶般的关系。“我赋予暗恋以伟大,是因为自己曾承受这样的耻辱”,阿乙如是写道。暗恋,甚至就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关系的隐喻,我们疯狂地爱它、想进入它,想和它达成某种隐秘而欢愉的关系,但它却总是置若罔闻、冷若冰霜。可悲的是,它越是如此,我们就越是感觉到它魅力的不可抵挡。阿乙写出了人与世界的“暗恋”关系,这是对当代人的全新读解。
阿乙的小说里,死亡成了日常事件,而其中的所有死者,归根结底都死于对这个世界暗恋的无望。暗恋通向的是无望,暗恋引发暴力,暗恋也制造逃亡。通读阿乙的小说,你会发现许多篇里都潜藏着一个“逃亡者”形象:《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的我因无聊杀死了自己的同学,开始了猫鼠游戏般的逃亡;《鸟看见我了》中的单德兴、《巴赫》中的巴礼柯、《隐士》中的范吉祥、《两生》中的周灵通,他们要么为了逃避追捕,要么为了逃避世俗,总之都选择做一个逃亡者。
逃亡者的形象设计并无新意,重要的是他们为何逃亡,逃亡的原因不同,体现着时代的不同。在阿乙的小说里,逃亡者的共同动因通常是无聊,或者是对生活的无法忍受,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个题目本身所传达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茫然和无聊。这部小说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恶人”,也就是没有可理解的杀人动机的恶人。电影《老无所依》中残暴的冷血杀手安东·奇古尔曾让人们为之震惊,他杀人毫无感情色彩,人们感受到这种意义被彻底抽离的冷酷。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的杀人犯却更进一步,安东·奇古尔杀人至少有一个可理解的动机——金钱,而这部小说的杀人者却仅仅是因为无聊而杀死了自己的同学。杀人者开始逃亡,他的逃亡并非要躲避罪责,而是想通过和警察间的一场猫鼠游戏,找到意义和快感。在审判中,法官、检察官、陪审团极力要为他的杀人找到一个世俗理由,但是他否认了这一切,他坦诚自己之所以杀人就是因为无聊,想通过极端方式刺激人们对无聊惊醒。我们从逃亡者空洞的瞳孔里,看到了世人行尸走肉般的倒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逃亡者的这一反抗行动成了对现代社会秩序的一次动摇。逃亡者形象的价值在于通过一次又一次各种意义上的逃亡,脱离并破坏固有秩序,建立一种固有秩序之外的秩序,从而为所有未逃亡的人展示另一种可能。
可能与危险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也就是我们书写这个世界的方式。小说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很难因结构创新而产生新的价值了,结构几乎已经被穷尽,再多叙述方式的花样,也无法创造出崭新的结构,因为人的认知思维已经固化。阿乙的小说在文学形式和观念上没有多少创新,但它们又毫无疑问是好作品。这就引发了一个难题:如何评判阿乙小说的价值?
在我看来,阿乙作品的价值恰恰于在文学自身的线索之外,或者说他向当代作家展示了新的可能,那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描写当下生活?在大部分作家仍耽于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和怎么样讲故事,阿乙更关注为谁讲故事,他的小说聚焦于当下的普通人,他并不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只写他们所承受的精神重负。以《意外杀人事件》为例子来看,在这篇小说里,杀手李继锡并不是主角,主角是6个被杀者。我们看到几条线索像导火索一样燃向同一个爆点,但在爆炸之后,我们才明白究竟什么是导火索中的火药。李继锡闯入红乌镇杀死6个本地人,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但6个本地人的死亡却又在前面的叙述中潜藏着必然,这看似是悖论,其实正是整篇小说叙事的起点和意义所在。在杀手出现之前,阿乙不厌其烦地分述了6个人的生活,但都在某个山雨欲来的点上戛然而止。在他们死后,读者会发现,赵法才、金琴花、狼狗、艾国柱、于学毅、小瞿6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已经走到了无聊的尽头,杀他们的外地人不过是帮助他们结束了这无聊。
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小说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价值。在出版者的推动下,阿乙和蒋一谈、曹寇、苗炜等一批作者一起,重新推进了短篇小说在读者中的地位,中短篇小说在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的围剿下,终于露出一丝缝隙。阎连科曾表示,似乎感觉到文学正涌动着一股热流,而中短篇小说就是文学的温度计,它的升温,昭示着文学正以多样和崭新的方式进入到现代人的内心生活里,这种方式不一定是体裁的或载体的,而是智性的。当下作家还没有能力以全景式的长篇去表现这个复杂的社会,而中短篇却以灵活和灵敏的触感,为读者点出许多敏感点。当然,读者也早就不期望像看《战争与和平》或《人间喜剧》那样去了解整个时代,甚至不期望像看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被人变成甲虫的异化所震惊。这是一个没有新鲜事的时代,人们之所以无所感,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麻木。从这一点上讲,我相信中短篇小说更具有价值。
从阿乙的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多种文学力量的左突右冲,这本身形成了强有力的张力,但也造成了某种混乱。这种情况,很像《笑傲江湖》里令狐冲身体里被桃谷六仙灌满了各自的真气,而要驾驭和消化它们,不但需要时间,还需有一次彻底的修炼。阿乙已经拥有了令许多写作者羡慕的内力,但现在他还无法将他们完美地合而为一,发挥最大的威力。阿乙执著于对过程和结局的描写,但对人物动机和情节转折点动力的开掘稍显不足,他关心人受到的压抑,但不关心人如何摆脱压抑。他写出了现代人的空虚无聊,却很少写造成这种无聊的原因,作为读者,我们惊喜于他对无聊的书写,但也同样关心这无聊究竟来自哪儿,是否可救。
这就让阿乙的写作存在着一个美丽而残忍的悖论,他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也极有可能耽于这个世界,大部分对阿乙小说的评价是他冷静地写出了什么,而很少有阅读者从书中找到心有戚戚之感。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空虚,更希望有什么来填补这空虚。这是一个不能以好和坏的价值来判断的文学世界,但我们似乎可以说,如果这个世界无法在根本上解决人们精神的痼疾,那么它就离最好尚有一站地的距离。我惟一担心的是,阿乙是否在乎这一站地,或者,这一站地是否真的通车。
我看到的另一种危险,来自于阿乙对某些情节的迷恋,比如来源于《乌龙山剿匪记》那个逃跑的人为了怕自己睡过头而点一支烟夹在手中的情节,他在《先知》中提到,在《鸟看见我了》中写到了,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又专门使用了一次。阿乙如此钟爱这个情节,也许是因为它表现出了一个逃跑的人所处的胆战心惊,但如此三番五次地强调这一情节,不仅仅是一种情节的过度消费,还很有可能把他引入一条窄路。这也正是写作的迷人之处,在同一个路口,它既通向未知的可能性,也通向未知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