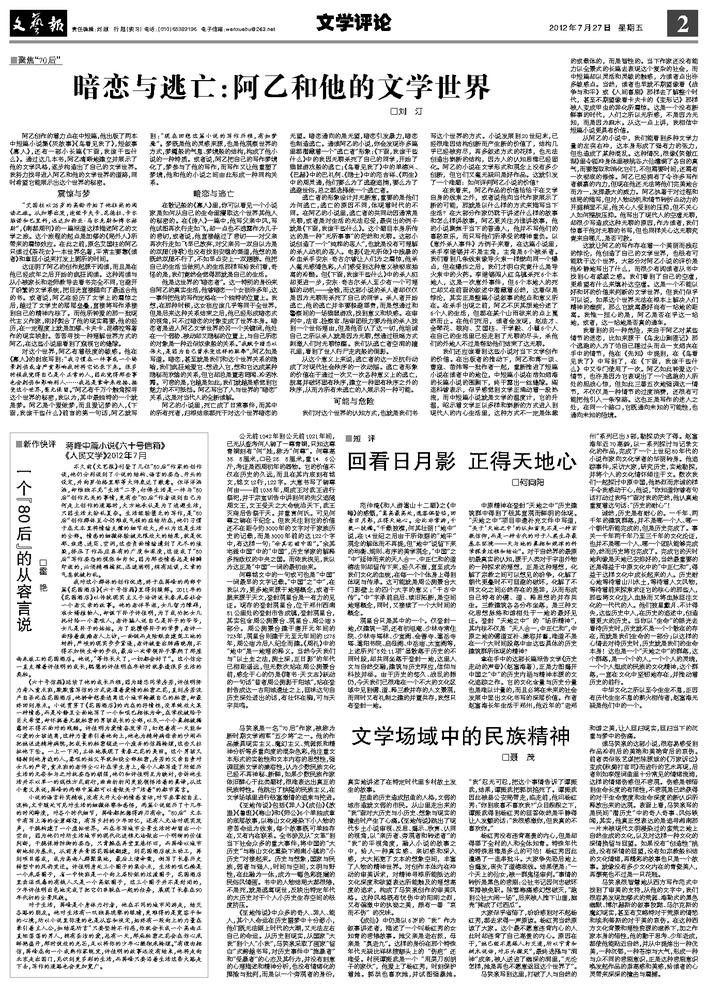不久前《文艺报》刊登了几位“80后”作家的创作谈,他们分别谈到了小说的结构、语言的姿态、开头的设定,并向罗伯格里耶等大师表达了敬意。但洋洋洒洒,却惟独不见“生活”二字,仿佛生活是一件与“80后”创作无关的事情,更有些“80后”作者谈到自己为何走上创作的道路时,大方地承认是为了逃避生活,只因生活太纷乱复杂。生活经验匮乏的写作,是“80后”创作群体至今仍难成气候的症结所在,他们习惯于在文本里将情绪支撑的细节放大,并以为这是生活的全部。情感的细微体验被无限放大的结果,就是忧郁、焦虑、迷茫、空洞,这些负面情绪遭到了无尽的渲染,挤压了作品应具有的广度和深度,这造成了“80后”写作姿态的慌张和匆忙,因为那些情感总是转瞬即逝的,必须精确捕捉、迅速阐明,稍有延误,文章的气息就被打乱。
我对这个群体的创作忧虑,终于在蒋峰的两部中篇《花园酒店》《六十号信箱》里得到缓解。2011年的《花园酒店》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讲述长春底层社会一个老父亲的故事。他的老伴早逝,女儿智力障碍,准女婿植物人,却诞下孙子许佳明,为了成功把女儿托付给一个聋哑人,老许骗人说自己是孙子的爷爷,女儿是孙子的姑姑。为了能攒够孙子的学费,老许一面陪着截瘫老人上访,一面铤而走险贩卖建筑工地的材料,严峻的现实步步紧逼,老许被查出肺癌晚期,不得不加快生命的步伐,最后一次带领孙子攀爬了那座尚未竣工的花园酒店。他说,“等你长大了,一切都会好了”。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许佳明的成长,聪慧的许佳明在年幼时就参透很多生活的奥秘。
《六十号信箱》延续了他的成长历程,因为暗恋同学房芳,许佳明努力考入重点班,默默靠写信的方式浇灌着爱情的秘密之花,直到房芳流产自杀死在花园酒店,他拼命想要逃离这个城市掩藏自己的秘密,却最终回到原点。小说贯穿了《花园酒店》的内在的抒情性,没单纯放大某一种情感,而是冷静且全面地写了一个和哑巴相依为命,在学校被给予巨大希望,却怀揣着无数秘密的男孩成长的全部,以及一个个真相被揭露时不得不面对的残酷。许佳明为爱情奋发学习,幻想着有一天能和心爱的女孩逃离,这种力量牵引着他向上,他也为精神病母亲的吵闹而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把成长的秘密锁进一个废弃的信箱掩埋,这些又拉扯他下坠。一上一下间,立体地展现了青春之花的美丽。这个男孩又辐射到他身边的人,聋哑的姑父早就知晓全部秘密,房芳的父亲自责对女儿的严苛,重点班的老师全心扑在学生身上,每个人都写透了所经历生活的无奈和与之对抗姿态的顽强,他们和许佳明互为映衬,告诉他生活并不以单一的线性方式前行,曲曲折折间更能领悟活着的真谛,从这个意义来说,蒋峰的两部中篇都可以看做关于“活着”的都市寓言。
小说的语言朴实精准,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对节奏掌控自主、流畅,文中随处可见对生活的细微体察和感悟,两篇小说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跨度,对各个时代细节,蒋峰都把握得游刃有余。“80后”文本中有写上海的金碧辉煌,有写乡村的少年回忆,还有人无法对现实发声,干脆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而在书写城市全景生活时却留出一个空白,因为他们对所生活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无法做出一个明晰的价值判断,干脆保持防御的姿态,只肯躲在弄堂里巷怀旧,而蒋峰以城市新地标为基点,从前身共青团花园被翻建,到花园酒店破土动工,再到项目落成,成为高尚人群聚集地,最后上演命案,侧写了长春历史转型中的风雨变迁。许佳明身处三个圈子的集合点,生活的哑巴楼是一个底层圈子,省一中快班是一个向上层阶级的过渡圈子,花园酒店里卖淫吸毒的有钱人又是一个高级圈子,这三个圈子并不是封闭的,少年许佳明出色地完成了把它们串联在一起的任务,展现了长春在90年代初的全景风貌。
对于生活,蒋峰是个身体力行者,他在不同的城市间游走,结交各路的朋友。他对生活有一双独具观察的眼睛,更难得的是宽容平和的心境,所以小说里弥漫的也是从容和淡定,始终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在牵引着主人公,如结尾所言“只要坚持不作恶,你就会长成一个高尚正直坦荡荡的男人,拥有圣洁的爱,总有一天,那朵秘密之花会在你心底鲜艳盛开,那时绽放的光芒,足以将你的少年心酸彻底掩埋。”有理由相信,蒋峰在向一个成熟作家蜕变,许佳明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他将走向北京走出国门,见识到更多彩的生活,而蒋峰只要沿着生活这条大路走下去,写作的道路也会更加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