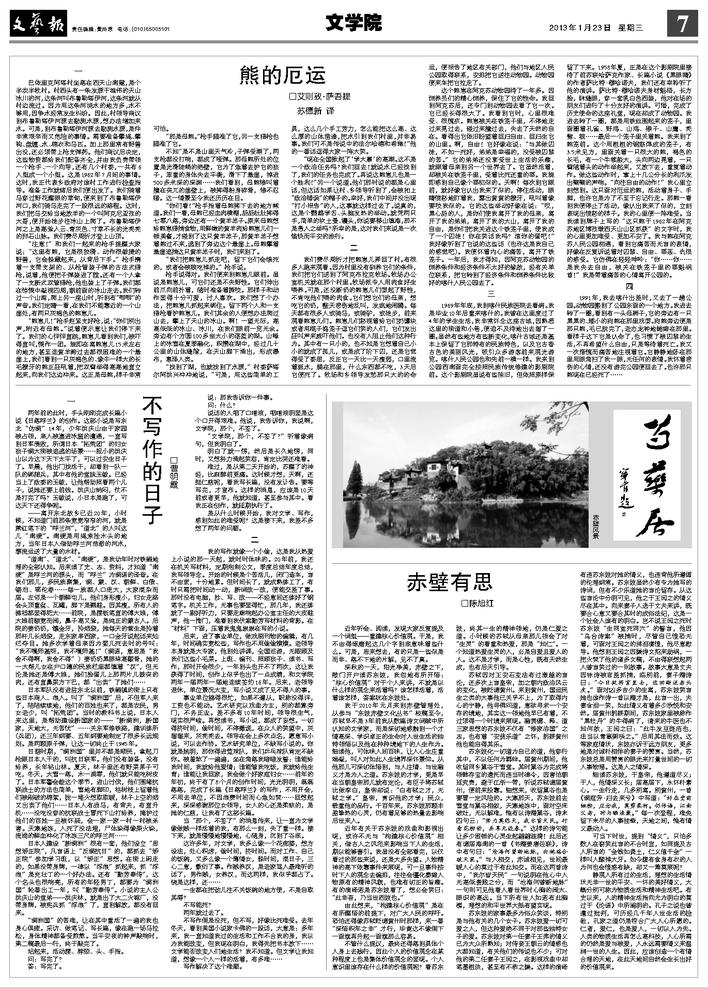近年听会、阅读,发现大家反复提及一个词组——重建核心价值观。于是,我不由得琢磨起这几个字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可是,思来想去,有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落不下地的片解,见不了真。
深秋的一天,阳光净美,赤壁之下,敞门开户读苏东坡,我忽地有所开悟:“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讲,不就是以什么样的观念来活着吗?该怎样活着,活着该怎样,答案犹在东坡处。
我于2010年元月来到赤壁管理处,从参与“东坡赤壁文化丛书”校稿至今,苏轼早不是3年前我从数篇诗文词赋中所认知的文学家,而是深切地感触到一个才情高深、学识卓正的生命对人世生活的独特领悟以及他在种种境地下的人生作为。细读他,可体味人间百味,让人心生庄重端凝,叫人对如此人生境界深怀景仰。从他那儿可深切体悟到,与人注情、与世融义才是为人之道。苏东坡的才学,更是早在当朝皇帝那儿就有定论,有臣子将苏轼比做李白,皇帝却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皇帝,赏识他的才学;民众,敬重他的品行。千百年来,苏东坡那颗丰盈挚热的心灵,仍有着足够的热量去影响后世来人。
近年有关于苏东坡的戏曲和影视出现,或许不无与“构建核心价值观”相关,借古人之风范来影响当下人的生活,期以能够善引。我虽没有全部看完,以仅看过的那些来说,还是大多失望。人物精神的高下依靠事件来展现,可一旦事件按时下人的观念去编排,往往会僵化萎缩人物原有的精神风貌,也难有切正的旨趣。有的演绎若是苏东坡看了,想必会笑曰:“此非吾,乃当世西坡也。”
由此想来,“构建核心价值观”是在有所醒悟的前提下,对广大人民的呼吁。恐怕还得像苏轼贬谪黄州时那样,来一番“深悟积年之非”才行,毕竟这不像倒下一面旗再升起一面旗那么容易。
不管什么提议,最终还得落到具体个人身上去践行,因此个人的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价值观念的显现。个人意识里该存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呢?看苏东坡,终其一生的精神领地,仍是仁爱之道。小时候的苏轼从母亲那儿领会了对“生灵”的看重和热爱,那是“知仁”。一个知道热爱生灵的人,必是自爱且爱人的人。这不是才学,而是心性,既有天然生成,也有后天引导。
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有过激越的言论,还多次上言皇帝,加之朝内政治风云的变化,被贬谪黄州。来到黄州,国运民生之类的大事他已关乎不上,为了取得内心的宁静,他寻佛问道,意欲寻求一个安存的境地,其实这一领地他早已有着,不过须得一个时境来展现。融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苏东坡不仅有“修家治国”之志,也有着“安贫乐道”之怀,躬耕黄州他也能自得其乐。
苏东坡化一切道为自己的道,他穿行其中,不以任何为羁绊。居黄州期间,他收留同乡巢谷于雪堂。其时巢谷为完成将领韩存宝的遗托而违当时律令,因害怕朝廷究责,避于江浙一带,听说苏轼谪居黄州,便前来投靠。细想来,收留巢谷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大寒那天,苏东坡前去雪堂与巢谷相叙,天寒地冻中,面对空床破灶,无以解难,惟有以诗赠巢谷,诗末四句云:“努力莫怨天,我尔皆天民。行看花柳动,共享无边春。”这样的诗句能让多少困顿的心灵生起翩翩涟漪!此后还有谪居海南的一首《书赠姜唐佐联》,诗中有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与人相交,赤诚相见,世间最暖人心的莫过于有此知交。而在这两首诗中,“我尔皆天民”一句说明在他心中人无高低贵贱之分,而“沧海何曾断地脉”一句则可见他看人看世界时心胸的阔大、眼识的高远。当下所有世人如若有此胸襟,理想的和平世界大抵有望实现。
苏东坡的家事最多为俗众笑谈,特别是与他有关的几个女子。苏东坡爱一切可爱之人,但这种爱绝不同于对那些独特女子的爱。苏东坡对第一任妻子王弗的情义已为大众所熟知;对侍妾王朝云的情感也大都知道,有关他们的传说也不少;可对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在影视戏曲中却笔墨粗淡,甚至有不恭之嫌。这样的演绎有违苏东坡对她的情义,也违背他所遵循的伦理纲常。苏东坡虽然少有专为她写的诗词,但有不少乐道她的言论留存。从这些言论中分明可见,他之于王闰之的情义尽在其中。向来妻子人选于丈夫来讲,既要合心意又要合其时的成俗法纪,这是一个社会人该有的明白。岂不说王闰之死时苏东坡“生同室死同穴”的誓言,他因“乌台诗案”被捕时,尽管自己惶恐无着,可面对王闰之的涕泪凄惶,他尽意慰导。他想到王闰之因嫌诗文招来劫祸,一把火焚了他的诸多文稿,不由得联想起两人曾言笑过的一则故事。故事大意是丈夫因咏诗被官差抓捕,临别前,妻子赠诗曰:“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面对凶多吉少的生离,苏东坡笑言她也该作诗一首以赠才是,此言一出,夫妻含泪一笑,如此情义有着多少欣悦和安然。居黄州躬耕期间,苏东坡家里被称作“黑牡丹”的牛得病了,请来的牛医也不知何故,王闰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后用其法而效。这等家庭情状,东坡亦诉于远方朋友,更多地是对诚朴相伴的妻子的赞赏。当然,苏东坡总是用赞赏的眼光来打量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理。这是人之情深。
细读苏东坡,于皇帝,他遵道尽义;于人,他情深义长;居高居下,永怀朴素心。一生行走,几多别离。别黄州,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中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每一次登程,难免留下未尽的人事挂牵,天地之间,惟有情义最动人。
可当下时世,提到“情义”,只怕多数人在窃笑此言的不合时宜,如同提及古人所言的“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一样叫人酸掉大牙。如今腹有食身有衣的人为何也会惶惑有缺,却又一筹莫展呢?
静观人所有过的生活,理想的生活情状无非一世的平安、一怀的美好情义,大概分别可称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吧。有史以来,人的精神生活指向尤为明白的莫过于《论语》中所阐明的。孔子之说也曾遭过批判,可历经几千年人世生活的检验,孔家之道仍是符合广大人心所愿的。仁者,爱仁,也是爱人,一切以人为先。人类的物质生活再怎么高科技,人心所需的仍然是爱与被爱,人永远需要情义来温润一世的人生。因此,应该创造一个有情合理的天地,在此天地间自然会生长出好的价值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