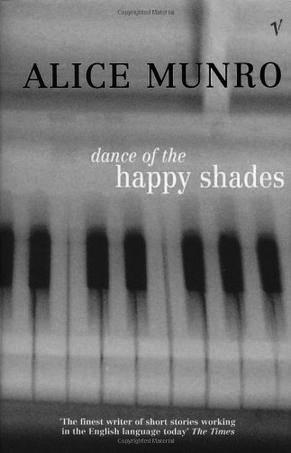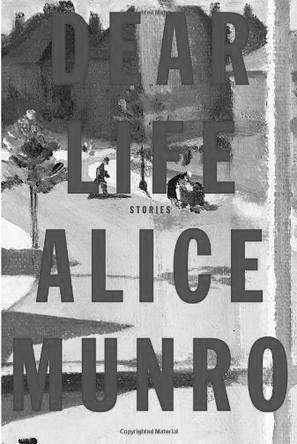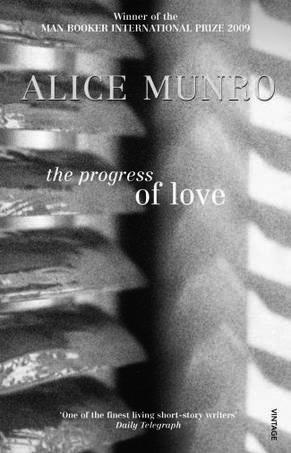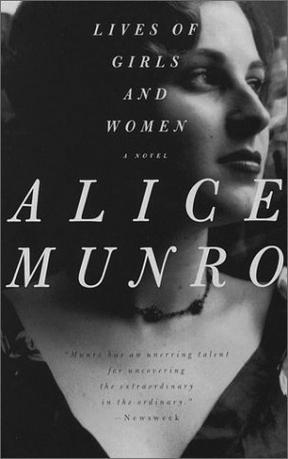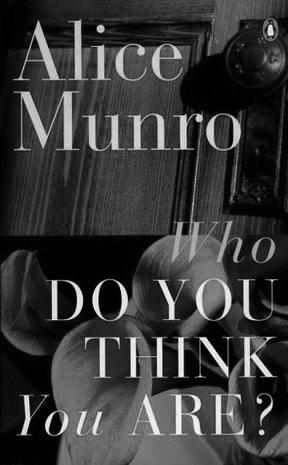(上接5版)
女性形象 地域特色 全知叙事
简单说,门罗的创作有三大特征:
首先是突出的女性形象。从一开始展现少女在成长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描写她们如何与家人相处,如何设法逃离所居住的小镇或者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到后来书写中年女性生活的艰辛、养育子女的困苦,再到后来描写女性人到老年的孤独与悲伤。可以说,从门罗的作品中,我们大体可以归纳出一个女性一生成长的轨迹,也能隐约体会到作者对女性从青年到老年成长过程的深度思考。
门罗的女性形象,又可以分为少女形象和女人形象。门罗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作了众多的少女形象。她们都经历了从少女时代到恋爱结婚、再到为人妻和为人母的经历,总是在生活中四处寻找意义。而每当她们意识到性的力量以及巨大的潜在混乱时,意识到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时,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社会关系时,往往是其走到人生关键时刻之际。而这一时刻,又往往与作者无情地解剖家庭关系融会在一起。像在《少男少女》(Boys and Girls )中,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少女从小就把自己看作是父亲的帮手,帮着他干农活。但随着她进入青春期,女性意识在觉醒,过去对自己的男性角色定位也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质疑,她最终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少女啊”。
门罗还将多个母亲形象写入到作品中,这些形象给人极为真实的感觉。其实,在作品中,门罗总是以自己作为母亲的形象,以此作为中心题材。在《宝贵生活》中带有自传色彩的4部短篇中,门罗的母亲形象更为突出。她的个人生活令人悲伤,命运对她来说也很不公平,而她敢于去面对命运。门罗曾把自己的外婆乃至叔祖母等形象写入作品,因为这些人物在其少女时期,比母亲对自己起了更大的作用。
在作者对男性与女性的认识中,《太多的欢乐》(Too Much Happiness )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代表作者对男女之别的认识:“要牢牢记住,男人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就把一切都丢到了脑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时候,却把房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带在了身边。”我想,这形象地说明了女性在生活中、特别是在婚姻中的挣扎与困境。
第二,鲜明的地域特色。门罗的创作背景就是其所生长的安大略省,具体而言是其下辖的休伦县中的小镇。在门罗80多年的生活中,除了有十多年生活在温哥华等地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安大略省西部的小镇上。而她写作的一大特征,就是作品总是围绕着小镇及小镇上的人物而展开。这一点,与中国作家莫言的写作围绕山东高密如出一辙。门罗认为,这里的地方文化对自己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个人一旦在一个小镇中居住久了,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也会见识各色人等。需要注意的是,门罗正如福克纳一样,虽然作品的人物局限于小镇,但这不仅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作者的想象力。我们既能看到其精彩的现实书写,也能在那些安静而平凡的描写中,不时地发现一些新鲜的意象或者新式的人物、耀眼的物体、闪光的思想,照亮了整个场景。如在《海边旅行》(A Trip to the Coast )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天空泛白、凉爽,亮光横扫过来,照亮了天际,仿佛就在一个贝壳之中”。像这样对人物、场景和人的状态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第三是全知的叙事模式。门罗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属于全知全能型的人物,她/他们似乎了解一切。有批评家经常把门罗的这一创作特色与美国南方作家相提并论,这不无道理,但就其人物而言,门罗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更加复杂多变一些,也有人将其创作风格归结为“南安大略的哥特小说”(Southern Ontario Gothic)。门罗写作喜欢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故事发展与契诃夫的作品有类似之处,情节居于次位,甚至有时并没有大的事件发生。但正如有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其简洁明快、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总会促使读者有幡然领悟的一刻,或者在恍惚之间得到一种启示。
总体而言,门罗的创作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与纪实性的写作。她的作品既可以从作家个人生活中找到发展脉络,也可以看到作者生活中的人和事的影子。门罗曾说,自己从来不会为写作素材担心,因为,家乡就是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源泉。
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先例,即第一次把桂冠授予一个专事短篇小说创作而较少创作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家。
在文学世界中,长篇小说一直都是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几乎是众多作家首选的文学表达方式。而短篇小说则往往难以被看重,一般被认为是杂志所青睐的文学形式,甚至被有些作家看作业余消遣时的副产品,即便是结集出版的小说集,往往也很难受到批评家和大众的重视。那么,门罗为什么要选择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呢?
门罗对自己的认识与定位极其清楚。她认为自己生长于边缘地带,同时,也很高兴自己处于一种非主流的写作状态。如果不是边缘化,自己或许没有这样的信心,也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再比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3位获奖的女性作家,其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主,加上某些创作特征,门罗难免会被看成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有女权倾向的作家,但门罗对此持否定态度。她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因为自己并不以那样的方式去看问题。
因此,就其文学创作形式而言,短篇小说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然,她也曾在接受采访时很谦虚地表示,自己所以能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取得成功,也许是因为没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同时,她也坦承曾尝试写作长篇小说,但后来感到自己的文学思维并不适用于长篇,因此很快放弃了。
但门罗确曾写过一些内容连贯的故事,除了上文提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外,还有《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 ),主人公也是反复出现,也被人当作是长篇小说来看待。门罗承认,她喜欢这样的写作方式。她引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话说:“哦,我多希望自己写一本长篇小说啊,我可不希望自己死后留下的都是些碎片而已。”门罗也说,自己很难断了“身后留下的只是一些碎片般的故事”这样的念想,“即使人们夸你是契诃夫”,但自己也还是会有那种感觉:不过是创作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罢了。
虽说如此,门罗将表达形式锁定在短篇小说,并将这一文学形式发扬光大,使其同样完美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声,足以显示出其对短篇小说创作并以这种形式反映个人思想的信心。她把每次写作视为是一次恋爱,可见其感情之投入。
门罗被人称为短篇小说大师,更被批评家称为“当代契诃夫”,这个称呼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当然是对门罗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度评价,认为她已经进入到了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家的行列之中。其次,门罗以其家乡为背景的创作如此精彩,她笔下的那片土地完全可以像“契诃夫的村庄”、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县”那样,成为“门罗之镇”。再次,门罗对作品的人物毫无先入之见,同时,更主要的是,其作品既不穿插意识形态,也无太多政治因素的考量,仅是平实地反映小镇中的女性形象、讲述那里所发生的甚至并不惊心动魄的日常故事,同样使其作品具有了文学之美。
门罗的作品富有洞见,具有怜悯之心,虽然深入探讨了众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及特性,但很少把自己的评价加诸于人物身上,而是留待读者去思考。就艺术创作手法而言,门罗的故事不重故事情节,但引人思考。在小说的开始部分,作者也并不暗示未来的故事会向何处发展。为此,有批评家认为,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在缓慢的行进中突然就转了向,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而有时,作者则通过一个奇怪的字眼结束全文,让读者回味无穷。《海边旅行》讲述了11岁的梅与外婆的故事。当外婆在最后死去的时候,作者用了一个词“victorious”(胜利、凯旋之意)。这就不能不引发读者去深思,为什么作者要以这个词来结尾?是想说明她就此解脱了,还是说梅的生活到头了,抑或有别的原因?这些,都值得读者深入思考。
门罗的创作给人以启示。身为作家,出身和身处的环境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矢志不渝坚持写作的恒心。门罗的父母亲都不是作家,也无法对其进行指导,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对她的很多影响甚至相当负面。门罗所身处的小镇也并非文学小镇,不过是世俗的大众社会之一角罢了。她曾经谈到写作时说,只要大家努力工作,都可以做得到。
其次,文学创作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就连主题也不必非宏大不可,完全可以是些凡人琐事,重要的在于文学能否反映人世间那份普遍的情感,能否去思考人生的莫测所带给人的种种困惑。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门罗写不写长篇小说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从她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长篇小说中可以想要的一切。
再次,文学可以关乎政治,也可以关乎民族,这些都可以使文学走向世界;同样,文学单纯表现个人,单纯反映一隅,单纯描写人性,同样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在评论门罗时,有人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有人说是家庭现实主义,也有人说魔幻现实主义,但无论何种主义,无论何种研究方法,文学就是文学。即便是在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文学依旧应该保持其反映人性这一最基本的特征。
阅读门罗,我们大体上可以感触到人生之不确定与世事之变幻莫测。有批评家说,我们从门罗的作品中看到的无不是逼真的人和事,这不是模仿,它就是现实,就是我们人类本身。或许,这正是门罗作品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