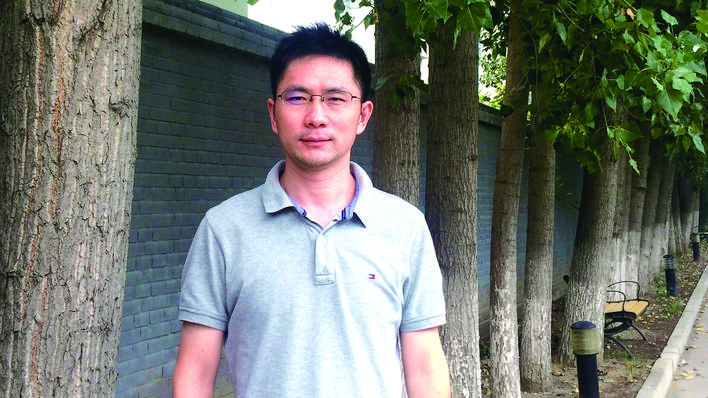告知家人要去鲁院“回炉”的讯息时,向来默默支持我的妻子流露不满。你不已经去学习过吗?孩子这么小,4个月看不到爸爸会在心里留下阴影你知道吗?上了鲁院就一定能写出好作品吗……面对妻子的驳斥,我当时哑言以对,不知该给出一个怎样的回答。
还是出发了,妻子整理的行李箱。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枕着车轮与铁轨哐当哐当的撞击声,意外地失眠了。和文学奇异的相遇,年月深久所砥砺生发出的“执手偕老”之感,如两个深爱不悔的人即使天各一方也日夜翘首。文学一次次悄然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从学校到报社再离开,教师证记者证注销,独自到省城,两地分居,周末往返,演绎双城生活,从一个业余写作者到每天要与文学与作家打交道的作协机关服务岗位。这样的身份转换,于创作是利是弊,如何校正头脑中的固有观念,轨迹之变又能走多远……
也许,我就是带着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重新来到鲁院的。
新鲁院的安静舒适,新朋旧友的亲密交往,依然如“家”般温暖。因为是“回炉”,生活上的陌生感很快消失,取代的是同学们对各自创作计划的投入,是散步时宽广话题的热议,还有鲁西迪新书《午夜之子》的荐传,偶有“放风者”抬头望望玻璃天窗外的天空,隔栏投去对鲁迅悬挂头像的注视,一支烟工夫就又钻进了紧闭的房间。院落、楼道总是安静的,但我听得到文学拔节生长的响动,匝匝有声,铿锵有力。
一天夜间,弋舟兄和我在鬼金的房间,欣赏他的油画涂鸦。随手撕扯下的画册纸上,色彩重叠,影像绰约,一个人,一棵树,一种情绪,一段爱恨,缤纷意象,扑面而来,在一方小天地之间饱满流溢。艺术之间的通感无处不在,我们谈论抽象派油画的当下窘境,话锋一转说到即将在鲁院再度过去的日子,不约而同迸发出同样的困惑。我们多数人到中年,激情锐减,理性击退感性占据上风,不好不坏、不多不少地写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70后”这一代受西方经典影响甚深,开口闭口能谈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的创作人生,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等形式风格在我们身上潜伏的深度连自己也不能准确探测,这固然是理应向经典致敬的方式,但我们到底缺什么,是否又有明晰的反思。对中国古典语言精妙广博的忽略,对写实主义的退守,对信仰、使命、情怀的闪避,与生活的隔离导致经验同质化程度之严重,我们是没意识到,还是依然故我大量补充着体内多出来的元素,而缺少的,还是缺少……最后弋舟兄一针见血地点明,按照中国的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我们是否也应该缺什么补什么。
窄小空间里的三人“回炉”夜话,让我有所顿悟和豁然。缺什么,如何补,你得自个搜寻前行,但这条道的方向不会错。身处名利蜂拥而至、物欲烽烟四起的时代,把心放在安静处,在浮躁中求得安定已不是件容易之事,写作是最需要自觉抵制诱惑和过滤噪音的事。谁都想做《西游记》中那个跟斗云一翻十万八千里的大圣,不愿当唐僧,孰不知看上去最弱最慢的唐僧,怀着对世界的大慈悲大天真,慢慢走过一山一水,才最终一笔一画写出人生和世界的真经。我们要做的正是唐僧这样的取经人。快与慢,轻与重,质地各异的金属回到鲁院这座高温火炉中重新熔化、锤炼的意义在此凸显,前行之中时常回望,不要偏离跑道。“回”,进入这个生动的世界衍生有多重含义,不是退,不是避,不是离。试想太极拳中的回收动作,是一种天地元气的吸纳、一次八面来风的积蓄,是为了更有力量的防守与进攻。
京城里车来车往,从八里庄到芍药居,两个院落依然静若处子。我曾经在鲁十三是春天来、夏天走,鲁二十八是秋天来、冬天走。两次学习,恰好经历北京的一年四季,一个循环,一种圆满。但这只是学习形式上的圆满,并不意味着结束或成功。许多同道中人嘁叹的文学边缘化,只是我们还不够自信“我所在处即世界中心”,还没能拿出好的作品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还没真正体悟到享受写作要比享受写作中不可控的成功更美好的微妙。文学就是需要一群人傻乎乎地解决终生困扰自我的问题,这既要坚守那份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又要保持那不可或缺的沉潜与深耕。
其实文学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路上有风雨也有风景,我们都懂得执念,开始了就不要停下,一直走,如同朝圣“麦加”者般拥有一颗纯粹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在火车上辗转迎来的那个清晨,窗外遥遥可见旭日喷薄,列车呼啸仍感距离甚远。回想这幕情景,借用作家七堇年的一句时髦话励志——太阳虽远,但必有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