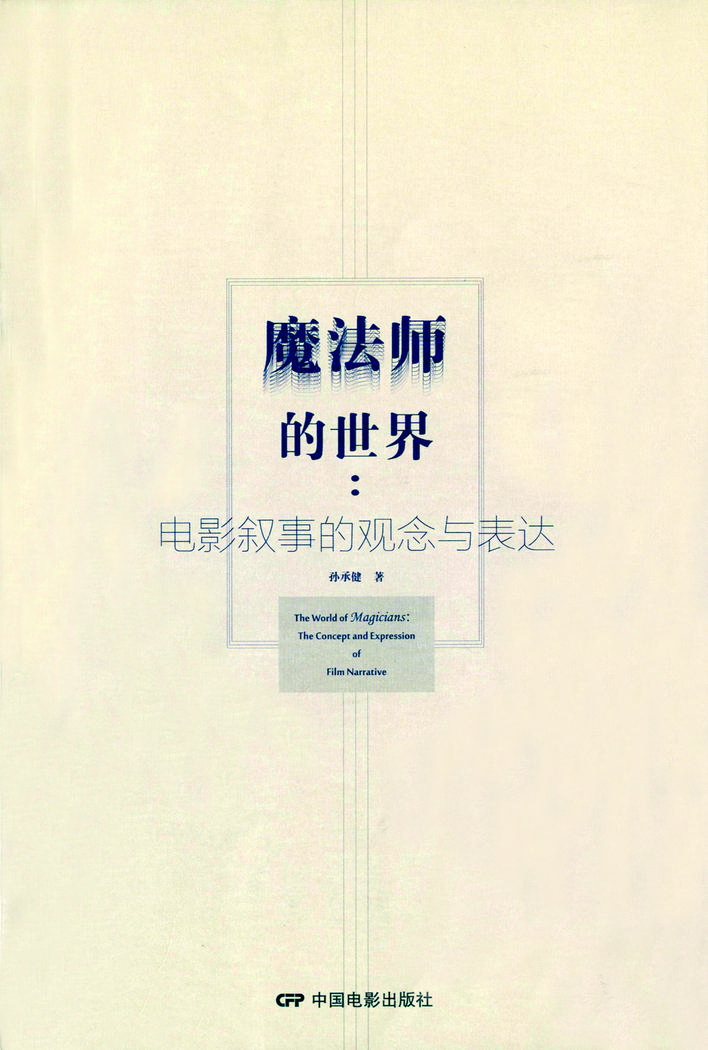出生于俄罗斯的美国著名文学家、小说《洛丽塔》(Lolita)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认为:“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对于一部艺术作品而言,“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要素,“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显然,对于纳博科夫而言,“魔法师”这一命名及其意义的内涵所指,所代表的是一种非凡的艺术创造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非凡的艺术创造性并不是对现实的“逼真”模仿,现实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而作为“魔法师”的作家或者编剧,实际上所要创造的是一个“奇妙的天地”。正是在这样一个“奇妙的天地”之中,人们基于现实与文化经验中的存在与虚无、真实与荒诞间的边界,被这些“魔法师”们借助于一种“合乎情理”的艺术想象,予以有力地穿刺。于是,那些隐匿在理性、秩序的边缘,与混沌、荒芜交织在一起的人性弱点及其欲望诉求,无以遮蔽地浮出水面,露出了其本来面目。而现实中的荒诞,与荒诞中所呈现出的真实,互为交错,从而使这个“奇妙的天地”,更值得反思与回味。
纳博科夫所言,虽然是针对文学,但在根本上也同样适用于电影。并且,“魔法师”这一命名,实际上更适用于电影编剧。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具有神话般魔法美丽的艺术创造性,并不完全适用于现实主义的表达需求,叙事作品要反映现实和表达现实,必然要遵循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表达范式,这样一种观念认知,显然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狭义而刻板的理解所导致。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主义实际上可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蕴含着“真实性”的观念和态度。但真实性并不等同于对现实与客观存在的简单复制与描摹,也并不排斥艺术创造性,相反地,基于事物本质及其真实性的追求,恰恰需要这种非凡的艺术创造性。
事实上,创作者并不需要被各种主义的观念所禁锢。许多时候,针对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人们甚至无法给予某种“主义”的明确界定。任何主义,或者主什么义,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艺术的真实性面前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意义,创作者无需将自己的创作实践,生搬硬套至哪种主义的范式之中。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曾经执导过一部影片,中文片名为《生命是个奇迹》(Life is a Miracle)。这部充斥着浪漫、夸张、荒诞、幽默、甚至是类似“漫画式”叙事风格的影片,显然无法简单地明确归类为哪种主义的作品。但创作者超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以及对战争、人性与情感的极具现实观照的反思,足以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从而也使作品本身呈现出极具真实性的内在张力。
然而,如果仅仅认识到这样一个层次,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层次,实际上在思维与认知的观念层面,依然是囿于一种普通批评者的视点。影片之所以具有某种魔法魅力,更重要的还在于,创作者有效地创造了一个纳博科夫意义上的“奇妙的天地”。并且,这个“奇妙的天地”不仅仅是观众可见的,那种物理空间层次上的构成关系,诸如创作者将这一故事设置在波斯尼亚山区铁路线旁的小镇,一个原本如“桃花源”般,充满着祥和、浪漫、欢乐的地方等等。实际上,这个“奇妙的天地”还同时包含着围绕这个故事为中心,向外拓展、辐射与延伸想象的一个更大的空间场域,这个场域即是一个文本的“世界”。就如同黑夜里在一片空旷的草原上,有一盏明亮的灯,创作者所要讲述的是有关这个灯的故事,而灯光所辐射的则是一个更大的场域。并且,这一场域的存在,某种意义而言,为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合乎情理”的逻辑前提。因此,虽然这个世界的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在观众的内心之中,这个世界却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既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即是说,这个世界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与秩序规则。正因为如此,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而言,虽然创作者仅仅只是要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在根本上,“魔法师”实际上所要创造的是一个世界,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故事是不可替代的、具有统摄力量的主体。
实际上,就宏观的叙事策略而言,大多好莱坞电影都会着力打造一个既区别于现实世界,又能够自成体系的特殊世界,或者说是一种异域世界。诸如西部的荒蛮世界、城市的地下世界,以及异时空的僵尸世界、魔法世界,甚至是科幻的未来世界、外空世界等等。在这些“魔法师”所创造的世界之中,孕育和生产了众多精彩的故事,诸如《大地惊雷》《木乃伊》《盗梦空间》《哈利·波特》《阿凡达》《银河护卫队》等等,都可以说是这些异域世界的产物。事实上,几乎每一部影片,都可谓是“自成体系”的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特殊世界,而“体系”所指涉的恰恰是一种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属于虚构与异域世界的一整套秩序规则。这种秩序规则也在根本上构成了整体叙事的逻辑起点。并且,秩序规则得以有效建构的基础,是基于创作者、电影文本与观众之间所形成的某种约定性。这种约定性的产生,自然与文化无意识层面,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范式所型构起的整体人文观念密切相关。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被文化所创造。正如中国传统的武侠电影、玄幻类电影等所具有的江湖世界、鬼妖世界一样,异域世界中的秩序规则所折射出的,实际上是文化中的人的某种精神指向。
然而,与好莱坞电影相比,当下中国电影的整体叙事策略,似乎缺少这样一种特殊世界,或者说是异域世界的创造意识。这样一种现象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这一现象也导致在创作表达层面,当下中国电影只是不断地复制和挖掘传统文化中异世界的文化元素与精神意象,而缺乏新的创造性。这其中所涉及的一个有关认识论层面的重要问题,即是创作者对于异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并不是建立在构建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秩序规则层面,而是在消费娱乐层面,将异世界的各种视觉元素,作为一种文本消费的符号,不断地复制并予以娱乐化的消费。其中所缺失的,正是针对虚构与异域世界的秩序规则的创造性,而这恰恰是涉及一个叙事文本内在精神指向最核心的问题。
(《魔法师的世界:电影叙事的观念与表达》,孙承健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