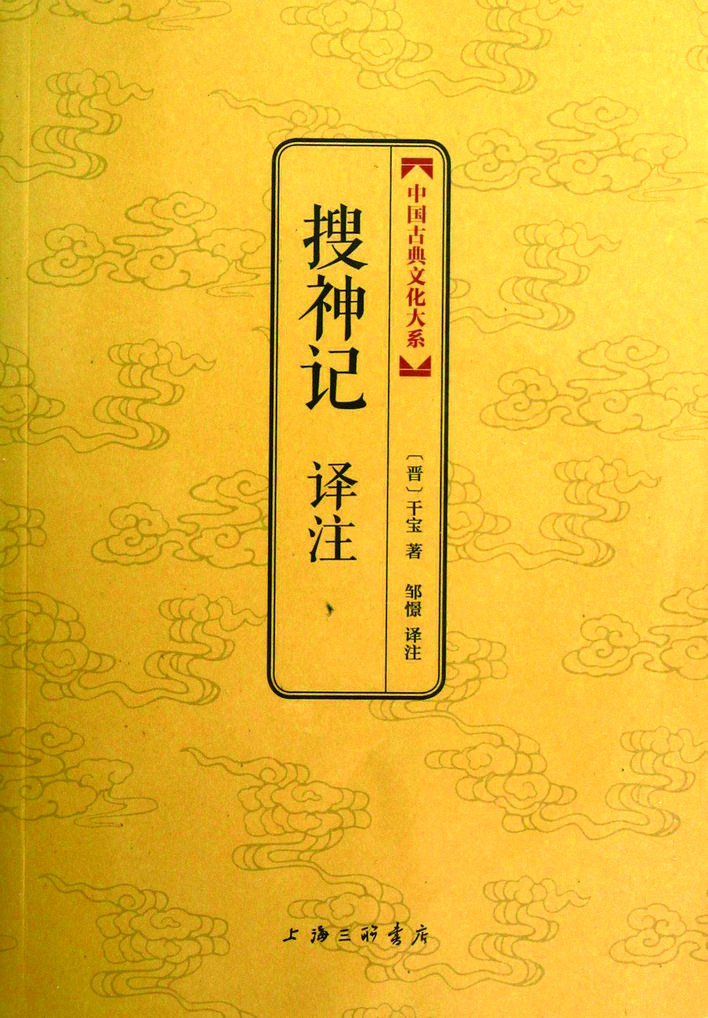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曾这样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此番说法未免有些刻薄,却也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新文化运动自身的问题。在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传统上,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以新异动人之说,迎阿少年”,“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进而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变迁讨论新文化运动对其全盘否定式的态度:“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
这场争论至今已过百年,那些激进的或基于权宜之策的考虑自然也逐渐淡化。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没必要重新回到那个具体的语境为二者断一个是非,倒是着眼当下,重新对这一命题加以审视,可能更有现实意义。正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那些被重新叙写的神话、传说非但没有因“故事”的“传统”而显得不合时宜,反而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了特别的意味。即便不去深究其间颇具针对性的讽刺,单就小说在几近凝固的传说里“只取一点因由”而铺展开来的巨大想象就是弥足珍贵的。它不仅是一个重申小说而非史传的过程,而且经由想象让那些传说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产生具体而又活跃的、不断翻腾的文学内力,其凶猛、凛冽、诡异、俏皮、滑稽相比那个时代正襟危坐的创作更加显现着小说的属性和魅力。而后观新文学百年,很大一部分创作似乎自然免疫式地将中国传统文学的资源排除在外,以后知后觉、奋起直追的方式在短暂的时间里重现了西方文学的演变。这固然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式,但从其结果或文化多元的角度看,又难免令人心生遗憾。那种拿来主义式的写作,在当时固然显示着它的新异,但这种新异同时又成为了它自身的牵绊,那似曾相识、大同小异的文学“现代化”在完成其时代使命之后便昙花一现般地杳无踪迹。这其实也在提醒着穷追猛赶式的“创意”或“实验”难以逃脱的宿命。这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传统与资源的模仿、吸收与再创造,而是避免其进入某种单一循环的尴尬处境。因此,在不断向外汲取养料的同时,整理、调动中国传统文学的资源,使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激发文学的生长无疑是必要的。
李敬泽借《诗归》的序文在《咏而归·跋》中道出了新作意欲“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咏的是“古人之志、古人之书,是自春秋以降的中国传统”,而归则是归家,是心和眼的去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身处当下某种心灵可被安放之地。比照之前的评论文章,李敬泽在《咏而归》里似乎显得更加自由放纵,行大道而不拘小节,嬉笑间把事情摆摆清楚。在这种“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叙述里,其实有着颇具匠心的文体意识,它是语言也是态度,正如弟子在孔子面前各陈其志,最动人的却是沐浴、吹风、唱着歌尽兴而归,所谓生活或生命的真谛本不需要过于一本正经或多费口舌,更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比如在《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中说,尊严就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刻“烈然返瑟而弦”,乱世之患、大寒将至,于道何干?再如《孟先生的选择题》里,孔子比孟子的可爱之处恰恰在于其人性的弱点,在于“好商量”,而孟先生手握大是大非,政治正确,但现实生活却不是仅凭道义与是非便可以大而化之的选择题。《一盘棋》里,宋闵公与南宫万的一盘棋下得血肉横飞,凭空为人世添了一缸不知去处的肉酱,也下出了“面子、荣誉、风度、胸襟”等等虚文——“但人类生活如果虚文不讲或者讲不好,那么剩下的也就是硬的暴力、软的酱”。李敬泽在古人的志趣里为当下的灵魂寻找一个归处,它是现世的文学想象,也是重申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老理儿,它不是将人们引向远方,而是把古人那些早早参悟却与高深艰涩无关的情怀与哲学带回人群之中。这就像我们已然起早贪黑不可挽回地加入了早晚高峰,但这也没什么,只要心里装着“迎曦而出,沐夕而归;伴虫入眠,闻鸡起寝;循天时而动,不负光阴华灿”就不会觉得太悲催。
还有一些青年作家重新捡起了志怪的传统。但此时的“志怪”却不同以往,它更多地指向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再创造。传统志怪小说往往带着弘扬神道之心来记述鬼神的传奇,如《搜神记》是要发现“神道之不诬”;《洞冥记》旨在“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列仙传》是为明确“铸金之术实有不虚,仙颜久驻真乎不谬”。但在赵志明的《无影人》《中国怪谈》和阿丁的《厌作人间语》等作品中,修仙成佛、降妖除魔或人鬼情谊皆不指向鬼神本身,而是更多地继承了志怪小说在故事曲折婉转、气氛渲染以及天马行空的虚构与想象上的文学经验。志怪将小说内在的矛盾推到了一个更紧张又更奇妙的层面,因为它的奇与怪,大概在今天人们已然先行预设了它的“不真实”,但它本身又竭尽全力地追求着“真实”,至少在读者合上书的前一刻,它不能先行破坏了那种被营造出来的真实感。这种尖锐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对小说的故事、语言、氛围、场面提出了更高的文学性要求,毕竟在这一逻辑里,只有信其为真,小说才能更有效地与阅读者发生关联,才能由文字、文本转化为可以形成对话的经验,才能让人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具体的环境,可以突破肉身所在的种种局限,遇见从未遇见的人或非人,体验从未体验的生活。《中国怪谈》中的《庖丁解牛》显然已与“养生”无关,赵志明大篇幅地续写了“解牛”之后的故事。备受优待的庖丁最终接到了魏惠王“解人”的要求,人们像迎接盛大的节日一样怀着战栗、好奇又隐隐乐于以身试刀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没有谁可悲或荣幸地成为那块试金石,庖丁手起刀落,在一瞬间将自己肢解完毕。“在这方面他显然是自私的,他让在场的人看到了绝唱,却转眼带走了杰作,徒留深深的遗憾”——庖丁的“自私”无疑成就了大德,他以自我献祭的方式终结了某种技术性自负所隐藏的道德危机。小说因而指向人心,指向了人的自负。阿丁的《厌作人间语》是对《聊斋志异》诸多篇目的重述,“重述聊斋——这是我认为的,向蒲留仙老先生致敬的最佳方式”,但阿丁的重述不仅把基本的故事情节安置于当下,而且在一些重要关节进行了颇具时代感的改写。其中的《乌鸦》源自《聊斋志异·席方平》,原本魂入城隍庙为父伸冤的故事在阿丁那里变成了更具现代意义的虚无。种种酷刑在《乌鸦》里似乎成了必须经历的繁杂又恼人的过程,而真正使“我”感到绝望的是那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声音和语言的什么都“没必要有”的存在,这种没有来由或固执地发于内心的绝望与虚无构成了对阿丁笔下的席方平最彻底的摧残。《聊斋志异》中那个由恩怨推动的轮回故事在重述里以相似的曲折情节变成了现代人难以抗拒的精神困境,相比阿丁自认为的“狂妄”,这更像是一次对原作极具深情的致敬。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学的诸多重要资源与经验远远没有充分地进入到当代文学的创作中来,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乎写作技术的问题,还与情怀、趣味以及心灵归属有关。所以,当我们重拾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无辜地淡化、隔绝、排斥的中国文学传统,让它在新的环境里重新焕发生机时,也许会发现它是可被亲近也易于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