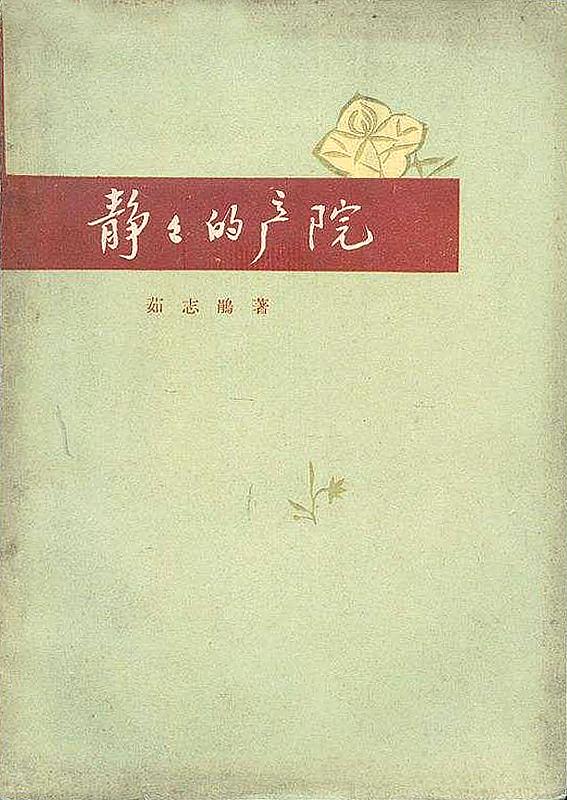作为小说来说,最基本的美学特征就是它的叙事性,也就是写作者会按照时间顺序或者其他某种顺序来进行有策略性的叙事。因此,这决定了构成小说文本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叙述者”,即是说,究竟是谁在对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这个讲述者有时候是作家本人,而有时候却是他创造出来的某个人。这个讲述者是陈述故事的行为主体,又或者称之为“声音或讲话者”。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视角”,是根据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即是说它确定了故事的来源与方向,表明了是从谁的角度在看故事,观察故事。
不同的叙事视角,会对小说文本的内容以及小说的质量起到极大的影响,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不仅决定了读者能看到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是如何看到这个故事的,甚至会最终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写作家在选择角度时,一方面是为了自身叙述故事的方便,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叙述策略,通过一种刻意为之的策略来达到某种叙事效果,使读者获得某种阅读快感。也就是说,我们在探讨阅读的时候,其中对叙事视角的探讨,会帮助我们了解到作为讲述者的本人,希望读者看到什么,或者希望能产生一种如何的文体效果的主观意图。因此,本文就将从对茹志鹃小说《静静的产房》的讲述者的分析入手,考察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重点放在心理分析对阅读愉悦性的作用上,指出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这样的叙述方式的难得,以及对作家个性的体现。
谁是故事的“叙述者”
一般而言,小说中的作者都会在作品中为自己设计一个形象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因此,对于叙述者的考量也可以视为对现实中作者的考量,分析叙述者的形象和姿态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当时的现实生活以及在现实生活里的作者。显然,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视角,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技巧问题了,还包括叙述者的文化立场和情感指向,甚至包括价值标准。
常规而言,我们可以将小说的叙事角度分为全知全能叙事、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三大类型。全知全能叙事的讲述者就好像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他可以知道所有已经发生的时间,并且可以将所有的事件全面地叙述出来。这也是在传统小说中最为普遍使用的一种叙事方式。因此,在全知全能叙事中通常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然而在茹志鹃的《静静的产房》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叙事方式,虽然在她的故事里也采用了通常的第三人称叙事,但却并非是全知全能叙事。这种叙事方式,美国文学批评家W.C.布斯将这种叙事称之为“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叙述者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但把自己局限于故事里的某个人物的经历、思想和情绪中,或把自己的观点局限于数量极为有限的人物身上”。很明显,这就不再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因为叙事受到了人物角度的限制,从而变成了一种限制叙事。这样的“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往往可以比其他的叙事方式更能形成一种复杂的阅读效果,从而带来阅读快感。
这样的叙事视角在“十七年”小说中并不多见,茹志鹃应该说是在那一时期中为数不多的采用这样的视角进行写作的作家。然而在绝大部分关于茹志鹃的论文中,我们发现大都集中于对她的成名作《百合花》的论述,而关于她的《如愿》《春暖时节》以及《静静的产院》等一批作品却鲜有人涉足,至于作者叙事视角的运用就更少有人谈到。其实,在“十七年”的中短篇小说中,茹志鹃以深刻揭示普通小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享誉文坛。在这些故事中作者塑造起来的静兰、谭婶婶等人物担任了双重身份:他们不光是故事的主角,是作者描写的重点,同时也是故事的视角人物——叙述者,除了他的所见所闻之外,对于他本身的心理活动描写也是作者写作的重点所在,也是小说文本中最精华的一部分。
在《静静的产房》中,谭婶婶既是主角又是视角人物,在主角的视角中,人物的心理描写首当其冲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描写方式既可以完全反映人物心理活动的发展变化,又可以展现他的丰富与复杂性。这一点对于善于从人物心理研究中去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从而涉及他们精神历史的茹志鹃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种写作手法。同时也特别适合她去刻画一个转变型、成长型的人物,比如这样一个谭婶婶——自豪又自满是因为自己掌握了新技术,是公社刚培养出来的“新法接生员”; 激动兴奋又心安理得满足现状是因为看着公社产院从无到有,正好赶上了社会变革期的好时候;结果这一切,却在遇到了更为年轻的一代,而且也更科学的产科医生的荷妹时,变成了一落千丈的沮丧,又气又羞又失落的心情;好在故事的最后,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又被重新激发出了学习新医学知识的坦然和勇气。
这篇小说以“谭婶婶”为叙事视角,故事里的谭婶婶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她既是作品的主人公,又是整个故事作品的感受中心。在产院这个故事背景下所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事件也大都通过谭婶婶的眼睛去发现和看见。在作家笔下的千余字里,茹志鹃用谭婶婶这样一个主角人物构成了故事叙述中心,透过她的眼睛去看产院的变化,用她的心灵去感受时代的变革,在整个故事里,是她在看;她在想;她在观察;她在感受;她在起伏也是她在评价。因此,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就在于谭婶婶的心理活动的展示。
讲述者(“谭婶婶”)的心理变化
在故事中,谭婶婶这一人物形象被茹志鹃塑造得相当成功。整篇小说作者用委婉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在公社化的大背景下,农民们自己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产院,这样一个曾经进步,却不知觉间保守,又重新进步的主人公,并深入剖析了她从开心、骄傲、震惊、责备、迷茫、不安到最终愿意从新的起点再前进的心理过程。在整个作品的叙述中,并没有采用小说写作中常见的行为描写方式,也没有过多的去依靠故事,甚至也没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节描写,而是大量运用了心理描写,试图通过大量的心理过程描写来反映其中的变化,从而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比如:“谭婶婶心里翻腾了一阵,就望着电灯,恨不得立时来一个产妇,她真想在电灯光下面接生,就像在镇上,在城里的医院里一样:产妇躺在洁白的产床上,躺在雪亮的灯光下……”一盏电灯,电灯明亮的灯光都能激起这个小人物——故事的讲述者的心理涟漪。此时的谭婶婶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往昔以及现状的欣喜。然而,当象征着新思想新技术的荷妹给她的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后,当她真正走进了曾经理想过的场景之后,却产生了不同的心理感受,如:“去给医院打电话,这不是第一次,可是今天,谭婶婶心里刮起了大风。电灯、电灯下面雪白的产床,床上躺着产妇,一切都如理想中那样,可是她,她只能跑来打电话,前年是这样,去年也是这样,如今有了电灯,有了汽车,有了拖拉机,可她还是这样跑来打电话,眼看着救护车把产妇从雪亮的灯光下接走,而产妇需要的,只是一次十几分钟的手术,只要拿起剪刀和钳子。谭婶婶第一次感觉到,给医院打电话,竟是一件这样难受的事。奇怪的是,自己在这以前,打过多少次这样的电话,竟然会那么心安理得”。这时的谭婶婶,已经从最开始的激动、开心、骄傲、满足,过度了不满、闷闷不乐这样的时期,而进入到了即将接受新事物新生命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她进入到了一种再审视内心的状态。
高尔基曾经指出过:一个创作者必须尽可能地“找到自己对生活、对人们、对既定事实的主观态度,把这些态度体现在自己的行驶中,自己的字句中”。从这两段心理描写中可以发现,作者在创作中,并没有气势恢弘的场景描写,而是截取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最简单最普通的开灯关灯的片段,使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讲述者本身的过程变化,还能体验到人物性格与感情中细微的差别变化,这样的写法也正是对作者自己本身很好的诠释,她“选取一些生活的小事件和正在成长的新人,从挖掘人性美、人情美的角度去展示人物的内心和品格。 她的作品好似在磅礴的大海大江之旁逸出的一股涓涓溪流, 给壮美之风劲吹的文坛带来了清新俊美之风”。
不仅如此,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全部紧紧围绕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感情波动来进行,并没有过多的旁枝末节,而且,讲述者谭婶婶就是作者尽全力去描绘的人物,所有出现的其他人物都是为她而服务的,所有以上的一切都浓缩在了可以展现主人公灵魂深处,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却惊心动魄的一段内心戏中:“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风暴席卷而来,仿佛滔天的巨浪向前扑来,它们气势磅礴、排山倒海地向前推,向前涌,谭婶婶忽然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三年前潘奶奶的心情,那时候为什么潘奶奶对她跳脚,又对她诉苦,为什么有时候又苦了脸,谭婶婶现在知道,那是她恐慌,却又不肯承认自己落在时代的后面”。
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普遍不太关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因此这样一段去关注人物内心的心理描写不仅难得可贵,更可以视为当时中国小说中意识流的雏形了。侯金镜曾这样评价茹志鹃:“我们当然没有丝毫理由把茹志鹃着力于心理描写的方法当作最好的或是唯一的方法。在人物的行动和人与人的尖锐复杂矛盾关系中同样能够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做丰富、精细而又深刻的描绘。可是也应该提到,有些年轻的作者,他们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常常把握不牢,或是缺乏经验,不能做到精确入微的描写,他们的作品常常只告诉读者,主人公们做了这样或那样重要的事情,可是不能直接写出或暗示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写出英雄人物的一些很突出的行为,但是不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人物所以做出这些行为的心理的、性格的,实际上也就是历史的、社会的根据。……从这一方面来说,茹志鹃同志所发挥的创造性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
通过心理变化来做铺垫,
结局昭然若揭
茹志鹃将这样一个故事的中心人物谭婶婶放进了一个最平常最普通的工作环境中,放进了与工作同事的关系中,即使是两者之间发生的冲突,也并没有采用去就激化人物之间冲突和慢慢解决冲突的常规写作方法,而是从细节入手,用“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这样一种限制叙事的方法,通过她的眼,她的口,更多的是通过她的内心戏去展现她内心激烈的冲突,用了一系列的细节及常见环境去配合其内心活动,并绘制出一幅心理变化的画卷故事图,让结局昭然若揭,最后谭婶婶的成长也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也让读到这里的读者恍然大悟。
于是“风用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在后面推着她,拥着她,迫使她好像是脚不沾地地在向前走……各种各样的感情忽然汇集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情绪,谭婶婶她兴奋,她高兴,她羡慕,她对自己不满。……她觉得这一切,和头顶上那盏耀眼的电灯,是那么调和,那么相称。”
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配合相应的视角,以及必不可少的细节,使“风”、“电灯”等元素成为了力量及现代化的象征,体现出了在受到时代潮流冲击中的一系列人群,他们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的性格所受到的影响,这也是茹志鹃在塑造人形象时的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方法。
在前文所提到的视角中,“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在心理描写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在一篇故事的写作中,由于人称视角上使用的自由,造成这样的叙事方式可以随意打开人物的内心,让她去“兴奋、高兴、羡慕、不满”,让她去“怯怯的,但又是勇敢的”,直接揭示出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即是说可以更加淋漓尽致地打开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完满也更生动,人物性格更加立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茹志鹃其他的作品,比如成名作《百合花》里所塑造的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和《高高的白杨树》里写到的两个张爱珍都不如《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的形象来得丰满深厚。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叙述者的角度以及视角,对于揭示人物的精神及内心世界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由此可见,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叙事的出现,不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尤其是对之后的“普通人”和“小人物”的描绘和撰写,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叙述方式和叙事视角。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原本就是复杂多变的,如何能够讲述出一个动人心魄又扣人心弦的故事,如何能够增加阅读的体验性,对于《静静的产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茹志鹃通过“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在时代的变革下,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的嬗变过程。这本身就需要作者具有极其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显然,这样的方式要比全知全能叙事中,那种无所不能的心理分析要更符合故事的实际和阅读的诉求。
这样的心理描写方法,在现今的文学界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方式,然而在“十七年”小说中却是鲜有所见。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茹志鹃可以这样地去探索内心世界,就算不能说是开先河,但也可以说是极为冒险的一种写法,然而这也正是她创作个性的极佳体现。而这种“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的方式从“十七年”小说中开始崭露头角,也促使了之后的作家们在写作上慢慢地开始了越来越多的,集体有意识地向内关照人物的内心世界。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