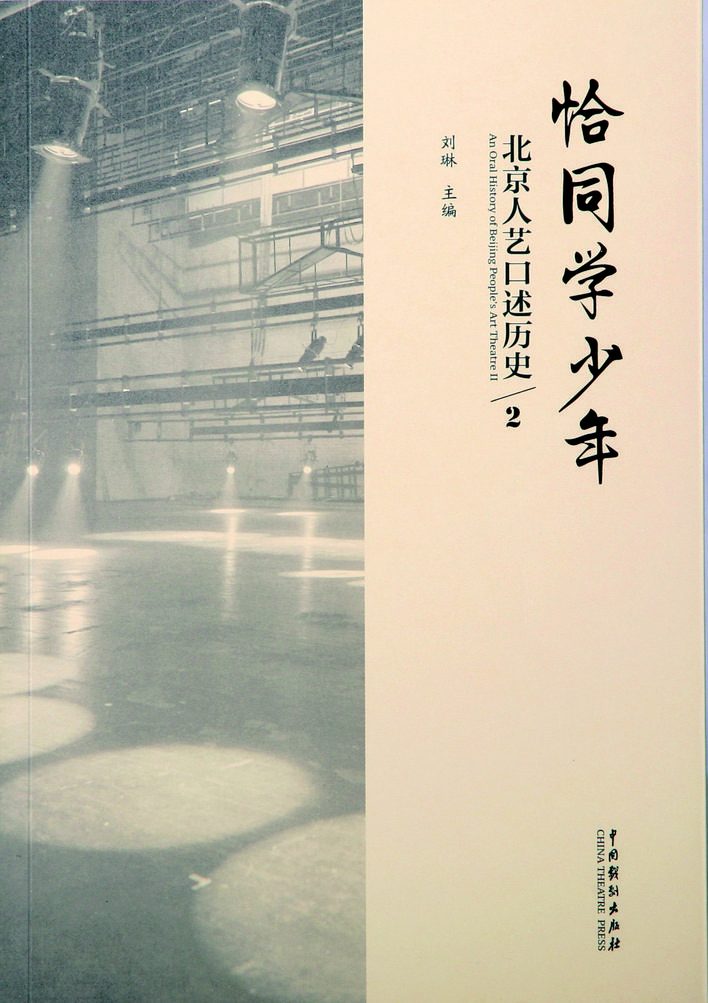在中戏表演训练班取真经
新中国建立伊始,一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来援助建设,他们遍布各行各业,有的是援建,有的是教学。1954年,戏剧界也来了几位专家,为业内同仁所瞩目。因为一直以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世界戏剧的主要体系之一,苏联的戏剧是全世界最强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共识。但那时候我们很难派出多少人到苏联去学戏剧,真正能够看到苏联戏剧的机会也很少。所以有苏联的戏剧专家来教学,我们就管它叫“取真经”,因为这真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故乡的戏剧专家来到中国亲自教课。
先办了一个导演干部训练班(简称导训班),是面向全国招生。我们剧院去的是田冲和耿震,还有欧阳山尊,他是导训班的班长。大概过了半年,第二个班——表演干部训练班(简称表训班)又开始招生。很多人去考,当时我也申请去考,不知为什么剧院没批准。后来有一天剧院通知我,说表训班招考名额没招满,还要再补招一批,苏联专家点着名让我去考。我估计他们是看了我的戏,我那个时候有两个戏,一个是《明朗的天》,我演一个志愿军政委;还有一个《非这样生活不可》,是一个俄国剧作家写的德国的故事,我演一个工程师。除了我,还有张瞳、赵韫如。结果我们三个人就都考上了,赵韫如学了一个学期就调回来了,我跟张瞳继续学。
那时候叫脱产进修,我们在香饵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院子上面加了一个顶子,还盖了一个小舞台,那儿就是我们的表演教室,其他比如声乐教室、食堂都有,我们每天就住在那儿。一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就开始上课。表演课是主课,其他还有政治课,学联共党史,还有声乐课、形体课,很多。文化课也有,还请了一些专家讲座,讲剧本。但是主要的就是表演课,是苏联专家亲自教。我们的老师库里涅夫是一位老红军,瓦赫坦戈夫剧院附属戏剧学校的校长,人非常好。
老师让我们做很多表演练习,比如说从小品练习开始。我们做完之后他当场指点,帮你加进点儿内容,或者给你一些启发,然后这个题目就结束了,明天再做新的。就这样让我们每天不停地在那儿想,老得想我还可能演点什么。反复的实践,然后他给我们指点。让我们在实践当中逐渐纳入到一个状态,理论讲的很少。这跟我们国内的教学方式不太一样,我们的教学中,学生做一个表演小品,老师老给你加工,不断地丰富,但练习的强度没有那么大。
我们学了将近两年。这两年收获特别大,比如过去剧院有一些有经验的老演员,他们演得很生动,但是怎么好?自己并不清楚。经过这段进修就让我明白了一个正确的表演道路,通过学习,我心里面建立了一个对于演的正确与否的评价标准。比方说我们从很多舞台纪录片上看苏联演员演的特别生动,他演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那种虚假造作的招数,怎么才能达到这种状态?你得演一个人的行为、行动。这个环境里有那么多人,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跟这些人之间怎么沟通、怎么交流。再进一步说就是人物形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习惯甚至于外部的动作。
表演课最后打分,要打三项分,一项是表演分,一项是导演分。当时《暴风骤雨》小说很有名,写东北农村土改的。库里涅夫说你们就用这部小说,每个人自己选一个角色,或者他给你派一个角色,你们就自己根据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做小品,做完了之后他给我们点评。最后从这里面选出一些小品来,把它连接成为13场戏,就成为一部完整的戏。本来他想找一位作家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但是当时很难找到一个既熟悉生活又熟悉剧目的作家。这13场戏的每一场都有一个学员做导演,当然还是由老师指导。别的剧目也是这样,就锻炼了我们掌握一个戏的总体处理的能力。
还有一项打分就是表演教学。库里涅夫的意思很明确:我教你们,希望你们不仅仅作为一个演员来学,以后还要能够把你们学到的再扩展开来,再带给别人。作为一个戏剧教育家,他考虑得很全面。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找到正确
的方法
在中戏带表训班的同时,库里涅夫在北京人艺又兼了一个教学点。同时他带了我和张瞳,还有田华,把北京人艺的演员分了四个班。我、张瞳、田华各带一个班,他自己带一个班。也是从单元的基本训练开始,时间不是太长,有一个多月,每个星期一次。然后就搞一个实习剧目,选了高尔基的《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下称《布雷乔夫》),因为这个戏的人物很多,能让大家都得到实践机会。后来我听英若诚说过一句话,北京人艺的很多演员找到正确的表演方法都是从库里涅夫那儿学来的。
排《布雷乔夫》受益最多的是郑榕,因为他就演布雷乔夫。郑榕也是北京人艺的一个好演员,特别用功。他那时候已经演了《龙须沟》的赵大爷,《雷雨》的周朴园,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戏排练中,有一场戏他刚一进来,库里涅夫就说回去。回去了再上场,他还是那一套,老不对,库里涅夫就不理他了。过一段时间接着排,叶子饰演妄图骗取布雷乔夫钱财的女修道士,布雷乔夫发现了她的虚伪狡诈,库里涅夫提示郑榕:拧她的屁股!用这桌布抽她……慢慢地郑榕意识到这个人得活起来,不能不管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光照着自己准备的演。从那开始郑榕就逐渐开窍了,这个所谓的开窍就是演一个活生生的人。
库里涅夫来北京人艺教学,最用功的是焦菊隐先生。库里涅夫对焦先生也很尊重,《布雷乔夫》的总导演是焦菊隐,库里涅夫只挂了一个艺术顾问,但是实际上排戏、给演员指导都是他在那里做。焦先生真的是听得最认真的,每天都做笔记。如果说他今天有事没来,一定让场记把详细的记录给他看。
从我们进入表训班进修,到库里涅夫到北京人艺办这个班,通过教学剧目来指导,这个应该是北京人艺在表演培训上的第一步。
北京人艺自办演员学习班
等到我进修毕业了,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办一个北京人艺在职演员训练班,把我学的教给大家。正好剧院那时候有这种要求,焦先生曾亲自跟我说过,觉得这一套演剧教学的方法对我们非常适合。那时候大家的学习欲望都很强,我有学习机会,但是很多人没有。当然我也想通过教学检验一下我学了多少,我学的怎么用。
最初剧院是让我和张瞳一起办班,但那时候正要排《风雪夜归人》,张瞳被选中演主角,他觉得机会难得,不舍得放弃。最后就是我来办这个班。因为给我的时间连一年都不到,我不可能按照正规的训练来做教学方案,只能按照剧院的特点适当压缩,把重点放在观察生活、观察人物的表演练习上。这个跟北京人艺重视生活积累、从生活出发是一致的。最后这个班就叫作“演员学习班”,有童超、林连昆、狄辛、秦在平等二十几位演员参加。我办这个班就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是来参加学习的得出于自愿,虽然有学习愿望的人很多,但也难免有的演员正在自己创作兴致很浓的阶段,很满足于自己的创作方法,那也不必强求。再一个要求就是申请一点经费,我想让大家大量的观摩,主要看戏曲、京剧。
学习班开始,早晨七点半练功、练声,9点开始整天学习,每星期六下午还请来中国戏校的老师教京戏武功。上课时有一点单元训练,不多,单元结合着小品。比如说“想象”这算是一个单元,我分了两步,第一步:想象,比如每个人想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的人说我在飞机上,有的人说我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我在海底,就是尽量想吧。第二步就是表演,都不要真的,就是以假当真。说我在海底的,他就搬了一把椅子当成一个小船或者是一个盆,拿着这桨就划。我说你这不对,你说的是海底,可表演的是在海面上,海底怎么演呢?正好旁边有幕布条,我就随便抓了一个挺长的,我说你在海底下蹚水,这是水的阻力,这就有点像救生带,能把你拉上岸……
所以这个教学就比较累,平时演戏就想我自己的角色,教学的话我得同时为这20个人动脑子。他演对了要给他引导,不对的话你就得想办法,光说人家不对等于是扼杀了他的创造,还得想办法引导到另外一个路上,所以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在在职演员学习班悟出来的,就是表演教学更像是一种水利工程,大禹治水。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因为他老去堵,堵是堵不住的。好的办法是该堵的堵,该疏导的得疏导,你得给它一个可以流动和释放的口子。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天性,表演教学就是把他这个天性诱导出来,把不对的那条路给他堵上。
当时大家都很投入,氛围很好。但还是有人兴趣不完全在这儿,因为他老是希望你告诉他一个秘诀,掌握这个秘诀就能演好戏了。表演是不能教的,表演是教不会的。但是又必须有表演课,所以表演课实际上是一个引导,你得把他引到一个正确的路上。他逐渐体会到了,就明白了,但真正创造起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不一定是每个人都需要经过训练,这个训练只不过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能够让你比较自觉的辨别正确和错误,好和坏,帮你少走弯路。要真正成事,还得靠自己的灵气悟性、生活积累、文化修养等各方面促成。
说到观摩,那一阶段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1957年大量的京剧名角出来演戏,基本上每一次演出最后的大轴都是梅兰芳。我记得有一次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荀慧生唱压轴戏《樊江关》,也叫《姑嫂英雄》,就是樊梨花是主帅,她的小姑子薛金莲是一个先锋(将军),两个人碰面了就在那里斗气。这两位当时都已经50多岁了,开始进入老年了,他们在台上一点儿不使拙劲,往那一站,往那一坐,就稍微的一个动作身段,你就相信她们是两个年轻的女人。
还有就是曲艺,当时全院都在学。曲艺的老师吐字清楚,他们讲吐字归音。比如说单弦、大鼓、相声,字头、字符、字尾,一个字从开始到收都要非常清楚。骆玉笙(小彩舞)也来教过我们,她听我这声音不错,说我教你一段,是《剑阁闻铃》还是《丑末寅初》?我说我特别喜欢,但您别教了,我跑调。后来她教我们班年龄最小的金昭,金昭当时十几岁,学得特别好。当时还有良小楼,她名气不大,但是教学教得特别好,她想收金昭当徒弟,金昭舍不得话剧,就没有专门学。
金昭在这个班里是旁听,她原本是要被调走的,因为那时候女演员多。虽然是旁听,但在我这儿没区别,所有实践、练习都一样。我最后的教学剧目是《名优之死》,金昭就是因为《名优之死》的刘凤仙塑造得特别成功,就留下来了。
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简化了前面的单元训练,直接进入到小品演戏,然后很快进入到人物的观察,观察生活,在生活当中看到什么人物把他演出来。这里面有很多很生动的事情,童超是最具代表性的。童超是一位个性很强的演员,基本上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他大学毕业以后没工作,我说那你跟我们一块演戏吧。他很有才,有悟性。他为什么参加这个学习班愿望最强呢?因为在这之前,他在《日出》里演王福生,谁都觉得他演王福生特别合适,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角色太适合他了。他演的还挺好的,但是没有突破,所以特别苦恼,不知道怎么能够在表演上再上升一点,所以他特别想学。可巧《名优之死》也正对他路子,为了这个戏,我用了大量的时间让所有参加学习的人去体验生活。到很多剧团去,那时候还有民营的京剧团。前门外的庆乐戏院还有一个老戏班子,他们演老的连台本戏,比如《火烧红莲寺》。我们就天天到那个戏班子看戏,跑后台。我要求这个戏里的所有角色,有演名角的,有跑龙套的,有后台跟包的,管大衣箱的(即现在的服装管理),这一套全都得拿下来,后来大家全熟悉了。
你这人物怎么来?就是要熟悉生活。你是这角儿,这角儿的行动坐卧待人接物应该什么样?因为演员接触多了,逐渐地明白了。举个童超过去经常说的例子。当时北京京剧二团(后来的北京京剧院),谭富英和裘盛戎领衔的一个班。因为我们跟这个团的谭元寿、马长礼是同龄,就混得很熟了。那谭富英、裘盛戎就算是长一辈的。因为童超在《名优之死》里就演角儿,而且是大的名角儿,他就想找名角儿的感觉,就请谭元寿给引荐一下谭老板。那天谭富英正在那儿扮戏呢,谭元寿过去说,“北京人艺的童超想见见您”,这谭富英就在那儿没反应,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没任何表情。谭元寿和童超就都僵在那儿了。僵了半天,忽然童超就明白了,这就是角儿。谭富英先生不是架子大,平常他是一个待人接物非常随和的人,但是他不怎么说话,因为他是梨园世家嘛。可这会儿他正在这儿扮戏呢,他也不会应酬,那意思就是我现在已经进入到角色了,别的都不能分心。
那时候我们还请沈三玉先生讲了很多角儿的故事,他对梨园行特别熟。比如他讲金少山的派头,金少山到东北去演出,场子都已经定好了,上火车的时候他肩膀上挎着一只猴。人家说这猴儿不能上火车,金老板扭头就走了,这头一天的演出就误了。第二天主办方赶紧和火车站协商通融,当地一个官员就有点儿不高兴,心说到我这儿架子那么大,明天你看我怎么整他。有人把这话传给金少山了,金少山也没言语。第二天这官员带着人到后台了,大伙想这是专门要整金少山来的,不定出什么事呢。没想到金少山立刻像老友一样:“哎呀!老兄你来了,好久不见呀!”那个人就愣在那儿了,“是呀,金老板,久仰久仰,你可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让金少山这气势给接过去了。他说这就是梨园行。当然这些故事不一定都用的上,但是至少得知道梨园行的人跑码头,会碰到各种事,你得会应付。《名优之死》里的人物也是要应付很多事儿。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对老的梨园行熟悉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戏是《潘金莲》,也作为教学剧目,后来大家都做了结业的汇报演出。包括基本功,有些身段、形体等等,秦在平表演带翎子的起霸,金昭还弄了一个马鞭子走了个趟马,包括唱,大家看完了都很高兴,觉得经过这半年多的学习确实很有收获。
如此,从参加表训班学习到跟随苏联专家实习,再进入到自己组织教学,我有幸经历了这个完整的过程,这一系列的实践无形中成为北京人艺探索培养人才之路的开端。从1955年到1957年,这三年的扎实步履,不但使大家在表演方法上树立了正确的观念,更推动北京人艺逐渐形成自己选拔人才的标准和科学的教学体系与方法,为1958年开启学员班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本文由刘琳根据2017年2月20日蓝天野口述内容整理而成。
(《恰同学少年——北京人艺口述历史2》,刘琳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