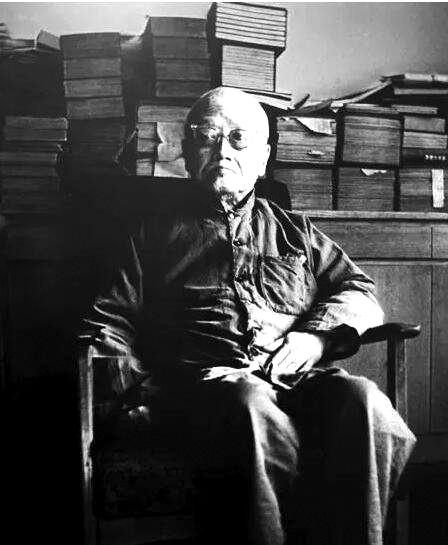《俞平伯全集》1997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张晖、孙玉蓉、汪成法、陈建军、鲍国华、李军、刘涛等学者相继披露了全集未收或失收的诗文、日记、书札、演讲稿等集外文字。一般而言,现代作家的集外作品多集中于民国时期,但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上难免也存在着未被捡拾的“零珠碎玉”。如作为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俞平伯的十余篇文章,多数已经收入全集,然仍有散落集外的篇什。
195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署名俞平伯的《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一文。1956年9月11日,该报第8版刊载署名俞平伯的《怎样美化苏州市》。两文既为全集所遗漏,亦不见《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著录,当为集外之作。现将前文抄录如下:
我觉得中国的古典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里应该占相当的比重,像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部分的编选,不论在量上、质上、系统上都嫌很不够。我自己对于中学的语文教学不曾有过很多的经验,依个人所想到的简单地贡献下列的意见。
很明显的,语文教学应该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爱国也是一种情感。爱国主义不是空泛的、教条的,应有它具体的内容。譬如空空地说,“我爱祖国”,若不知祖国到底有什么可爱的,这句话本身虽是好的,但却缺少了具体、真实的内容。在语文教学的进行中,把本国文学遗产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这就可以跟爱国主义的教育相结合了。问题在怎样才能够充分发挥,怎样才能够很好地结合。我以为要了解本国语文的如何优美,离不开它的文学。虽然语言文字的本身优点,也尽可以发挥;文学却是语文优美的最好的实际范例。有许多话不容易说得明白的,但学了实际的例子自然就明白了。
再说,历史传统是不能切断的,况且我们祖国有这样长久的历史。在这样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创造了十分灿烂的古代文化(当然也有糟粕),这个事实不容许我们忽略。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发展新的文化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不论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这角度来看,或从创造人民的新文化这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学的语文教学里都应受到相当的重视。
假如上面的观点不很错的话,中学语文课本如何选用古典文学作教材,我有三点意见:第一,不宜太狭。这并非无批判地兼容并蓄,把那些垃圾糟粕一起弄进去。但像现行课本这样选材实在太狭了。所谓古典文学原包括文言语体两个部分,文言部分或者稍多一些。我以为不妨有原则性的广泛地选录。发扬人民的感情,申诉人民的痛苦,反抗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些有人民性的、革命性的当然应该首先入选。即其他具有相当现实主义成分的和健康的抒情作品也可以选。即如表现祖国山河的壮阔、花草的美丽……也未始不可选。这并不是说必须要选,只表示标准不宜过狭罢了。如许我举例作譬喻来讲,选白居易诗,不一定光选《新乐府》,即《琵琶行》也可以选;选杜甫中年的诗,不一定光选《兵车行》,即《渼陂行》也可以选(在这里我并不主张要选那几篇,仅仅作为比喻)。至于不能过狭的理由,虽不能备举,也稍为说明一下。新的文化不能过于狭小,须从广大的面上孕育出来。从爱国这观点上看,若非锦绣山河,百花齐放,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祖国的伟大,油然发生热爱的心情呢。上面已说过无原则、无批判的国粹观点,我们当然反对;但这完全另是一回事。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所选材料不宜过短。伟大原不等于长,短小精悍之作也无妨它的伟大。我并不赞成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选过于艰深、冗长的作品,但像现在高中的课本,文言部分所选,有些篇幅实在太短。太短的毛病,不仅有时不能表现本国古典文学伟大的形象,而且教学方面也不易搞得好。简单说来,就是更不好教。听讲的学生,没头没脑的,更不大感兴味,所以也未必好学。不引课本为例,任举些短诗来说明,如《易水歌》两句,《敕勒歌》七句,两歌确是很短而伟大的。像“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确很好;不过依我个人的见解,或者竟是偏见,觉得不大好教,不容易使学生了解这所以伟大来。我认为教材,可以选篇幅适中的,稍长一些也不要紧,短小精悍的也可以酌选;长的短的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合适。若净是些短的,一篇有一个头绪,头绪本不容易引,才引出来便又放下,无论在教的方面,在学的方面,都不很经济。
第三个想法,就是不宜太少。我不知道教材的比例上应该怎样分配,方才合理。现在光就古典文学部分来说:(1)人人都知古典文学在时间上比现代文学长得太多了,约两千年和三十年之比。(2)现代文学跟古代文学是不能切开来看的,即白话跟文言也是如此。所以古典文学文言作品,如选得太少了,像现行课本的样子,非但使学生不能了解古典文学是什么,也不能了解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就不能完成语文教学应有的使命。下边就“文言”和“白话”两体的关系稍为一谈。
从历史的发展看来,中国的文学确实渐渐地在那边走向白话。所谓文言并非没有变动,也随着时代进展;不过文言自有一定的法则,又写在纸上,比口语变化要少一些,缓慢一些罢了。太远的如《尚书》、《左传》不去讲它。六朝的文章名说骈俪堆砌,实际上比两汉文章流畅优美,进步得多。韩愈他们所提倡的“古文”,名说复古实兼采当时通俗文字传奇小说,创为新体,来反对六朝旧体,所以人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这一体,总比骈文明白晓畅得多,一扫所谓词藻典故对仗等等,实为白话文开辟道路。若词曲小说采用白话或纯用白话,自然更不成问题。明代的小品文,最近不大有人谈,事实上也是一种新式的文言文。拿来抒情写景比骈文古文另有一种长处;我想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以小说而论,白话小说如《水浒》《红楼》固然很好,即《聊斋志异》有些文字实比唐人传奇尤能活跃传神。晚清的文人,对新的文言、新的文体也有种种的尝试,得到相当的成功。所以“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决非凭空起来,仗着几个文人脑子里的幻想便能够蓬蓬勃勃风行全国,实是上承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而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罢了。
上面的话,或嫌离题稍远。不过我想借此说明,假如把古典文学的文言部分紧缩成一个点儿,孤孤零零附在现代文学的后面,如何能表现这个浩浩荡荡的文章流变来,又如何能表现这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发展的文学革命来。所以即不从古典文学本身来看,改从现代文学、开创新的文学这角度来看,这样过少选材也非常的不妥当。
上边的话,不过就我想到的老实地说出来,可能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误的感觉(恐怕是当然的),就是我在这里主张多多地、大量地选古代文学作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我的意思却并不是这样。不过认为比现行的课本,选得要宽一些、长一些、多一些罢了。我希望有一个更活泼有生气,亦比较完善妥当的中学语文课本出来使教学两方面进行得更好,大大发扬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
自1920年起,俞平伯便先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执教,将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1922年7月,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俞平伯以视学的名义前往美国考察异邦的教育,以图运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以上的这些经历,使得俞平伯对教育问题不乏个人的独特认识,间或撰述相关文章。1929年3月,俞平伯曾作《教育论》,以杂文的笔调,表达了对于教育与人性关系的思考,提出教育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观”。1948年9月,俞平伯曾在北平电台作题为《孔门的教学法》的广播演讲(讲稿载于1948年10月3日《广播周报》复刊第107期),对孔孟施行的问答教学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与阐释。
新中国成立初期,俞平伯对教育依然时有关注。1952年1月,他的《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发表于《语文教学》月刊第6期,针对如何启发青年的爱国思想这一目的,讨论了语文文学课程的三种选材、语文教学中的五点原则,也应时应景地大谈无产阶级立场。一年后的《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延续了前文的部分观点,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创造人民的新文化”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古典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得到相当的重视,建议中学语文在选用古典文学作教材时不宜太狭、不宜过短和不宜太少。本文不仅体现了俞平伯对于中学语文教学中古典文学的重视,而且还论及“文言”和“白话”、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因而颇具学术价值。
《怎样美化苏州市》全文如下:
苏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历史的古迹亦很多。美化市容是很有意义的,且有足够的条件的。第一,园林的建筑艺术继承宋、元、明、清四代的传统。如沧浪亭、网师园都是宋,狮子林是元,拙政园是明,留园等等是清。虽已不能完全跟原来相同,却总保存了相当的规模。现在几个主要的名园都修整了,保存了传统的风格,可谓修得又好又省。却还有一些重要的,以限于经费尚未修缮。如网师园已荒废了。环秀山庄假山还在,房屋已很少。惠荫园在一个学校里,它的假山水,公众不容易看到。据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人说,全市大小园林约有百余处。它的缺点就在于分散。将来逐步修建,用花木的荫道连结起来,则全城可成为一个大花园。
其次,城池的建筑,原来城区的规划,不但是“古”,而且很好。苏州城建自春秋吴国,距今二千五百年,后来将土城改筑砖城,而规范大致如昔。至今所谓“六城门”,如阊门、胥门等,还沿袭春秋时的名称。在全国范围,这样的城就不多。街道纵横平行相交,作棋盘式。水道也是这样,主要的城河,所谓“三横四直”。城圈以内以外都有城河如带地环绕着。这跟北京是一个格局。很显明,不是谁因袭谁,乃同出一源。这是中国古代城池建筑规划的优良传统。
现在本地人士要现代化苏州市,这本是好的。对于拆城填河,个人有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拆城说,若为交通方便起见,则功用并不多。它以里外两条城河环着(外城河是运河胥江,不能填塞,内城河现市府已在疏浚),交通主要靠桥梁,不拆是这样,拆了也还是这样。要使城内外交通便利,多开些“豁口”造些平桥也就可以了。若从另一方面想,城垣现虽失掉军事防御的价值,但它本身亦是古代建筑艺术之一。如适当地保存城垣,配着里里外外的河水,河上种了花柳,更有北寺、瑞光等古塔点缀着,并不费多少人力,而处处都是公园。拆了城,在古迹名胜方面却有不小的损失,而且是得不偿失的。
填河情形稍有不同,亦复类似。为了居民的卫生,适当填平一部分缺少水源淤浅的小浜,像苏市目前这样的计划也是对的。但大体上还该保存水网城市的特色。古人所谓“户藏烟浦,家具尽船”。今昔情形虽很不同,但“小桥流水人家”这种光景,苏州城里往往可以看到。像菉葭巷、钮家巷,那一面河房临水,这一面靠河是树木,过来是窄窄的一条路,道旁又有人家。两岸之间,好些小桥横跨着。这样的巷陌表现了水国的风光,非常秀美。水和树木,在都市里,仿佛美人的一双眼睛。有人或者觉得城河很脏,这也是事实。但我以为水的洁净污秽不是本身的问题,在乎人们把不把水来弄脏。疏浚水道,经常保持清洁,一面美化城市,一面并不妨碍环境的卫生。这比一味地填塞,似乎要好一点。将来河道旁边种上花草树木,这苏州的市容更可以美丽了。我们不仅应为目前打算,并且应该有远景的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北京、南京、苏州等古城的开发与建设成为文化人士与普通公众共同关注的一大问题。上文首先分析了苏州园林建筑和城池建筑的特色,随后提出对于“拆城填河”的意见,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苏州古城墙,并建议美化市容“应该有远景的规划”。苏州是俞平伯的家乡,本文的写作显示了作者对于桑梓的关心,渗透了其对故土的深情与挚爱。
1945年12月12日上海《光明》第1卷第2期刊载了一篇署名伯公的《文人之痴》,同月18日《世界晨报》第2版也刊登了一篇署名俞平伯的《文人之痴》。经比对,两文内容基本一致,且与1937年8月1日刊于上海《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的散文《无题》(署名平伯)系同文异题之作。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附有《俞平伯笔名索引》,列出了俞的14个笔名,其中并无“伯公”。由此可知“伯公”是新发现的俞平伯笔名。据笔者目力所及,其他报刊上还有署这一笔名的文章。其中是否还有俞氏的手笔呢?这有待我们继续探究。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