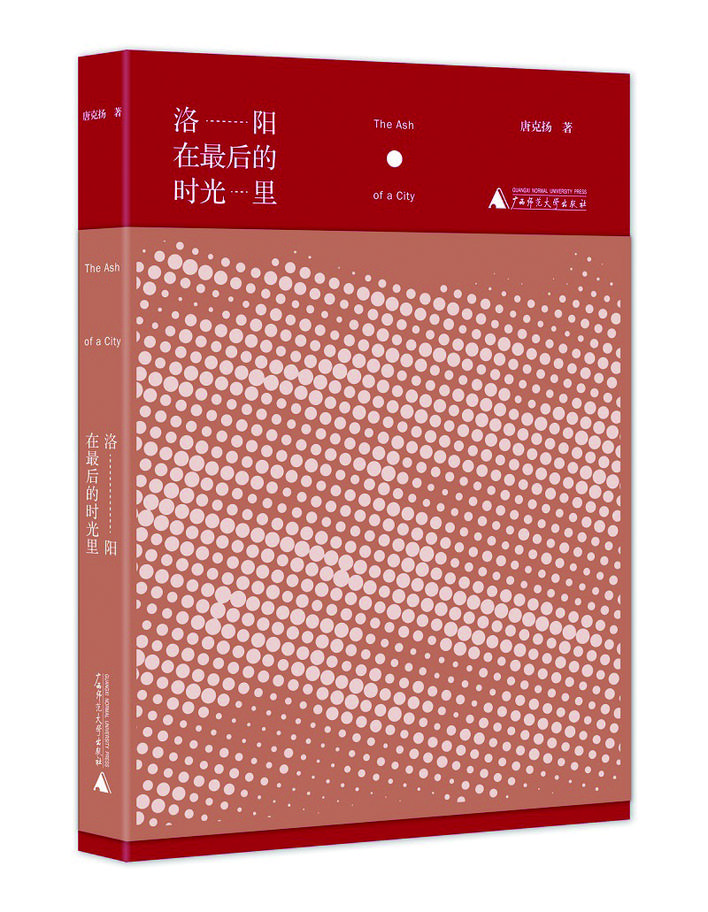20世纪里的很长时间,一个人若是坐火车经过河南洛阳东行,车从白马寺站过后片刻,沿着陇海铁路的南侧,放眼广袤的农田之间,会看见一丘稍稍高出的土阜,那便是著名的北魏(386年—534年)永宁寺塔的遗迹了。包含永宁寺塔在内,铁路两侧几无显著地面遗存的巨大废墟,原先都同属于一座古代的城市:汉魏洛阳故城。如今铁路愣是由“城中”穿行,约莫也就是3000米的路程,对疾行的火车而言不过一分钟的时间而已——人们或许难以想象,他们目光扫过的这片不起眼的平畴,曾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都市之一。
“洛阳人”“洛城人”……在中古世界,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说起这座城市居民时,那种欣羡的语气,就和今天人们提起“巴黎人”“纽约客”的口气相仿。瞧他们用的那些极尽美谀的词句,什么“洛阳纸贵”“衣袂京尘”“洛阳花下”……除了长安这另一座伟大的中国城市之外,还有多少地名,能够依然活在这些语言和形象中呢?
带着这样的向往,我去了洛阳,不止一次,既为苍凉的故城所吸引,也流连在它现时代的烟华之中。然而毫无疑问,洛阳的荣光已经不再,今日的洛城已非昨日的“神都”。河滩边漫漫的蒿草中,这座古代名城的往昔已湮没了,曾经贵为“天下之中”的十三朝古都,如今已沦落成了一个省一级的普通工业城市,被喧嚣和沸腾的当代慢慢遗忘。即令涂抹了重重的脂粉,当它以各种“景点”的名义重又回到人间,洛阳的身体里那个高贵而又遥远的灵魂已不复存在了。
洛城的兴衰,便也牵系着中国人一段失落的过去。
这种失落不仅仅是时过境迁、风水轮转,它同样也源于深刻的时代变局和文化裂痕。今日的中国城市虽则蓬勃发展,但和这废墟中的洛阳一样,它们立基于一片荒芜之上,尚显著地匮乏自己的“记忆”。
“记忆”,说起来有点“文创产品”的气息了——且慢,莫向坊间流行的历史里“打捞”记忆,莫向我开讲各色民间故事,而且是只能当旅游纪念品出售的那种……洛阳的“失忆症”病状自明,但理性地想一想,它竟是无法轻易治愈的。由舶来的西方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角度,或是几张真假难辨的“老照片”,虽然可以潦草认定字面上的“传统”——不管它们是民国还是前清,是鄙俗抑或清雅——却不能复刻出人们对中国城市历史的共识。陇海路边的这片荒城,可以让一个人紧赶慢赶地走上大半天,但它却是毫不起眼的、一览无余的,既无半分繁华旧迹,也谈不上什么显著的“古典”,眼前即得的“传统”里,倒是多了几分“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乡土气息。相信大多数今天的造访者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疑问:如此衰破的“记忆之城”,它和当代生活的关联究竟落脚在何处呢?
“古典”、“古老”本身就自动构成“经典”吗?
过去的生活毕竟汗漫无边,如果复数的文化意味着无数个彼此相异、甚至彼此冲突的个体心灵,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构成洛阳的“基础记忆”?
挂一漏万,就像陇海铁路的规划师将这座古代的城市遗忘,在同一片土地上,对于汉魏故城的探询乃至“重建”也会将更早的、规模较小、制度不同的城市形态遗忘——由今日各种与荒城有关的“复兴项目”来看,这种新桃旧符相替而致的遗忘是迟早的事:在枯竭的生活之河的断岸上,对特定历史地层的兴趣注定截短了历史,由于后人分歧眼光的注视,以及相应的形象重塑,时间里的“断层”只有程度的区别而不会有性质的不同。
就像只对精美器物本身感兴趣的收藏家将“日常”遗忘,大肆搜求秦砖汉简的博物馆,多半将这些展品干净但是孤零零地放置在黑屋子里,这样一来也已将更广袤的“文化”遗忘。各种轻率的“戏说”显然是不可靠的,但是面对茫茫一片都不见的文明的废墟,个体的“心灵”和广大的“外在”之间更直接的联系也亟需得到重建。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作为社会实体的城市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折光,与此同时,作为众多有形建筑物的构成体,城市又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
因此,城市既是集体的“产品”,又是为集体而创作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它既是可科学研究的对象,又很难不设身处地去体验和感受。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纸面的城市历史,或是过分骄纵不加审视的“感性”,都是理解历史城市的歧途。
当有限的现实向无限的过去发问时,我们的知识就陷入了经验的泥沼;反过来,仅仅靠抽象的、冷冰冰的事实也并不能织就有生命的历史。作为天翻地覆后的新世界里的中国人,我们对过去想当然的“知道”,其实往往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声称热爱的一切我们其实是全无感知的。
一切魅惑将从城市失去记忆的那一刻开始……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唐克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