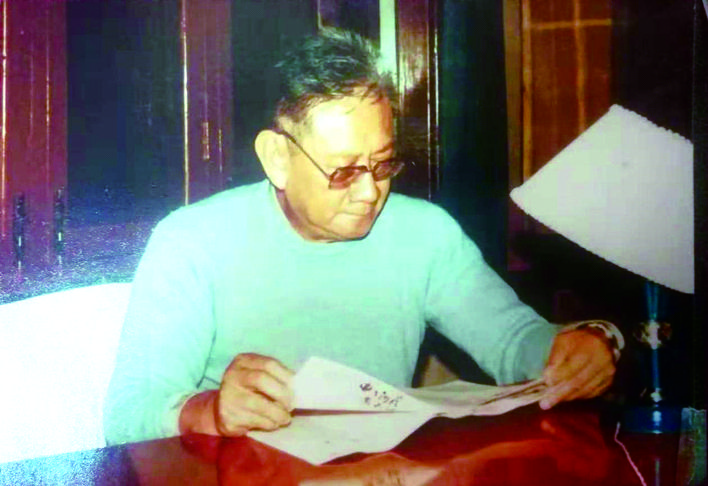《秦牧致姚雪垠》,写于1977年10月12日;以《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为题,初刊于《上海文学》1978年第2期。
从1977到2018,41年的时光消磨,把这封信酿成了史料,且因为珍稀而宝贵。现在又翻出来,连带其相关信息,一起简短截说如下,既图与读者共享,也为表达对秦牧先生的追怀。
(一)写信缘由
1977年4月6日,姚雪垠致秦牧信函一件,一是告知“《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三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分两次挂号寄上”, 二是坦言“书虽出版,心情反觉沉重”, 因为“对如何写历史题材,如何古为今用,如何写大部头长篇小说等问题”,“虽然作了一些探索,但深感认识不清,功力不逮,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借第二卷刚出版的机会,除征求工农兵读者的意见外”,希望文学界的同志们也能给以帮助“提提意见”;三是请求秦牧“看完第二卷以后考虑考虑”,殷盼能满足其愿望。
秦牧先生是文坛多面手,散文、童话、小品、小说等门类都富有产出,历史题材也是驾轻就熟,但他毕竟是作家不是评论家,对他来说,搞文艺批评等于为他人作嫁,是远比搞创作要繁杂许多的大工程。何况《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三册近百万字,通读、摘录、品鉴、评说,然后再整合再叙述,待一系列动作完成,该有多少精力多少时间要被耗费掉!但秦牧先生毫不犹豫热情应承,在信中谦虚而真诚地告诉姚雪垠:“由于您谦虚地向各方面征询意见,也问到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下这份答卷。”
到底是散文大家。秦牧先生的“答卷”,洋洋洒洒6000余字,形似信件实为文评;去掉台头和落款,就是一篇用散文笔法写成的“《李自成》专论”。其格调之昂扬,视野之开阔,神思之绮瑰,语言之灵动,都可以与作家本人的散文名篇《土地》媲美。文章纵笔放谈,旁征博引,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绚丽的情采和丰厚的知识洋溢于字里行间。
(二)信文内容
正文共有18个自然段,内容大致如下:
第1段(约270字),为姚雪垠生命不息笔耕不辍的奋斗精神点赞:“您以六十八岁高龄,致力写三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单是这种意志和毅力,就很令人敬佩。”在秦牧先生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勤奋些才对,作家应该比一般仅仅按时上下班的人勤奋些才对”,但他眼中的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文艺界“艰苦奋斗的精神看来还是和时代不很相称”,所以他由衷希望姚雪垠的“这种工作精神”能和他的小说一样,“为更多的人所知道 ,从而也起一种擂鼓助阵的作用才好”。
第2段(约2200字),全面肯定《李自成》的“巨大成功”和“杰出”贡献。行文可分3个层次:
第一层,读后感言和总体评价。“读《李自成》,是一顿精神上的盛宴,有一种艺术享受上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鞭辟入里,荡气回肠。”秦牧先生以其特有的诗性语言,热情赞扬姚雪垠“准备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三百万字的篇幅,来写一部关于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小说”,认为“就已经出版的部分看来,写得这样笔力万钧,气魄雄伟;这样的有血有肉,活龙活现,是很可钦佩和庆贺的”。
第二层,肯定《李自成》“既是一部写明末农民起义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概括地写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和封建皇朝斗争历史的代表作”。文章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绵亘不绝。明朝从永乐到崇祯,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民起义更是浪花奔逐,世代相继。明代的农民起义是历史长河中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继续,而以李自成为主要代表的明末几乎遍及全国数大流域的农民起义又是明代无数次起义的继续”。作者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遍数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次次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农民起义,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明季的阶级大搏斗中,“官军刽子手和农民起义军方面,各自都是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又到了朝廷内里蛀空、边患频仍、大崩溃的前夕,作为义军杰出代表的李自成义军和朝廷双方的搏斗,更具有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拼个你死我活的严峻性质”。所以,作者认为:“描绘这一场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场面,并以此为经,写出明代末叶,从朝廷、通都大邑到荒村僻野的人物百态,这么一部鸿篇巨制,它所具有的代表性是十分突出的。我们从中很可以窥见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斗争的一般风貌。”
第三层,肯定小说主人公“李自成”的形象塑造,进而肯定《李自成》“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历史上伟大的农民英雄树立丰碑,而且也在于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面貌,提供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文中写道:“李自成以一个雇农,驿卒,在地方贫瘠、灾难频繁、人民负担沉重,阉党剥削最残酷的陕北崛起草莾,迅速成了起义军的卓越骁将,在高迎祥战死后被推举继任闯王。数年之间,虽然备受打击,艰难竭蹶,潼关南原一役,甚至曾经全军覆灭;以后在商洛山中,在郧阳山中,屡次受到严重围困,甚至还有部下企图叛卖,张献忠阴谋吞并等凶险遭遇,然而他领导义军,坚持斗争,看准时机,疾趋河南,终于迅速使一支人数稀少的疲敝衰兵发展成为百万雄师,下洛阳,杀福王,纵横河南,平定陕甘。同时起义、揭杆称王的各路义军领袖纷纷自动归附,义旗所指,终于麾师直下京畿,迫使崇祯自缢。如果李自成没有异常过人之处,十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颇为严格的军纪,相当周密的规章制度,以及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谋士战将,深得群众拥护,是断然不可能达到这一成就的。”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长篇小说《李自成》的杰出之处,在于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通过李自成驰骋疆场,平定哗变,关心民瘼,激励士气,待人接物,罗致贤豪,追忆往事,论述形势,以至起居饮食,读书练武等许多细节,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得光彩照人而又翔实可信。同时,围绕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描绘了一系列正面和反面人物生动的形象,剖析了这其间的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了巨幅的充满了工笔刻划的细部历史长卷,使读者开拓了对近古生活的视野,又从中体会到事物发展的规律。”
第3-9段(约2200字),分析《李自成》“大获成功”的原因。
其一,“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处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从中整理出重要线索,以简驭繁,条理清晰,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做得相当好。”“一方面,大力塑造农民革命英雄人物,加以讴歌赞美;另方面,也不讳言李自成具有皇权思想、天命观和受到孔孟思想的侵蚀。若干属于艺术虚构性质的情节,也充分注意到在历史上发生的可能性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秦牧先生认为,正因为作者坚持了唯物史观,坚持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使得小说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使人读了有恍似躬历其境,亲闻人物馨咳的感受”。 而“由于生动真实,小说中不仅李自成、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人许多纵论天下大势的言谈引人入胜,就是一些恰如其分地出自各种身份人物之口的粗言俚语,也产生了艺术魅力”。
其二,“作者具有异常丰富的史料知识,并且又有相当深厚的现实的感性知识作为融会贯通这些史料的基础”,从而“做到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程度”。 “小说展开了明代社会生活的长卷,首都、城市、农村、山川、战阵、营寨、驿道、寺庙……以及宫廷、朝仪、官制、农事、百工、风俗、喜庆、医药、卖解、狩猎等许多场面,各种各样正面反面的人物活动其间,仿佛把读者导进了一个古代封建社会的博览馆”。
其三,“《李自成》除了描述起义农民群众和明朝官军的博斗,以鞭挞剥削阶级、讴歌义军英雄、表现历史规律作为总的主题外,还随着各种人物的登场和大小故事的开展,体现了许多副主题。众多的副主题更加丰富和深化了总主题”。“写周后生日,宫女刺血写经以及和尚被迫自焚,既暴露了皇后、太监、长老们的残忍卑鄙,也揭开了作为精神鸦片的宗教黑幕。写李信妻子汤夫人在丈夫决定投奔李闯王的时候,深思熟虑之后,怎样饶有深意地赠剑红娘子,又怎样留下了缠绵悱侧的绝命诗,一系列自尽前后的经过,既写出她作为‘卫道者’的一面,也写出她作为礼教牺牲品的一面,揭示矛盾,很有深度,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总之,《李自成》“正如一株参天大树,不仅有主干,也有枝丫一样”,“许许多多的副主题,宛似枝杈围护主干,众星拱卫北辰,加强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力量”。
其四,小说中“群像罗列,互相辉映”。“书中不但塑造了李自成、张献忠、刘宗敏、袁宗第、老神仙、牛金星、宋献策、高夫人、郝摇旗、李过、双喜、李岩、红娘子等人物,就是一个义军的老兵王长顺,也都写得绘声绘色,活龙活现”。“对垒的人物方面,崇祯和他的后妃,卢象升、孙传庭、熊文灿、洪承畴、杨嗣昌、黄道周、福王、左良玉等,也都写得栩栩传神”。“书中用大量笔墨刻画崇祯”,通过“临朝、议事、驰马、问卜、下棋、‘省愆’等许多细节”, 反映出他的“残忍忌刻而又故示宽仁大度;刚愎自用而又装作博采臣议;实际上颟顸无能、贪婪成性却又标榜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本质,既“使读者加深对剥削阶级人物的认识和对明廷崩溃之势已成格局的了解”,“而且也更加烘托出义军英雄们品格的光辉”。
其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能够时而粗犷,时而细腻;时而意笔,时而工笔;有时远望全景,有时显示细部,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这种“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的艺术手法,使得细部和全景彼此衬托,交相辉映。书中既写‘城头战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千里无鸡鸣,铠甲生虮虱’的景象,也以讽刺之笔写辇毂繁华,朱门歌舞。一下子鼓角雷动,气吞河岳,一下子是箫笛轻吹,柔情如水,使人获得一种既惊心动魄,又低徊吟味的感受”。“正如茅盾同志所称许的:‘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鹍弦,风光霁月’”。“这种手法贯穿全书,大大地增强了艺术魅力”。
其六,作者在许多节骨眼上,都倾注了强烈的感情。“高夫人探视慧梅箭伤,李信征途闻耗,红娘子结亲,刘宗敏审问吕维祺,闯王审问福王等章节,都可以看出作者流露的深厚感情,这自然增加了小说的动人力量”。
第10-17段(约1000字),指出读《李自成》时“所见到的缺陷”:一是存在前后矛盾现象。如郝摇旗贻误戎机后,前面李自成吩咐张鼐派人将其“送往老营看管”,后面又对郝说“我叫你暂时住在麻涧,听候处分,不要来老营见我……”二是偶尔顾此失彼。如刘宗敏救村女,跃马渡江写得有声有色,渡江后被救村女却无声无息。三是个别情节头重脚轻。如对土豪宋文富兄弟,前面写擒拿审问时笔墨浓重,后面写诛杀时却寥寥数语轻轻带过。四是有的悬念隔断太久,给人以头绪纷纭不够完整的印象。五是常常在故事进行中对一些新出现的地名进行解释说明,其结果是影响语境氛围,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感。六是行文中的长篇议论颇多,其中那些“论述山川形势、探索战略战术、追溯历史旧事、分析敌方心理的言谈,为小说情节展开所依据,而且也加强了小说的气魄”,但“有若干段落显得沉闷”也是事实。
第18段,录《读《李自成》二卷有感》七律一首为全文结语:
怒马哀兵闯字旗,弯弓奋剑下京畿。
沧桑几度斩皇历,穷僻千秋说义师!
欣际锤镰开广阔,笑驱雾障辨迷离,
膏腴大地生花笔,三百万言写史诗!
(三)秦牧与姚雪垠
一封信,或者说一来一往两封信,把秦牧与姚雪垠两个文坛宿将连结起来。此前他们之间似乎不曾有什么过从,此后有了,但所见史料记载也只限于大型文学活动中:1979年7月,姚雪垠主持创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后更名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在广西南宁成立。秦牧与丁玲、于黑丁、王朝闻、艾青、吴伯箫、肖殷、杜埃、杜鹏程、俞林、柯岩、秦兆阳、秦似、康濯、魏猛克、黄秋耘等同为顾问。1980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年会)。会议期间,曾邀请秦牧先生莅会作专题报告,题目是《散文创作一得谈》。1985年1月,《南洋·星岛联合报》举办“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和“新加坡华文文艺金狮文学奖颁奖大会”,姚雪垠、秦牧、萧乾均以“评委”身份应邀出席。后来秦牧先生曾作《思索三毛的悲剧》一篇,其中有专门记叙三毛与姚雪垠在告别宴会上的一段文字。1991年12月,姚雪垠赴广州出席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10届年会,会后作《在珠岛宾馆宴请欧阳山、关山月等老友》七绝一首,诗曰:“旧雨文坛人渐少,风流怀想意纵横。岭南高照关山月,粤海旗飘宿将营。”结句下有注②言:“目前全国集中老作家较多的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广州老作家年龄较高的是欧阳山。其次是杜埃和陈残云,将近八十。秦牧和黄秋耘较年轻,也都过了七十。这一批老作家成就不同,都算是文坛宿将。”
从上面所记可以看出:秦牧与姚雪垠不是“莫逆之交”类朋友,而是清淡如水的“知音”和“同志”;他们不是“深交”是“神交”,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事业上的惺惺相惜。他们一个谦虚谨慎,一个自矜自骄;一个平易亲和,一个锋芒毕露——脾气性格的迥然不同,并未妨碍他们的相互欣赏和推重,也没挡住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相契相通。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秦牧读《李自成》时的倾心倾力真情投入,也才有了他评《李自成》时的无所顾忌高声喝彩。就在《秦牧致姚雪垠》中,他这样说:
“《李自成》这部长篇,在人物塑造、生活色彩、思想深度、艺术魅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上乘境界。”“我很高兴同时代有人写了这么出色的历史小说,我衷心地喜爱和赞美这部长篇!”“这部长篇,具有批判地反映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雏型的性质。人们即使仅仅想了解封建社会横断面、纵剖面是怎样一个概貌,也是很应该读一读它的。”“中国曾经在封建制下经历过茫茫长夜,在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旧的因袭的重担还常常压在人们的肩上。较系统地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封建制的剥削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封建主义的流毒,对于我们今天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清除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小山也似的垃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部小说,在这方面也大可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所以,“我觉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很需要阅读它,这不仅是文学欣赏的需要,同时也是政治学习和历史学习的需要。”“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仅为当代读者所热烈欢迎,并且必将成为世代流传之作。在若干年代之后,它也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推断,而不是溢美之词。”因为,“在一个古国获得了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今天,我们必然有一批优秀文学著作,其中包括若干优秀历史小说要涌现。而若干当代杰作,会成为将来的‘古典名著’,自也毫无疑义。如果说前人所达到的文学水平是今人所不可逾越和企及的,不反而是无稽之谈吗!”
摘录至此,欣然发现:40多年土埋尘封,竟遮掩不住老作家的激情奔涌神思飞扬,改变不了老作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爱憎分明的情怀,光明磊落的态度,既见文品又见人品;言近旨远的文字,潇洒自然的抒发,既寓思想意义又具文学色彩。秦牧是在评说他人,也是在诠释自己。形诸内而发诸外的真诚与坦荡,洋溢着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浩然正气。听,还是他在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所谓‘真’,就是要阐明生活的本质,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诓诓骗骗。所谓‘善’,就是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
知道《秦牧致姚雪垠》早已翻篇,也知道信中蕴含的思想阐发的观点和流露的感情都已过时,却依然念念不忘秦牧先生那些灌注了“崇高”“健康”“先进”“成熟”思想的沁人心脾豁人耳目的文字,依然忍不住为他与他们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一个“大写”之人的精气神而满怀钦敬和尊崇,故而特敬录秦牧先生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这样的生活(指作者青少年时代度过的相当艰难困顿的生活),加上优秀书籍的指引,使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公正之心,追求民族翻身,追求社会解放,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我就从这一点点儿觉悟开始,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道路……‘认真学习,不辜负做万物之灵;辛勤奉献,报答祖国的深恩。倒不是为了什么名垂青史,重要的是:俯仰无愧于人的一生。’”
最后再附带说明:《秦牧致姚雪垠》后来以《关于〈李自成〉的通信》为题,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姚雪垠研究专集》。该专集于1985年8月由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与秦牧信列于同一题目下的,还有《沈雁冰致姚雪垠》《郭沫若致姚雪垠》《胡绳致姚雪垠》《夏衍致姚雪垠》《林默涵致姚雪垠》等。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