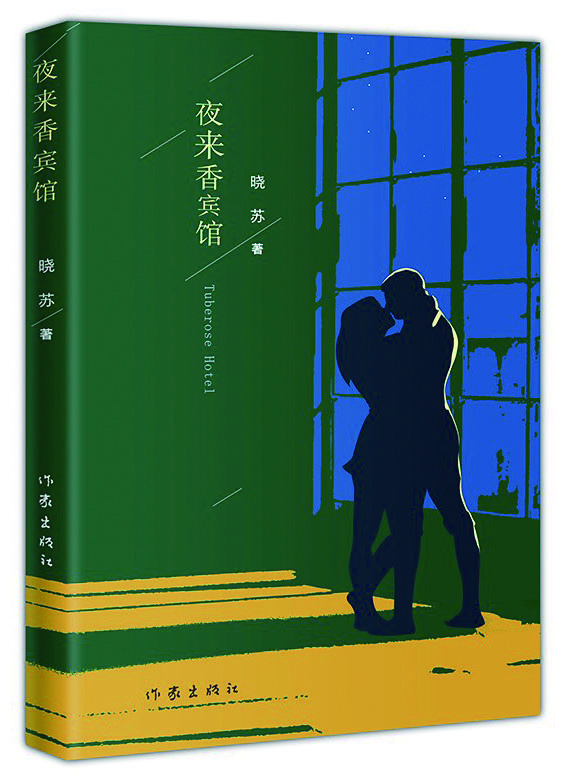一
题材的选择是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它最直接地反映了小说题材本身的拓展性和传播力,以及小说家对人类发展规律和传统文学精神的认识程度。好的小说题材,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规律,还是从文学精神来看,都必须是合乎自然的。
以《诗经》为例。《诗》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源头,其文学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本乎自然。《诗》的题材涉及之广,可谓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服饰、饮食、风俗、祭祀、宴会、劳作、徭役、战争、爱情、婚姻、家庭等等,无所不包。其中,性的主题就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一,从身体的自然规律来看,对性的尊重、赞美和歌颂直接体现了合乎自然的文学精神。《关雎》基本讯息即在性:“关关雎鸠”是飞禽的性讯息,“寤寐求之”是人类的性讯息,这种求偶的性讯息充满了整个自然界,使整个春天生机勃勃。“关关雎鸠”是自然美好的,“参差荇菜”是欣欣向荣的,“左右流之”是欢欣愉悦的,“琴瑟友之”是健康友善的,“钟鼓乐之”是幸福美满的,整个诗篇呈现的均是从性的讯息出发而产生的自然和谐的景象,人与万物合乎自然,顺应时令,生生不息。《关雎》居于三百篇之首,其文体范式和文学思想的典范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合乎自然的题材也贯穿于《诗经》始终。《摽有梅》讲的也是求偶,讲人如草木,也有春华秋实的季节,因此首先尊重时令,顺乎身体的自然规律,按时婚嫁繁衍,这就反映了“男女以正,婚姻以时”的道理,否则,不尊重自然规律,违背了自然时令,人就容易产生“怨”,就会影响个人、家庭以至社会的秩序。《桃夭》《鹊巢》讲的是嫁娶,《螽斯》讲的是繁衍,这都是将人回归于自然之中,以自然万物的规律来通观人的生存,不论是从文化习俗还是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理解其婚嫁规制、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都不可否认是以身体的生息繁衍为基础。再如《商颂·玄鸟》,是在严肃的祭祀场合颂唱的诗篇,首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性和繁衍,是商的始祖契的出生问题。无论我们是将其理解为氏族时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性行为结果,或者认为是春分时节祈神仪式上男女交配的结果,它都说明性的重要意义和神圣地位,而这也是“武丁孙子”及“方命厥后”“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的前提,是实现领土思想和统治理想的基础。
其二,两性关系作为性的表现形态之一,也反映了人类情感和秩序的层次关系。体现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促生了丰富的情感体验,如《有女同车》之喜悦,《殷其雷》之思念,《绿衣》之悲伤,《击鼓》之痛苦,《氓》之悔恨,《有狐》之担忧,《中谷有蓷》之哀怨;同时,两性关系还被进一步隐喻君臣关系、上下关系,乃至国家情怀,如《子衿》《简兮》《柏舟》《候人》《小弁》《何人斯》等篇章,皆是如此。之所以两性关系能对君臣关系构成隐喻意义,关键在于互信又莫过于两性之恩爱,失信又莫过于两性之弃绝,稳定平和的秩序必是以互信为基础,这也直接对社会秩序建设构成重要意义。因此,两性关系是建构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基础,以及家庭和社会秩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以两性关系来隐喻君臣关系,是社会秩序发展中自然产生的结果,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书写和艺术手法的瑰宝。可见,从文学题材、文化思想和艺术精神来看,《诗经》并没有回避性,而是尊重、赞美、歌颂健康的性、自然的性、美好的性。
自然的性,是小说题材选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主题,也是小说追求自然真实的境界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诗经》所承载的这类文学母题,随着文化思想的不断变迁,直至今天,仍然在书写和接受的正当性、合理性上面临着一定的争议。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曾批评士大夫们阅读小说的态度:“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换言之,士大夫们对书籍尽管有其等级分别观念,并不能给予小说足够高的文学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对小说的喜爱和传播。这种现象,古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即使是小说领域,也仍有等级分别观念,也会出现“恶之而弗能弗好也”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士大夫不能放下其社会职能的预期,其文学评判的依据也服从于正统地位的文学范式及其教化意义,所谓“恶”是出于社会职能,所谓“好”则是出于私人体验,时代的人文风貌对个人的心理产生深刻影响,使个人的阅读心理便呈现出这种既好又恶的矛盾,并使这种矛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当代学者王先霈先生就曾引用胡应麟的这段文字来说明,“性”的书写不仅使古代士大夫产生一面“恶之”又一面“好之”的矛盾心理,即使是今天的读者,也依然对此矛盾重重,依然是一种普遍的矛盾。晓苏的《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同样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对当代众多作家作品的性写作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以性作为原动力来阐释西方经典文学,尽管有“泛性论”的极端化倾向,但是四大情结的提出,尤其是“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仍然对今天的文学阐释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古今中外文学接受与研究,都不能脱离对人的自然规律的尊重,对性的书写之认同与接纳,这既是文学题材的选择问题,也是文学接受的问题。
晓苏评价同时代的作家的性书写,对其积极意义与艺术造诣莫不赞赏。之所以这种正面评价难能可贵,则主要在于这种自然的书写需要有过人的胸怀、识见和笔力,其接受也需要有超越世俗的坦荡和本乎自然的文学精神。晓苏不仅从理论上论证这种书写的价值,而且,近三十年来,晓苏也始终围绕着性,不断丰富油菜坡系列故事,总体上构成了对自然的、健康的、和谐的性的赞美和歌颂。如果说,90年代《山里人山外人》呈现出的性的题材,表现出来的是写作者的选材勇气,那么,《夜来香宾馆》则更多体现出高度合乎自然的人文精神与文学思想。换言之,性的书写已不再是一件多么令人心惊肉跳的事情,而是“食色性也”,性已被认同为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私人生活必然会面临的话题,而小说对农村男女的书写,也大略可以观察到农村的变迁进程及其现实问题。
综观晓苏三十年以来的小说题材,性书写也从隐秘的私人事件逐渐发展为普世意义的社会关怀,包括当前农村男女人口不均衡、人口流动等社会现象,普通大众更多接触到的是新闻视野和研究视野的数据信息,而至于这些群体真实的生活形貌,小说则有着不可替代的感知意义。其一,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晓苏的小说题材,看起来都是书写性,但是题材内容已越来越丰富,并整体呈现出性观念以及婚恋关系的嬗变,也越来越深地触及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以及人的情感、伦理、经济及社会秩序的集体变迁。其二,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评论者、研究者关注到这些性书写之外的问题现象,并将其解读为农村问题小说、弱势群体现象写作、农村城镇化进程写作、乡土文学写作等等,这些解读看起来各异,且即使是同一个文本也能解读出不同层次的社会价值,这并非评论者的局限或附会,而是性作为人类生存的自然母题,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宗法制度时期,还是现代社会,它都是人们建立秩序或改革秩序的基础,也是秩序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直接表现。
因此,晓苏三十年以来的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历程,之所以说从整体上体现了见证社会生活与人文思想变迁的文学意义,与选材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性的题材可以最敏感、最充分地反映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性的题材的确很容易引发广泛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思考。这也说明文学要真正实现人学的意义,首先必须要从题材的选择上本乎人性自然,使文学面对人的身体规律和生存的真实形态,而非凭空地书写社会生活和各种情感,这也是人首先必须是合乎自然的人,而后才可能成为合乎社会理想的人。所谓“侯王若能守之(道),万物将自化”。不只是认识和建构社会秩序要道法自然,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也须循此规律。
二
如何认识题材,也是小说接受的基本问题。合乎自然的文学题材,需要有合乎自然的文学解读,这是读者进一步使文学实现其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的重要环节。读者对题材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基本形态,以及传统文学精神的发展面貌。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世儒解释终不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诗》本身从文体到内容思想都极为丰富,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时期的学者受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其见解自然也不尽相同。然而,无论是(汉)包咸注解为“归于正”,还是(唐)孔颖达认为“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而“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或者朱熹所引“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不难发现,超越具体的解读来看,“思无邪”本身是指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问题:听觉、发声体现着最直接的感官感受;情感、思想的共鸣和同化,则更深一层;精神气质、人文风气,则又深一层。
可见,传统文学精神所崇尚的“道法自然”,乃在自然万物的视野中去认识人、发展人、尊重人的自然发展规律,以此为社会秩序建设的基本前提。朱熹注诗,学理、秩序、道德的色彩非常浓郁,其宗旨在于建构秩序和道德的典范,以稳固封建政治统治。时至今日,《诗集传》欲以文学来建构秩序的艰难和狭隘暴露无遗,但今人(包括写作者和读者)欲以文学来建构社会秩序的心理仍然普遍存在。这也就常常直接促使小说变成了一场道德的审判,而偏离了生活的本真形貌,限制了小说实现审美和社会功能的可能。
回到当代小说题材的接受面貌来看,对道德的追求和对身体的诉求,并没有从文学接受心理上突破经久的矛盾,因此,个人阅读往往一方面希望建构社会秩序,以掩盖身体的需求和苦闷;另一方面又希望逃避秩序,更大程度地面对这种诉求和困境。这也是晓苏的小说接受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以《道德模范刘春水》为例。《道德模范刘春水》是非常正面地将人的自然天性与伦理道德放在一起进行较量的。刘春水是一个单身汉,刘春水的两个兄弟也是单身汉,从习久芬的叙述来看,刘春水是个几乎完美的女婿。这就是对读者一贯的秩序观念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如果道德与秩序是高度一致的,那么,为什么道德近乎完美的刘春水却没有享受人伦的基本权利?从刘春水的叙述来看,追求伦理道德并不是他的思维逻辑,实现基本的身体诉求才是。这就向读者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如果身体的基本诉求逾越了伦理秩序,但是在其他方面都堪称社会秩序的典范,那么是否还能被称为道德模范?如果读者考量到了这两个问题,就会发现,这场较量以身体诉求的书写取胜,道德秩序也被分成两个层面:一是旁观者预设、建构的观念网络,二是当事人亲自建构或解构的行为意义。刘春水逃避村长罗日欢和宣传委员胡车的到访,从小说的布局来看,这个行为的结构意义就是成功地使旁观者和当事人的世界错开,形成两个无法相互理解、沟通的场域;进一步讲,这也对应地使小说的主题意义更加明确,即旁观者的观念意义上的道德欲望,实际上是以他人的牺牲为代价的,这种欲望出于无知,而且残忍;而当事人的行为意义上的身体欲求,对前者而言则形成了强烈的蔑视与讽刺。可见,这篇小说以分离、错过、回避的结构布局,反映了旁观者和当事者的视角差异,人的自然天性与伦理道德的无声较量,看似毫无锋芒,小说结尾只一句“阴沟”,便指出了不尊重人的自然天性与基本权利的伦理道德秩序,本身构造出来的就是非常荒唐也肮脏可耻的生存环境。所以,这并不只是双关意义的性语,更深层的是在指陈看起来光明宏伟的道德秩序下逼仄阴暗的生存空间。
再以《推牛》为例。《推牛》同样也是在反映人的自然本能与伦理道德的较量,最终同样是伦理道德以失败而告终。与《道德模范刘春水》不同的是,道德秩序与人的本能始终在纠缠斗争,并且从一开始道德秩序就在强势地掩盖人的本能,但是当以锦旗所象征的道德秩序将个人的生命一步一步扼杀了以后,这时,小说开始出现反转:被道德秩序遮蔽已久的事实真相瞬间澄清出来,整个道德秩序变成欺骗和剥削的谎言,它如同匕首,刀刀逼命。那么,作为高云天的儿子和孙子被赋予的“道德秩序”的编织者,周成功由农村户口转为了城镇户口,司机杨永寿由普通驾驶员被提拔成了客运站副站长,写稿人丁一根从一介教师变成了政府宣传委员,李佐也从村党委副书记升为了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最主要的策划人刘川则从县委宣传部部长高升为县委副书记。所以,从结构布局来讲,高云天的故事从被建构到被解构,始终以高云天子孙的生存为线索在推进,高云天的英模形象被建构得越热烈、越成功,则高云天的子孙被剥夺得越凶猛、越残酷;高云天的英模形象被解构得越彻底、越清洁,则高云天的子孙越自然、越充满希望。可见,旁观者构成的道德秩序,相较《道德模范刘春水》来说,是更加可怕,它甚至是有意为之的陷阱。直到血腥的悲剧发生,读者已无可忍耐,以至深深地恐惧起来。
宋明理学探讨“人心”“道心”,反映出人的自然需求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西方哲学家福柯则将现代人的自然的身体、灵魂与社会秩序进一步呈现出来,只是形式上不再是直接的压抑、禁止、剥夺、排斥的“否定性形式”,而是以“个体化、主体化、满足生命福利、技法欲望话语”等“肯定性方式”生产各种社会关系、真理体制。从这个层面来讲,两篇小说都是从题材上让人物不断产生着道德欲望,又不断建构着自然需求与道德欲望的矛盾,当人的自然需求与道德欲望、社会秩序之间抗争得越是胶着,读者也越能感受到小说人物生存权利和话语权利的轻微。最终,当生存诉求战胜了道德欲望,读者会感到小说人物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生存境遇是一种顺应自然并终于不再被继续扭曲、剥夺的智慧,小说人物回到真实、自然,看似无解又无尽的苦难至此才有了斡旋的余地。如果说《道德模范刘春水》是以虚与委蛇、委婉回避的方式获得了余地,《推牛》则以此消彼长、锋芒毕露的方式取胜,至此,也不难得知,回归自然不仅是小说人物扭转悲剧局面的智慧,也是小说家穿越社会秩序的重重障碍而终于抵达自然天性的写作智慧和人文关怀。
文学创作需要合乎自然,文学接受也需要合乎自然,不仅是伦理道德与自然生存之间的较量,就是性与伦理道德秩序之间也始终从未停止较量,甚至性的话语内部也开始呈现出不同角度的较量。这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必经的主题,也是个人的生命中大概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去面对的话题。
以《吃苦桃子的人》为例。《吃苦桃子的人》整个故事围绕着憨宝和车花来写,写他们的见面、相处、谈话和分别。一个单身汉,一个自由女,这是一个孤男寡女的关系背景,很明显,它非常容易产生正面的性书写。性是始终悬在憨宝和车花之间的一个话题、一个念头,所以,他们从彼此的性和婚姻谈到两人之间的性,逐渐使性具有了从话题到行为的可能,这就使性成为了故事的中心,也几乎要成为故事的结局。但是,小说势头十足地推进的性,却让读者完全落空了这种情节预测,并且让读者心服口服地把注意力放在苦桃子上,反复地咀嚼苦桃子的文学意义。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非常透彻地洞悉了读者的接受心理,而又非常成熟地控制了读者的心理临界点,因此,在最准确的时间,情节十分自然地出现了逆转,而读者浑然不知。为什么会浑然不知呢?因为性的书写一直在延续,丝毫没有停止。既没有出现道德、伦理与性的冲突,也没有出现身体对性的制约,所以,它是很难令读者警觉的。那么,实现苦桃子的文本意义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憨宝的心理。读者如何去理解憨宝的心理?憨宝在内心或许早已将车花和寡妇比了一百次,但是憨宝非常自然、平稳地与车花保持了一定距离,这就是憨宝的打算,是符合他的真实处境的。所以,憨宝和车花之间的悬念无论如何千钧一发,都必须回归到憨宝的自然常态,憨宝必须要维持属于自己的常态的、持久的“美好”。从人的自然生存角度来看,这是性的话语内部发生的一次较量,所以,它可以说是更具体细致,也更富有瓦解功能的一次探讨。
尽管这使小说关于性的书写看起来更具备内部反省的功能,但深究起来,它还是指向了对伦理秩序的更深层次的瓦解和批评。憨宝对寡妇的忠贞在家庭伦理秩序之外,它并不具备伦理秩序的天然合理性;相反,车花与司机的清白本是在家庭伦理秩序之内的,但它却产生了读者接受心理上的狐疑。这里面就暗藏了一个身体与伦理秩序的悖论,即身体(甚至加上情感)的忠诚是否就能保障伦理秩序的纯粹和稳固?显然,他们都没有指向对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无论是车花希望僭越界限,还是憨宝守护的界限,都并非读者所建构的社会秩序观念。那么,它有什么突破性意义呢?它更直接地指向了社会伦理秩序的语义范畴,使读者打破秩序的外延,进而考虑将这些貌似混乱的关系也纳入秩序,这就又出现了一个悖论:这种纳入,是否说明读者本身也是秩序的破坏者,或者同时也是新的秩序的建设者?如果被认为是破坏者,是否又说明读者本身就是以伦理秩序在碾压弱者的生存权利?如果被认为是建设者,是否又说明正在丧失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感?这一连串的悖论,都步步逼近伦理秩序的评判意义,也即,伦理秩序是否具备其评判的有效性和公平性?这些都会引导读者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并回归于社会现实问题,使文学进一步实现其社会功能。
综观之,《道德模范刘春水》与《推牛》是不同的两种艺术结构和审美情感,共同地呈现了人的自然诉求与道德欲求之间的关系形态,并逐步剥离出各个层面的社会问题和心理状貌。至于《吃苦桃子的人》,则由对伦理秩序的外部观察转向了内部反思,更进一步提出了人的自然诉求的层级差异与范畴变迁,不断剖析出社会普遍存在的秩序悖论。三篇小说之间较典型地构成了一个逐渐向内审视的层级关系,呈现出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被逐层破坏又被不断建构的社会进程,以及秩序观念逐渐由瓦解到重构的意识形态。
因此,以合乎自然的接受心理来面对文学题材,是发掘小说题材与艺术成就的重要途径,它可以进一步使作品世界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使小说题材不断生发出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
(摘自《夜来香宾馆》,晓苏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