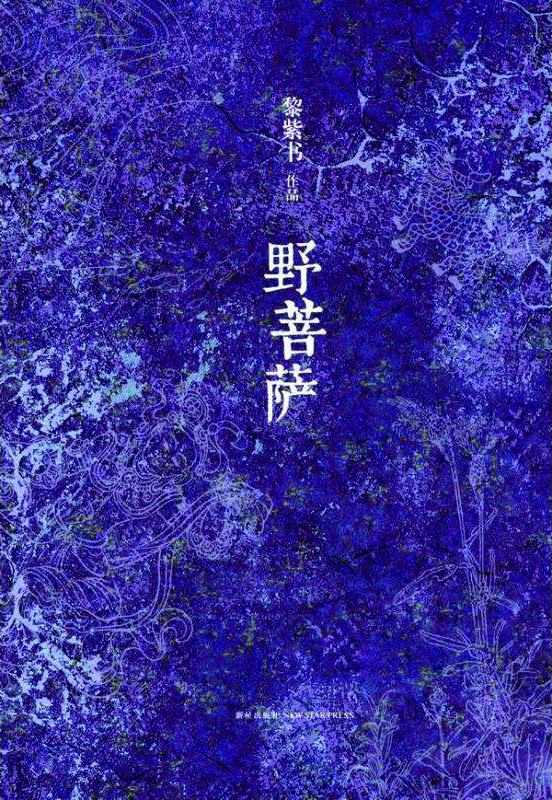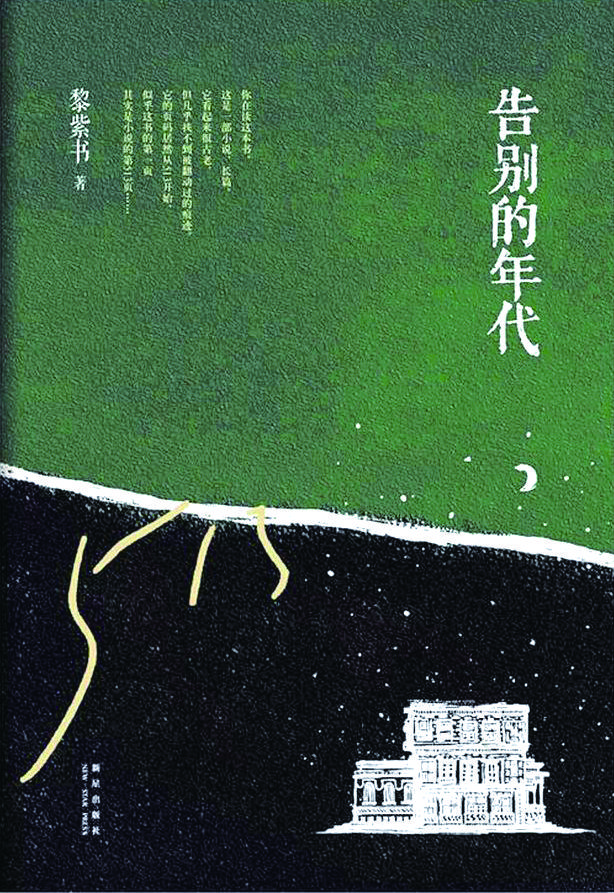黎紫书在充满喧嚣和论争的马华文坛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并非学院出身,也没有旅台的留学经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马华作家。但黎紫书用自己的方式出道,并迅速成名。1994年,她以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得第三届花踪马华小说奖首奖,之后蝉联多届小说推荐奖及散文奖,成为花踪文学奖历史上得奖最多的本土作家,形成了轰动一时的“黎紫书现象”。
正如黎紫书给自己的定位一样:“我的文字,终于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异端邪说。”无论是前代本土和旅台作家,还是同为新生代的黄锦树、钟怡雯,黎紫书与他们的创作主题与风格都不相同。出生和成长于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她的小说既有天然的南洋乡土风情,也背负着原生的国族焦虑——“那些不能被新学的语言所覆盖的乡音,那些经多年书写与宣泄后仍排遣不了的惊慌、恐吓、阴霾与忧伤,他们从未消散,都融进了我贴身相随的影子里”。如果说乡土抒情和国族焦虑书写来自于“马华作家”这个身份本身,那么在这之后的黎紫书,写下了大量幻想、阴暗、表现人性无名角落的诡谲文字。她发现了最适合自己写作的温床:“我确知自己像老鼠一样的个性,总要在阴暗与潮湿之中才能得到存在的自觉。”从创作实绩来看,黎紫书不愿过多纠缠于“马华文学”这个充满着历史阴影与尘埃的标签,她“放弃追寻稳固、统一的族裔身份,在离散的状态下自由表达着我的存在的多重意义和质感”,这是黎紫书个人写作轨迹的偏移,最后也被证明是马华新生代作家的一种集体性的转向。
历史寓言及其魔幻化
以诡谲的方式书写带着南洋雨林气息的家族寓言,这是黎紫书小说中最早被侦破的特质。《国北边陲》中,一个流浪者的剪影,小镇、雨林和边境,上一代族人的回忆像电影片段一样闪现。小说有多层的“断根”隐喻:“世代子孙活不过30岁”的巫蛊、家族的灭绝与倾覆、无根的龙舌苋。龙舌苋的根是惟一的解药,也是流浪者寻找的对象。然而最终流浪者发现,龙舌苋是无根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家族灭绝的焦虑导致陈家子孙在20多岁急于繁衍,这如同末日的狂欢,充满荒诞与悲情;被记载的世间珍奇之药龙舌苋,敌不过马来本土随处可见的壮阳草药东卡阿里。《国北边陲》用颇具魔幻色彩和心理书写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寻根寓言。马来西亚华人族裔受到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双重影响,在这影响之下,黎紫书用奇崛的小说语言,表达出一种根植于历史、国族、原乡的焦虑。
除了像每一位马华写作者那样思考国族命运,黎紫书早期也在小说中表达对于历史的思考。《七日拾遗》中的神兽“希斯德里”(history),长相如狼似虎,非猫非狗,专食沾满历史尘埃的书册。老祖宗与神兽的设置,是肉与灵的分离,是对历史匮乏的戏谑——老祖宗年过百岁,在族人中自有知识和阅历的双重权威,却对神兽日日饲以书画图册,不让所有人知晓。这种戏谑背后是对缺席历史的焦虑——个体关于存在本身的焦虑,作为社会成员对于家国、民族短暂历史的忧虑。《七日拾遗》用魔幻的笔触和诡谲的玄想色彩,将这种历史的焦虑变形。另一则小说《蛆魇》用灵魂重生的视角描述一个重组家庭的残缺与病态的欲望,充满热带雨林黏腻、腐烂和死亡的气息。
黎紫书笔下有着浓厚的原乡记忆。这种历史感依托于她的家乡——怡保。怡保在马来西亚有“锡都”之称,这里融合了闽粤文化,具有浓郁的马来西亚华人氛围。“我的记事薄上写满了吉打州的乡情:金光色的稻田、天空染血的夕阳、一群在田里捕捉泥鳅的孩童,赤铜色的皮肤,汗水沿着颈项汩汩而流,风,哼着小曲去拾稻穗”,黎紫书善于写原乡的风景,以及怡保小镇生活的世俗百态。《州府纪略》将时代变换的缩影定格在怡保镇,以不断变化的人物视角和粗犷的笔触,拼贴出女伶谭艳梅唱戏、嫁人、革命与死亡的传奇一生。小说高度浓缩了马华群体上世纪的生活现状,那些卖茶果的潮州婆、卖海南鸡饭的福建佬,后来也出现在黎紫书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中,几乎成为黎紫书最为稳固的原乡记忆。
在《告别的年代》和《推开阁楼之窗》等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五月花旅馆,这一马华群落随处可见的普通旅馆,变成黎紫书笔下一种离散的符号及隐喻。住在阁楼和旅馆中的女人,只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群落的暂居者,是过客。女性命运变迁与无根的漂泊,是黎紫书书写原乡时的一个主题。《野菩萨》就是以中年女性阿蛮的回忆意识流还原上世纪中后期马来西亚华人群落的生活状态,黑道横行、政治倾轧、阿蛮及其胞妹的情谊,黎紫书以这种多棱镜的方式,揭开生活背后的心酸与倔强的底色,延续着前代人对马华女性困境的书写。
伦理错位与弑父冲动
黎紫书常常在散文随笔中审视和反思写作的必要性。写作成为她处理与这个世界关系的重要方式。但更多时候,她在写作中审判自己。从《推开阁楼之窗》到《卢雅的意志世界》,再到《告别的年代》,她将大量个体的存在性经验,投掷于写作这块幕布之上,变成一幅幅或诡谲或浓烈的静物画。那些童年时代被戕害的创伤性记忆,作家本身独特的幻想方式,和马来西亚蕉风椰雨、密林虫豸的地理和人文氛围,共同形成了黎紫书小说的结痂美学。
《疾》是一篇憎父的独白——小说主人公在父亲的棺椁前回忆一切,病房的死亡前奏,父亲被拘的日子,缺乏父爱的童年生活。主人公对父亲充满恨意,讲述的情节支离破碎,但细节丰满,情感逻辑异常完整,文字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宣泄。《蛆魇》中的亡灵少女是母亲再嫁的拖油瓶,丧失了亲生父亲的关爱,不受继父及继祖父的待见。这种恨直接导致她产生杀死弟弟的报复心,恨意如同热带雨林的白蚁,滋生心灵的蛆魇。黎紫书的小说中,只要有父亲的角色,那么他或者是缺席的——“只要一天你还在,我就无法对婚姻释怀”,或者就是一种反面的典型:常年离家在外、吃喝嫖赌、蹲监狱、不得善终。小说中折射出创作者自身的童年阴影,这成为黎紫书小说很强的叙事动力:精神上的弑父冲动。用文字将“父亲”一遍遍杀死,或者将由缺乏父爱导致不堪的童年经历,一遍遍用文字洗刷,那种宣泄仇恨的快感,阴郁的基调,成为她小说抹不去的底色。
这种弑父的冲动,进而演变成伦理错位和欲望的夸张变形。《蛆魇》中孙子与爷爷令人作呕的不正当关系,《我们一起看饭岛爱》中在同一逼仄空间中的母亲与儿子,是通过网恋纾解生理欲望的彼此。伦理关系被遮蔽后,人性的幽暗便如同荷尔蒙般滋生,在沉默喑哑的生活里如暗流一般蔓延开去。《我们一起看饭岛爱》像是被定格的留声机,人人都成为了都市景观中冰山丛林的一角,把都市生活的乏味、冰冷、孤寂,平静地呈献给读者。
黎紫书这类小说中存在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国族的、伦理的、性别的关系都是错位的,人与人之间最佳的距离是陌生人般的冷淡疏离,一旦有血缘和伦理关系的牵扯,她就以极强的幻化能力去打破所有桎梏,深入人性晦暗和隐秘的边边角角,用诡谲绮丽的意象,敷演出她那如荷尔蒙般旺盛分泌的另一重世界。
呓语、梦游与都市臆想症
黎紫书在马来西亚大报《星报》有多年的媒体生涯。她长期以记者、作者和观察者的身份,游走在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欧洲等世界各地。这些异域的旅行经历给她创作带来了离散气质,同时也带来更超越和开放性的写作姿态。她在散文集《暂停键》中旗帜鲜明地表态:“所谓祖国,所谓原乡,成了我岁月中的宾馆,生命长旅中的驿站。”“把灰蒙蒙的原乡和异乡都关在窗外,好让自己别再去意识到我在这广大世界中的位置。”相比于国族叙事这个“命题作文”,黎紫书显然更痴迷于书写人性、欲望与罪恶本身。
黎紫书的笔下,旅行如同一场漫长的梦游。她尤其喜欢用精湛的短篇去呈现人生旅途中那些沾满湿漉漉回忆却又无意义的片段,就如同《假如这是你说的老冯》,那种人在旅途中最常见到并擦肩而过的无名过客。面临日复一日的庸常的生活,她没耐心去描摹生活的一笔一画,而是逃遁于幻想的世界中,沉迷于个体的呓语。这种逃离的姿态,在小说中是令人着迷的。《烟花季节》里女主人公在琐碎寡淡的生活中怀念年少的私奔,一种生活的纵深和落差感,让文字浮现出巨大的情感张力。《此时此地》呈现的是两个毫无交集的普通人,他们每日擦肩而过,并为对方取名——“何生亮”“Winnie”,两个人便由此虚构出四个人的多角关系。平庸的生活里,总是有人在假想中塑造完美的他者,以投射欲望及幻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囿于“此时此地”的生活。黎紫书的小说,就是日常生活的写实与荒谬之间的一次次探险。
黎紫书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视为“想象中的想象之书”。为了长篇小说的体量与尊严,她在《告别的年代》中,又重新返回马华原乡,书写了马华土地上的女性、五月花旅馆、街道巷弄的世俗生活,故事主体是小人物杜丽安的奋斗故事,充满了现实主义气息。但黎紫书不甘于其平淡,在小说中安置了许多装置。比如小说是从第513页开始写起,这是个让马来西亚人敏感的数字:1969年5月13日所发生的种族流血冲突,造成极大死伤,是历史的惨痛记忆。但《告别的年代》与此历史事件并无关联,仿佛是作者故意投下的烟雾弹。小说多层次的叙事、复杂的结构、多元的视角转换,这一切后现代主义的技巧,悬置了作者本身的写作意图。马华历史成为掏空的符号,是作者构筑她这“想象之书”的空心砖,使其穿过历史、国族、原乡等写作的重重雾障,抵达她所期待的终点。《告别的年代》中始终包含那些过去不断出现的命题:阁楼上的梦游、掷向虚空的呓语、受困于历史的臆想症,这些短篇小说中浓墨重彩表现的元素,在长篇小说中一如既往被呈现出来。
总之,黎紫书的创作,有马华社会的缩影,有历史断根的焦虑,有回溯和寻找的写作冲动。但随着黎紫书写作经验的扩张,以及对写作本身的思考,她从故乡怡保、马华群体的本土生活出发,写出了更开放、更具有超越性的文字。同时,黎紫书又是一位“内倾型”的创作者,回忆与往事、童年创伤、呓语与臆想症,都像热带丛林里弥漫的湿气,覆盖于她的小说世界。城市、历史、社会和个体经验,就在这种呓语式的写作中不断扩张。正如王德威评论道:“不论是书写略带史话意味的家族故事,或是白描现世人生的浮光掠影,黎紫书营造出浓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
马华女作家黎紫书的小说,终究变为那掷向历史的烟雾弹。在喧嚣的历史中,浮现的是她对于人性幽暗深处持之以恒的探索,而远处,如她所预言,“南洋已经逐渐沉默在更浩瀚的时代之中”。